书籍资料库
中央欧亚民族的成就与研究上的困难丨丹尼斯·塞诺
❖作者: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
❖译者:王小甫
❖校对:罗新
❖选编自《论中央欧亚》,《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年。本文标题為主编所拟。
❖“新清史”专栏编辑:蔡伟杰,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博士候选人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如果我们试图指出探明中央欧亚历史的一些特点,从通史(general history)的观点看来是最重要的,那么主要的一点就是这片区域在与之接壤的那些伟大定居文明间所起的一种媒介作用。
尽管从统治的意义上说,巨大的游牧帝国也难以覆盖整个中央欧亚,但这些帝国中确有一些疆域如此辽阔,与不止一个定居文明接壤。而中央欧亚那些名义上不隶属于这样一个帝国的部分,政治上发育得还不够,不足以阻碍经由他们而进行的交流。游牧民带着希腊的外高加索的或伊朗的艺术,穿越西伯利亚荒原前往中国,并将任意采取的诸多艺术母题混合进一种艺术之中。用卓越的考古学家埃利斯·敏斯爵士(SirEllis Minns)的话说:"一块中国北魏墓砖会怪兮兮地类似伦敦圣保罗教堂墓地为人熟知的北欧浮雕,这种情况并非纯属巧合。"
不仅是艺术母题被带着穿过了中央欧亚,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货物。本书中到处都提到的伟大的丝绸之路,其大部分路段都经过蛮族控制的地盘。只要有一个游牧国家兴起,就会带来旅行条件的改善,从而中国和印度、伊朗乃至西方世界之间的交通就变得更加活跃了。
渗透进游牧国家的宽容精神,使得他们对宗教影响特别放。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经过中亚到达中国,基督教也是如此。这些宗教有的在中国留下很少的痕迹,另一些,尤其是佛教,影响却较大。有意思的是,尽管商业和技术基本上是沿着一个由东向西的方向流动,有关精神的事物却是由西向东流动。印度或中国的思想在西方没有留下痕迹,而伊朗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和基督教却在远东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我认为,这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央欧亚起到了一种媒介作用。无论那些最大的游牧帝国可能怎样扩张,其中心都位于蒙古高原,其主要的兴趣都集中在中国身上。
跟任何地方一样,统治者的宫廷也变成智力活动的中心,由于这些中心总是邻近中国而不是邻近西方,牧师和传教士只好从游牧帝国的西部边界直奔远东以便被引见给统治者。因此,方济各会的修士们不得不前往蒙古高原的哈拉和林以拜见大汗;可是,中央欧亚的西部却没有一个使得一个道士想要前去投奔的人。
统治者宫廷的位置也导致了大量欧洲人或伊朗囚犯和"难民"出现在蒙古高原和中国。人们常常忘记,13世纪中国有一支帝国卫队是由阿兰人组成的,其故乡在高加索,而当时在中国北部还存在一个俄罗斯人的移居地。
至于说到技术成就从东方向西方的传播,例如丝绸的生产或印刷术,我倾向于认为,正是欧洲人在其传布中起了推动用。毫无疑问,把白人带到地球最远尽头的冒险精神,几乎是他们的专利。欧洲可以夸耀产生了最伟大的发现者和旅行家,尽管就中央欧亚来说,首次在中央欧亚旅行并为我们所知的人,只有很少的几个,而留下一份有关其旅行经历书面记录的人就更少了。13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加宾尼(PianoCarpini )、鲁布鲁克(Rubruck)、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人的成就,令我们深深钦佩,但是他们的报告表明,还有好多其他欧洲人先于他们到过蒙古高原,其中某些人返回时必定带回了中国技术的知识。马可波罗的书面报告有助于我们评估由他和其他人口头传播的信息的总量。
尽管传播技术发明可能是欧洲人的成绩,但传播能够实现却是借助了那些庞大游牧帝国的组织系统。
中央欧亚对通史主要贡献的其他方面,更加难以估价。在这当中,人们注意到,在漫长的岁月里,蛮族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敌人,难以想像,如果没有他们的压力,中国历史会发生什么变化。光是公元以后,中国就被蛮族王朝统治了大约800年。匈人、阿瓦尔人和匈牙利人如此成功地入侵欧洲,成为他们各自时代的重要因素。不过,在所有的蛮族国家中,蒙古帝国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最难以磨灭的印迹。从这一总的观点来看,蒙古对中国的统治或许不像它对中东命运的影响那样重要。蹂躏波斯和花刺子模,使其再也未能从这场毁灭中恢复过来,洗劫巴格达,谋杀哈里发,这些无论怎么说都是主要事件。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冲击相当大,在这个国家的典型特点中,独裁传统的发达必须认为是蒙古占领的结果之一。直到近代以前,没有国家实现过蒙古人那样的扩张。直接或间接,它都给通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研究中央欧亚有其特殊的困难,差不多所有的困难都是由缺乏中央欧亚各民族自己的原始史料引起的。这些民族,历史地讲,是不可思议地活跃,对历史传统少有感觉,每一个成功的帝国都过于短命,而不足以建立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过,严格说来,这只是书面史料缺乏的心理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物质的原因,是更重要的。书写艺术在蛮族中并不普及,区区几份书面文书,在一个经常移动而没有固定居处的社会,其幸存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然而应该说,那些留存至今的土著历史的典范作品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它们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其稀有,而且也因为其优美,以及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游牧帝国的构成及其功能。有两份典范作品值得特别的关注:鄂尔浑河附近发现的突厥文碑铭,断代为公元8世纪,13世纪的《蒙古秘史》,用蒙古语写成。这件事本身也是意味深长的,即二者之间流逝了大约500年,却没有片言只语的当地文献留下来对此加以说明。奇怪的事情还在于,后一份文献的作者对前一件碑铭所处的那个时代毫不知情。另外一群人用另外的语言写了他们自己的历史。然而,当你两者都读,当你进人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你不禁就明白了蛮族历史永恒的同一性。

▲鄂尔浑河附近发现的突厥文碑铭
我们的确握有几份当地史料,但都不容易使用。鄂尔浑碑铭所刻写的文字必须经过解读才能明了其内容。由于它们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最长的文献,几乎没有其他借鉴可以帮助语言学家。因而有一些晦涩的段落恐怕会永远保持晦涩。《蒙古秘史》的阅读也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一项困难任务。其原文是用蒙古语写成的最早的文献之一,所表现的特点在任何已知蒙古语言中都找不到。然而使得阅读这部编年史更加困难的是它得以保存的奇怪形式。蒙古语原文是以汉文音译的形式留存至今的,这就是说,多音节的蒙古语被尽可能地音译成汉文的单音节形式。由于我们并不知道13世纪汉语文字的准确音值,而且我们直到《秘史》发现才知道13世纪蒙古语的发音,原本的重构显得相当困难。有些困难仍然没有解决,但既然只是语言学问题,因而无损于原文的历史学用途,它构成了蒙古历史的主要史料,而且,确实是中央欧亚最有启发力的书面史料。
因此,找们手里掌握着,有关整个中央欧亚差不多两千年间,仅有这两份主要的原始史料。所有其他我们知道的事,都来自由围绕中央欧亚的定居民族写下的史料。这就把历史学家放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位置上。显而易见,当他承担起重构历史的任务时,他就必须面对这些困难,他掌握的都是敌对民族提供的信息。然而,使得该历史学家任务更为复杂的是,他必须洞察中国和波斯语言学的神秘,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为了撰写历史,他必须依靠中国、伊斯兰和希腊的史料,这还只是主要的三种。偶尔,他甚至还不得不对付斯拉夫语的材料以及中古拉丁文。如果他不是这每一个领域的专家——谁能声称自己是呢!——那他就只好依赖二手信息,在多数情况下这全然不足以为他的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本书的另外一部分显示了处理汉文材料的困难。由于可靠的译本非常稀少,镶进画里的每一小块马赛克石都必须费劲敲打才能到位。波斯文史料的处理要稍微容易些,不过即使在这儿困难也是如此之大,一个在料方面训练有素的史学家会发现,甚至要理解所面对的难题都是困难的。与汉文材料相比,波斯文材料的主要优点是数量较少,也常常是渲染多、说明少。危险在于缺乏原始性,几个世纪前的陈旧信息被说成是当代的东西。作品被拷贝了再拷贝,毫不顾及在其背后可能或不可能有的真实情况。这种因素在拜占庭史料里也并非全然不存在。这里写作的苛严,使作品符合某种经典的企图,扭曲了真相,并导致年代错乱,还总是不易被觉察。不过,至少拜占庭史家是欧洲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仅我们更好理解,而且整个来说也更具批判性。汉文、波斯文和欧洲文字的史料,把各自不同的光亮投射在它们所记载的事件上。虽然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光线和阴影的多种效果使得难于辨认被不同文字所描述的同一史实。
突厥和蒙古的专有名词(propername)经过一个中国或波斯历史学家音译以后,如果是以前并不知道的词,经常就变得不可辨认了。这不仅是由于该历史学家一开始的粗心大意,而且也因为用汉字音译外来词或用阿拉伯文字音拟外来词所固有的困难。阅读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古代文本的困难更是众所周知,这儿有必要作一详细的描述。通常,上下文帮助我们补充那些阙失的成分并进行必要的订补,可是,如果要重建一个专名的原始形式,从而常常是为了比定有关事件所提及的人物,要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归根到底,只能通过大量而详细的搜证。翻翻一些欧洲的蒙古史书就暴露出来,专有名词的拼写是如此不一致,以致学生试图归因于两个不同人物的业迹,其实只是一个人完成的。历史学家还不得不面对一种相当初级的困难。就是汉文名称(就正在讨论的情况而言,就是汉文音译的其他外来名称)的不同的欧洲音译。他会发现,在一本欧洲的手册中。例如一个汉文词汇的英语音译,该词用13世纪的读音(常常不同于今天的读音),音译的是一个欧洲专名的波斯语形式。链条越长就越容易误解。对非东方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必须作为一条绝对规则的是,决不把任何假说建立在与某本欧洲作品中已有的专名译法类似的基础之上。从18世纪以来,匈奴(Hsiung-nu)与匈人(Huns)的勘同就一直困扰并仍然困扰着我们的手册,尽管那整个学说其实是建立在两个名称音译间的模糊类似的基础上。
刚才这里提到的这些困难,总的来说都是语言学方面的。它们只是构成了历史学家艰难旅程的第一道障碍。如我前面说,几乎我们的全部文件都来自所描述人群以外的史料。
中国人或拜占庭人对蛮族的历史感兴趣,只是限于其政治利益涉及的范围。一个民族的名称出现在汉文史料中,只是在它对统治意味着麻烦时,记载大都也只限于干巴巴的列举入侵、胜利和战败。有时候,蛮族文明的一个特别奇怪的特征会打动某个中国史学家的想象力,于是便进人他们的史著或某种百科全书。一个习惯于丰富的文字史料的历史学家,看到中央欧亚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满足于如此贫乏的材料,一定会大吃 一惊。突厥人建立过中央欧亚最重要的帝国之一,他们在大约200年里是统治王朝最危险的敌人,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如果编成欧洲的书本形式,总共不会超过大约200个印刷页。有关其西部帝国的记载收在唐代史书中,译成法文总共不到40页。
无论如何,我们有关中央欧亚历史的知识并非完全基于文字史料的证据。考古和语育材料也给我们补充了不少信息,甚至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问题的线索,而这些问题在文字史料中全然没有提及。
由于中央欧亚文明的特殊性质,考古发现和旧大陆任何部分比,在数量上几乎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修建城市,其文明遗迹必然是容易消失的。大多数发现都是金属小器物,很少的情况下在冻土里保存着有机物质:衣服,甚至人的残骸。由于涉及的区域浩瀚广袤,人口又极端稀少,考古发现直到现在都非常少,因而我们有信心期待, 将来会有重要的考古发现。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领域,考古成果很少能转换成历史名称。把考古发现归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群总是危险的。在没有外部证据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把一座墓葬归属于一群人而不是另一群人?当读到这种墓葬属于一个突厥或蒙古人时,我忍不住要问一个好笑的问题:是不是找到的锅、碗或者就是头盖骨用突厥语或蒙古语句子跟其发现者打招呼,从而便利了他的比定?
这就带给我们第二个问题:考查语言学家对中央欧亚研究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语言学家能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小,只能用于对原始或史前时期作些阐明。重要的事情又是相当负面的:你不能没有明确的证据就把一种语言归属给一个民族。在这个关节点,提醒一下是适当的,无论你阅读手册能得出什么,我们委实不知道匈人、阿瓦尔人、匈奴以及柔然等说的是什么语言。当我们把他们说成是突厥人和蒙古人时,我们不过是在躲避问题。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宜假装说这个领域史学搜证的结果一定能是可靠的,就像我们习惯的对欧洲历史的研究那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所有的批判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可靠的历史是写不出来的。人们沮丧地看到,这样一种基本的谨慎一直被忽视到了何等程度。历史学家们大都是用忽略的办法克服这类研究中的语言学困难的。例如,写成吉思汗的书不计其数,罕见有比其他三、四本欧洲人所写的书更具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少有比作者个人的"解释"更其原创性的著述——其"解释"的可靠和透彻,大约赶得上一个六年级学生给朱利乌斯·凯撒(JuliusCaesar)的评价 。现在的问题是,比如,以某种程度的准确性撰写中央欧亚历史是否可能?至少在目前阶段,集中对所有可以获得的史料进行翻译和注释,放弃任何综合的企图,是否就不太好?我认为这样一种说点必定不会被接受。
进一步收集材料显然是必要的。我认为,对伊斯兰史料面言尤其重要,据我看,这些史料很可能产出比我们期待于汉文史料的更重要也更丰富多彩的材料。还可以期望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研究将给我们贡献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央欧亚的知识。这个领域的前景是远大的。对语言学研究就不能这样说了,不大可能会发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语言学资料了,因而研究将只好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材料。分析性研究要确实有效,需要一些可行性假说。因此,我不想提倡放弃任何综合工作的尝试。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应该带着一种格外的批判精神来进行,应该基于所有可获得材料而不是任意挑选出来的一两件事实。
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东方学家应当提出的建议是:多否定,少肯定。如果他们要开 始时不时地证实某些事情。而且满足于对事情进行描述,这个建议更加有益了。有人过于热衷轰动效应,热衷于发现,比如,某个新的惊人的迁徙。这种方式是要不得的,这已经为格鲁塞(ReneGrousset)所证明,他的《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值得作为一个能作和该做什么的完美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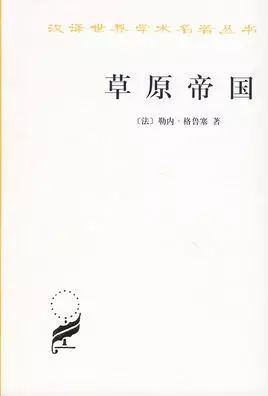
▲《草原帝国》书影
有志于中央欧亚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首要品质是怀疑。妄想轻易地、毫无根据的比定很可能就是最大的危险。我前面提到过,匈人和匈奴的历史勘同是基于其名称的一种模糊谐音。例子很容易就可举出好多,经常有人读到公元前的突厥人或蒙古人,尽管前者只是在6世纪才出现,而后者在9世纪以前还没有显露(要明智些就到13世纪再提他们)。当有人检查这些说法背后的依据时,他会发现,整个这些无根之谈,如同把希罗多德提到的那些神话人群如独目人(Arimaspoi),说成是突厥人或蒙古人。 希腊人的北方净土(Hyperborean)山被比定为阿尔泰山或乌拉尔山,或喜马拉雅山,以适应任何特定假说的需求。我们有关丁零人的全部材料总共只有汉文史料中的几页,包含很少的可用信息,他们却在一本又一本书中被巧妙地比定为萨莫耶德人(Samoyedes),依据仅仅是,据说他们使用雪橇。人们常会因为缺乏批评精神而困惑。知识狭隘、一知半解的人,追随着蛮族的脚步,由于像蛮族一样被排斥在宜人区域之外,而避难于中央欧亚草原,那里也许是业余历史学家最后一处快乐的围场。
有一点儿怀疑态度,人们多半就能避免中央欧亚研究中的很多大错。
可是困难在于,光有批评精神还无济于事,还需要完善的目录学知识。若干年以前,有个最杰出的宗教史学家对中央欧亚的一个神做了极其透彻的研究。他煞费苦心地分析了那个神名所在的那段突厥文碑铭,尽其所能使他符合总的图景。唉!那个神只是一个误读,差不多五十年前在一篇最专业的文章里就纠正了,那篇文章的标题一点都引不起宗教史家的兴趣。可怜啊,这个有问题的神在未来的许多年,都可能会困扰宗教历史的知识手册。
例子还可以举许多,不过这些就足够了。综合研究,如果是主张准确性的话,必须建立在牢固的事实基础之上。那些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核查基本材料可靠性的人,应该戒绝涉足中央欧亚历史学。不懂强于弄错,或者用伯希和——他在这一领域根绝的错误比任何人都多——的话说:"Unescience probe doit se résoudre à beaucoup ignorer(一门诚实的学问须承认有所不知)。"
我试图把中央欧亚放进历史的总体框架中,并指出它的研究特有的问题。对于带着真正的批评精神和学术准备进入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更有作为的研究领域已所剩无几 。要做的努力相当大,因为没有谁能把握中央欧亚的问题而不必预先研究至少已两个其周围的文明。无论如何,辛勤耕耘终将得到回报,发现会连续不断,新的世界将会展开在他眼前,只要他无畏地在这片未开垦的土地上劳作。中央欧亚的学生必须面对先驱者的艰辛和苦难。收获肯定是巨大的,可劳动者还不多。

转自“E史学”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