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徐冲丨何为“五胡”?
一、引 言
何为“五胡”?在“五胡十六国”已成通用词汇的今天,关于这一来自中古史料的特定称谓,学者间的意见反而愈加纷纭了。宋元以降的主流理解,将“五胡”理解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即永嘉之乱后至北魏统一在华北先后登场的五种主要族群[1]。而对此提出挑战的异说,管见所及主要有以下三种:
1.“五胡”称谓源自南匈奴之“五部胡”。“五胡”仅指匈奴系的屠各刘氏与羯人石氏[2]。
2.“五胡”是对当时少数族的一种泛称或虚指[3]。
3.“五胡”原指“五主”,即匈奴系汉赵与后赵政权中的五位杰出领袖,后在东晋十六国末期发展为将“五族”囊括在内的新概念[4]。
其中主第三说的陈勇一文是目前所见关于这一问题最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其基础应来自作者对十六国史料与历史的长期关注[5]。文章发掘出晋宋之际也就是“五胡时代”行将结束时才是“五胡”概念发展的关键时期,为研究的继续深入提示了重要方向。
笔者近期在考察元嘉五年(428)谢灵运上宋文帝《劝伐河北书》时,意外发现南方的建康精英反而热衷于言称“五胡”[6]。由此反观“五胡”称谓相关史料,逐渐意识到仅从“五胡十六国史”的内部视角进行思考,是这一问题始终难获突破的关键所在。“五胡”虽然与东晋南北分立,但源自汉晋历史的天下秩序及其意识在这百年间并未消失,仍在背后持续发挥着历史作用。这一点,如后文考察所见,对“五胡”称谓的出现与传播至关重要。
二、“五胡次序”故事的史料批判
前秦、后秦交替之际在苻坚与姚苌对话中出现的“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相关文字,一直是学者讨论“五胡”意涵的基础性史料。无论对“五胡”的理解如何相异,学者并未怀疑过这一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多以此为基础与其他特定史料相结合,展开自身所主张的“五胡”说。笔者将此史料称为“五胡次序”故事,本节先尝试对其进行史料批判工作[7]。
学者引用的“五胡次序”故事以《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为主,不妨先来看看这段文字前后的具体内容:
(苻)坚至五将山,姚苌遣将军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侍御十数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进食。俄而忠至,执坚以归新平,幽之于别室。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苌又遣尹纬说坚,求为尧舜禅代之事。坚责纬曰:“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坚既不许苌以禅代,骂而求死,苌乃缢坚于新平佛寺中,时年四十八。中山公诜及张夫人并自杀。是岁,太元十年也。[8]
或缘于对“五胡次序”的关注,学者的眼光多为姚苌与苻坚的对话内容所吸引,对其中涉及“图纬符命”的部分阐发尤多[9]。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包括前后文在内,这其实是一段有鲜明“立场”的文字。
如果不计最后一句“是岁,太元十年也”,可以认为整段文字由四个情节构成,即(1)苻坚为姚苌所执事、(2)姚苌向苻坚求传国玺遭拒事、(3)姚苌向苻坚求禅代遭拒事和(4)苻坚为姚苌所杀事。其中核心情节为(1)(4),构成了“苻坚之死”的基本叙事。(2)(3)则为插入其中的次要情节。虽然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的书写立场无疑倾向于苻坚一方。四个情节中都包含了渲染苻坚人格魅力的内容。如绝境中的“神色自若”,面对姚苌两度威逼的“天子之怒”,以及最后的“骂而求死”,都可以达到正面化苻坚形象的历史书写效果。对比之下,姚苌的形象就负面很多,带有些许妄自尊大的可笑感觉。情节(2)(3)作为次要情节,在整段叙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两个主要由苻坚发言构成的情节,其实并不影响“苻坚为姚苌所杀”这一基本叙事的成立;但加入之后,(1)(4)中比较含蓄的褒苻坚而贬姚苌的史笔倾向,就被相当明显的烘托出来了。
这就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一整段包括“五胡次序”故事在内的“苻坚之死”叙事,究竟是由何人书写的呢?故事的主角之一苻坚最终被杀,应该没有机会留下类似记录并传诸于世。而另一位主角姚苌虽然夺得了帝位,但他以及后秦史官绝然不会叙述这样一个美化苻坚却抹黑自己的故事。《晋书·苻坚载记》所见上述“苻坚之死”叙事,虽然包含了若干基础性史实,但整体上并非来自当事人或亲历者的记述。如此,在苻坚被姚苌缢杀之前,二人之间是否进行过以上包含“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在内的对话并被记录下来,其实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再聚焦于“五胡次序”故事即情节(2)。如前所述,学者主要关注故事中出现的“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并将其理解为当时的某种“图纬符命”。但这个故事本质上是围绕“姚苌向苻坚求传国玺遭拒”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姚苌所言与苻坚所答,都共同服务于这一主题,最终的指向是“玺已送晋,不可得也”。如所周知,传国玺在当时为正统之象征[10]。真伪姑且不论,将传国玺送至东晋的行为显然意味着对东晋正统性的认可[11]。换言之,这一故事在渲染苻坚威武不屈形象的同时,也达到了书写东晋正统性的效果。反过来自然也否定了前秦以及后秦的正统性,至少是将前秦的正统性置于东晋之下。苻坚的这一发言让人颇为费解。两年前正是这位前秦皇帝亲率大军南征,欲一举消灭东晋完成中华一统,随即遭遇了淝水之战的大败[12]。
要解决这一疑问,对以上“五胡次序”故事所在的“苻坚之死”叙事进行史源学上的考察或可提供线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唐修《晋书·苻坚载记》的此段文字,应来自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
(1)坚至五将山,姚苌遣将军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侍御十数人而已。神色自若,召宰人进食。俄而忠执坚以归新平县,幽之别室。(2)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应符历,可以为惠。”坚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乎?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3)苌遣右仆射尹伟说坚,求为尧舜禅代之事。坚曰:“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因问伟曰:“卿于朕朝作何官?”对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4)八月,缢坚于新平佛寺中,时年四十八。张夫人、中山诜等皆自杀。三军莫不哀恸。[13]
为方便比较,上述文字中加入了数字标示情节。除了个别文字的出入之外,《晋书·苻坚载记》显然因袭了《十六国春秋·前秦录》的记述。从四个情节的依次设置,到每个情节中的具体细节,都存在对应关系。情节(3)的内容《十六国春秋》较《晋书·载记》更为丰富,但仍以“姚苌向苻坚求禅代遭拒事”为主题,显示后者对前者有一定删改。而情节(2)姚苌向苻坚求传国玺遭拒事,双方文字几无差别,《晋书·载记》只是为苻坚发言加了一句“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以强化语气而已[14]。“五胡次序”故事在《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中已经以相当稳定的面貌出现了。
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定稿过程[15]。即使以成书最早的正始三年(506)而论,距离苻坚为姚苌所杀的太元十年(385)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言其著述因缘曰:
(崔)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16]
这里先言十六国政权“各有国书”,又言崔鸿“因其旧记”撰为《十六国春秋》。学者一般将这里的“国书”/“旧记”理解为十六国政权的“官修史”(包括“国史”和“前朝史”)。[17]同传载崔鸿上表,亦言:
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18]
对比看来,崔鸿利用的“诸国旧史”都是北魏政权内部已经有所流通的作品,不必求之于南朝;唯独东晋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19],“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以致于要乞求朝廷出手“敕缘边求采”。如此,作为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基础的其他“国书”/“旧记”/“诸国旧史”,似乎都与“江南撰录”无关了。
事实上情况是要复杂一些的。十六国政权确实多有史官之设,对历史书写的重视与汉晋政权并无本质区别[20]。但具体到各政权史书的成书状况另当别论。从《史通·古今正史》的记述来看,十六国诸“霸史”有若干种出于东晋南朝人士之手。“前秦史”即是如此: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21]
可见虽然前秦有“国史”修撰,且苻坚亦相当重视,但因为仓促而亡,距离成书应该尚远。“宋武帝入关”即义熙末东晋权臣刘裕灭姚氏后秦,史载当时“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22]。既然“并无所获”,说明后秦也未为前秦撰成王朝史。最后成其书者据《史通》所言为车频。车频事迹不详,与前秦史官车敬的关系亦不清楚,仅知为冯翊人。他资助曾“参撰国史”的前秦秘书郎赵整“著书不辍”的地点在商洛山。此地自前秦败亡后,先后为东晋和后秦所控制,至义熙末刘裕西征入关再次入于建康政权之手[23]。故赵整卒后,是由刘宋梁州刺史吉翰上表请车频“纂成其书”。吉翰出任梁州刺史在元嘉元年(424)[24],此时关中已为赫连夏所占据。可见车频撰成前秦史是在刘宋治下,且费时近廿年,颇具规模[25]。其书虽有前秦秘书郎赵整撰述的基础,但整体的政治立场无疑是在东晋刘宋一方。《史通》又记其后有裴景仁删车书为《秦纪》。此事《宋书》卷五四《沈昙庆传》所记更详:
大明元年,督徐兖二州及梁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本伧人,多悉戎荒事。昙庆使撰《秦记》十卷,叙苻氏僭伪本末,其书传于世。[26]
裴景仁“本伧人”,虽出自北方,却已入宋“助戍彭城”。裴书成于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后,政治立场亦当与建康政权一致[27]。其书“叙苻氏僭伪本末”,显然是一部完整的前秦史。则作为其基础的车书亦当如此。两书都应包含了苻坚之死的相关内容。
因此,并不能把崔鸿撰《十六国春秋》所依据的“国书”/“旧记”/“诸国旧史”,全部都理解为十六国政权的“官修史”。至少在前秦史的场合,崔鸿依据的主要作品来自“江南撰录”。前引《魏书》所载崔鸿上表言“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其中应包含了车频、裴景仁二书在内。这可能来自北魏内府秘阁[28],但也不能排除是崔鸿自藏。毕竟崔鸿家“二世仕江左”,入魏晚至北魏皇兴元年至三年(467-469)“慕容白曜之平三齐”[29],距离两部前秦史的先后成书已在十年以上。
中古史注、类书中有若干以前秦为书写对象的史书佚文留存。所称不一,有《前秦记》、裴景仁《前秦记》、《前秦书》、《秦记》、裴景仁《秦记》、《秦书》、车频《秦书》、裴景仁《秦书》等多种形式[30]。结合前文所述,主要当即出自车书与裴书的各种片段[31]。其中虽然没有留下与“五胡次序”故事相关的直接内容,但如下佚文的存在值得注意:
裴景仁《秦书》曰:“姚苌围符坚,遣仆射尹纬诣阙陈事。坚见纬貌魁梧,志气秀杰,腰带十围,瑰伟异常,惊而问曰:‘卿于朕世何为所作?’伟答曰:‘尚书令史。’坚笑曰:‘卿宰相才也。’”[32]
这一苻坚与尹纬的对话情节,亦见于前引《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苻坚之死”的叙述文字中,紧接于“五胡次序”故事之后。文字上有若干出入,但《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对裴景仁《秦书》此段文字的因袭痕迹还是相当明显的。实际上仔细对比现存《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佚文与车频、裴景仁二书佚文,基本也可以判定前者的史源就是后者。由此,其中出现“五胡次序”故事这样以苻坚将传国玺送至东晋为结局,借苻坚之口来书写东晋正统性的情节,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1]参见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二《地理类》,“五胡”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页;《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胡三省注,第3348页。近人意见可举陈寅恪为代表,参见陈寅恪:《五胡问题及其他》,收入氏著《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陈寅恪集》版,2001年,第453-454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83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3页;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第279-280页;川本芳昭:《五胡十六国·北朝時代における「正統」王朝について》,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第66-102页。
[2]参见孙仲汇:《五胡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第141-143页;雷家骥:《试论“五胡”及其立国形势与汉化思考——兼考“五胡”一名最初之指涉》,收入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北: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第83-174页。
[3]参见王树民:《“五胡”小议》,《文史》第22辑,1984年,第247-249页;吴洪琳:《“五胡”新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第90-95页。吴文并主张苻坚所谓“五胡次序”(详次节),特指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胡人的五德历运次序”或“五德历运中的胡人次序”。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亦认为“五胡”与“六夷”一样,是对活动于四、五世纪的少数民族的总称(第30页)。
[4]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第21-33页。
[5]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同氏:《〈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同氏:《〈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前秦、后秦国部分》。
[6]参见本书第七章《“西虏”与“东虏”:谢灵运〈劝伐河北书〉所见华北局势与历史认识》,第218-224页。
[7] “史料批判”与“历史书写”作为颇具新意的方法论,近年受到中国中古史学界瞩目。参见本书第5页脚注1。
[8]《晋书》,第2928-2929页。
[9]参见陈寅恪:《五胡问题及其他》,第453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83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条,第113页;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第279-280页;楼劲:《谶纬与北魏建国》,收入氏著《北魏开国史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5-76页;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第21-29页。
[10]参见田中一輝:《玉璽の行方:「正統性」の相克》,《立命館東洋史学》第38号,2015年,第47-75页。
[11]楼劲《谶纬与北魏建国》已指出:“传国玺作为天命重宝南归建康,……显示了五胡依次应谶合箓,至此实已运极道消,现在要揭开的是天命重归华夏的新时代。”第69页。
[12]参见田余庆:《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收入氏著《东晋门阀政治(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9-256页。
[13]《太平御览》,第591页。
[14]也有可能“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一句本为《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原文所有,只是为《太平御览》引用时所删略,《晋书·苻坚载记》反而保留了全貌。
[15]《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第1502-1505页。参见梶山智史:《崔鴻『十六国春秋』の成立について」》,《明大アジア史論集》第10号,2005年,第106-125页;同氏:《北朝における東清河崔氏-崔鴻『十六国春秋』編纂の背景に関する一考察》,《史林》第96卷第6号,2013年,第73-106页。
[16]《魏书》,第1502页。
[17]如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实”与“史相”之间》,第205-212页。
[18]《魏书》,第1504页。崔鸿此表并未正式上奏,是其后利用参修国史之机,违规加入(“妄载”)《世宗起居注》中的。参见梶山智史:《崔鴻『十六国春秋』の成立について」》,第109页;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实”与“史相”之间》,第205页。
[19]或即《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见《汉之书》(第963页)。参见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实”与“史相”之间》,第206-208页。
[20]参见朱希祖:《十六国旧史考》,收入朱渊清编:《朱希祖史学史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258-268页;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9-141页;王志刚:《家国、夷夏与天人:十六国北朝史学探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6页;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实”与“史相”之间》;聂溦萌:《十六国霸史与十六国时期的官修史运作》,《西北民族论丛》第13辑,2016年,第41-64页。
[21]《史通通释》卷十二,第359页。
[22]《隋书》卷四九《牛弘传》,第1299页。
[23]参见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上编,第333-334页。
[24]《宋书》卷六五《吉翰传》,第1717页。
[25]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推测《史通·古今正史》所言车频前秦史“三卷”为“三十卷”之讹(《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第5289页)。聂溦萌《十六国霸史与十六国时期的官修史运作》认为此书为纪传体(第55页)。
[26]《宋书》,第1539页。
[27]《隋书》卷三三《经籍志》所记裴景仁《秦记》尚有“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第963页),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此书的建康政权立场。
[28]《隋书》卷三三《经籍志》“霸史类”小叙言北魏道武帝完成华北统一后,“诸国记注,尽集秘阁”(第964页)。参见聂溦萌:《十六国霸史与十六国时期的官修史运作》,第61-62页。
[29]《魏书》卷六七《崔光传》,第1487-1488页。参见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92-122页;梶山智史:《北朝における東清河崔氏-崔鴻『十六国春秋』編纂の背景に関する一考察》,第76-77页。
[30]参见“五胡の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东京:燎原书店,2012年。
[31]《隋书》卷三三《经籍志》“霸史类”载何仲熙《秦书》,注云记苻健事,第993页。聂溦萌《十六国霸史与十六国时期的官修史运作》推测“何仲熙”或为“梁熙”之讹,其所撰《秦书》成于前秦之世,但并非国史(第56-57页)。中古史注、类书所引以“《秦书》”为称者,不能排除出自此书的可能性。
[32]《太平御览》卷三七七《人事部》,第1741页。
【本文初刊《文史》2020年第3辑,后收入《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为第八章,略有修订。此据作者书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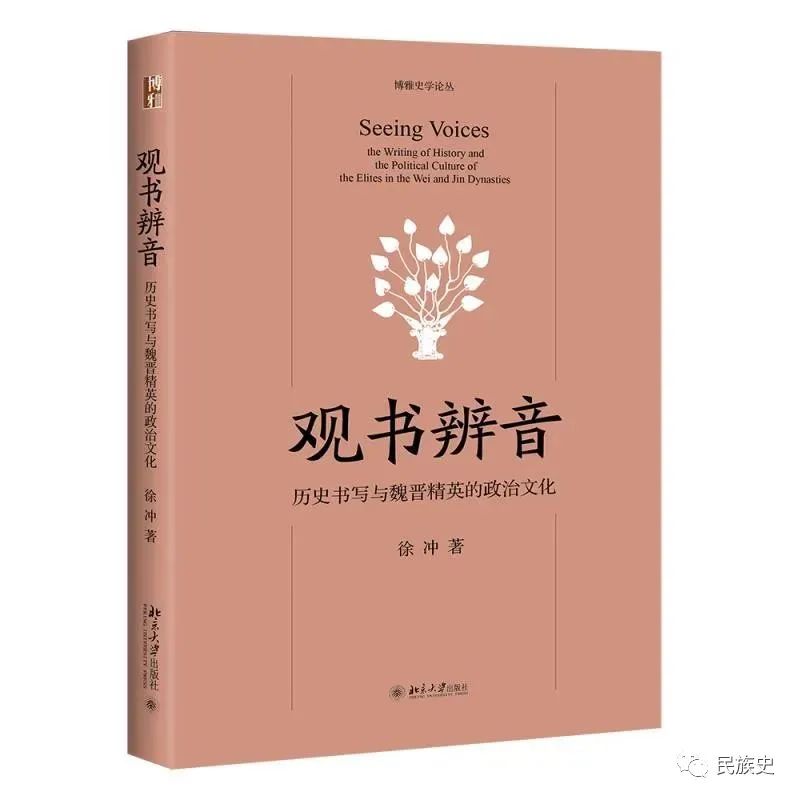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
内容简介
3—5世纪的魏晋精英,以多样化的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构筑了独具特质的政治文化。本书自这一主体的登场、全盛与流亡阶段,择取“献帝三书”、《续汉书·百官志》和《劝伐河北书》三组关键文本,分别从时代之史、制度之史和异族之史的维度,对上述历史现象进行了立体而深入的考察。各章多着力于文本面貌、结构与语境的复原,以新的问题意识唤起陈旧材料的生命力,追索历史书写背后的时代之音。斯音已渺,不复得闻,唯以史家之法,幻化于读者目前,是谓“观书辨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