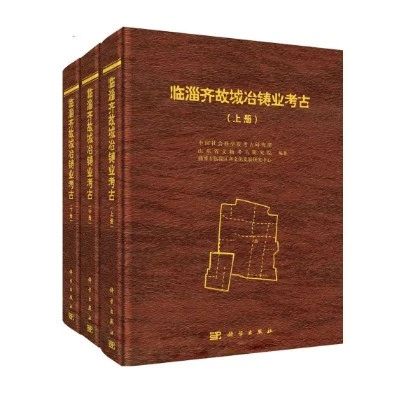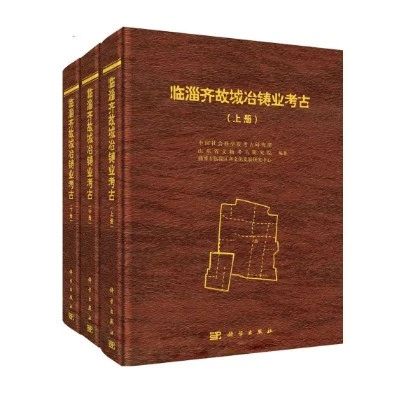专家观点
百工铸明镜 兢兢分秋毫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读后
摘要: 西周中期齐献公杀胡公,迁薄姑至临淄,至公元前221 年齐灭,齐国都城一直在临淄未改变。在长达600 余年的时间内,临淄始终是关东诸国中的大都会。在战国中晚期以后,甚至堪称为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战国策·齐策》说“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西汉至新莽时期,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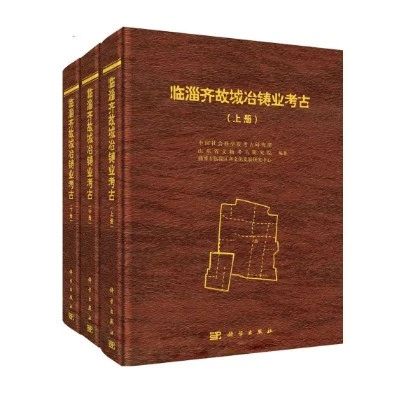
西周中期齐献公杀胡公,迁薄姑至临淄,至公元前221 年齐灭,齐国都城一直在临淄未改变。在长达600 余年的时间内,临淄始终是关东诸国中的大都会。在战国中晚期以后,甚至堪称为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战国策·齐策》说“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西汉至新莽时期,临淄地位始终十分重要。汉初郡国并行,临淄城作为齐郡郡治和齐王国的都城,城内先后设铁官、四市,至武帝时“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新莽时,临淄仍是著名的工商业大都。《汉书·食货志》中就说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临淄的辉煌,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地缘地位,更是基于城内高度发达的各类手工业。临淄城内各类手工业作坊密集,尤以冶铸作坊数量最多,金属手工业作坊在临淄城中的重要性似乎是其他列国城址所不能比拟的。临淄城以青铜冶铸、铁器生产和钱币、铜镜生产为代表的可能具有商品性金属冶铸生产活动,是两周尤其是东周时期列国都城中规模最大也最为发达的。从宏观布局看,各类冶铸作坊在大城和小城皆有。但由于临淄城大部分冶铸生产遗迹前后沿用,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往往沿用春秋时期的铸铜遗址。在未发掘前,对各作坊基本上都无法确定具体生产年代和产品。自1930 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根据文献记载线索开启了主动性的临淄田野考古工作。在80 多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对临淄城的手工业遗存,有大致的总体性了解,甚至也曾试掘过个别手工业作坊。但由于工作重点不同,直到本世纪初,临淄城内仍然几乎没有任何一处手工业遗址进行过系统发掘与综合分析。这不但影响了临淄城内手工业生产的年代判断和产品分类,对城址功能区划的分析也无法细化,更直接影响到对于东周至秦汉时期手工业生产能力、工艺技术的整体考量。这固然是临淄城田野工作不足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东周秦汉时期考古研究的视角,仍然集中在以夯土建筑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之上,未转变到利用类似平民居址、手工业生产资料等进行社会的描述与重建上来。进入21 世纪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模式开始进入转型阶段,以精细化发掘、多学科介入联动研究,发掘团队不仅限于某一个学术团体,是全国性考古工作的大趋势。在田野工作的变化背后,是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的研究转型的学术支持。这其中,对于手工业生产的关注,尤其令人瞩目。白云翔甚至将其提升凝练到“对于以人类古代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研究为己任的考古学来说,无论物质文化的研究还是精神文化的研究,无论是经济生活的研究还是社会生活的研究,都离不开社会生产的研究,都离不开手工业的研究”的高度。在这种学术思考逐渐取得共识的背景下,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联合组成项目组,以“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设立专项学术课题,以临淄城的冶铸生产为切入口进行个案研究。该项目在大范围调查的基础上,以阚家寨地点为中心,进行了四个年度的田野工作和五个年度的整理工作。这是临淄城考古工作目的明确,多学科合作最为充分、参与人员较多的一次工作。至2020 年《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科学出版社编校出版,系统公布了这一工作的过程与成果。从资料的刊布系统、翔实程度,报道形式看,该报告有显著的创新和特点,对中国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工作、资料刊布和研究均有重要价值。《报告》分为三编,上编为田野调查、勘探和发掘报告,分七章叙述临淄齐故城的冶铸遗址调查、阚家寨遗址的调查与勘探、阚家寨遗址B 区的发掘、东门村遗址的试掘以及齐故城新征集镜范与其他陶范的报告。中编是对所获遗存的科技分析和文物保护修复、模拟实验的26 篇报告。下编则以综合研究方式,将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分析结论进行拟合,讨论临淄齐故城金属冶铸手工业遗存的历史与社会问题。从这一结构设计来看,《报告》编著的目标并非局限于资料的刊布,而是将目标设定为田野考古、科技分析和综合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性报告。上编田野发掘报告,编写团队采用的体例是一种介于“举例体”和“全面公布的分述体”之间的方式。《报告》对绝大多数遗迹都进行了介绍,但遗迹与遗物分述,并未将遗物回归出土单位,按单位叙述埋藏背景与组合,而是采用分类叙述的方式。但需要强调的是,相较于大多数田野考古报告的举例方式,《报告》近乎完整地刊布了调查与发掘资料。对各发掘地点的大部分遗迹,《报告》基本上逐一介绍,这在东周时期手工业遗存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尚属首次。除了发掘所获的遗迹与遗物外,《报告》还将调查期间的采集遗物较全面地公布。更值得称道的是,《报告》对调查期间与勘探期间的绝大多数钻探资料一并给予了全面公布,精细到每一个探孔的报告方式,是中国考古学田野报告编写历史上的一次创举。这些内容,让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发掘片区以外地点的堆积状况,对不同区域遗存的时代和功能有初步判断的线索。这些信息,为复原齐故城内的遗存分布情况和城市功能格局大有裨益。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于不同类型发掘遗物的刊布范围、程度与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对非常见类型的遗存是否应该全面公布,学术界一直在探讨。中国考古学家们曾多次发掘手工业遗存,但既往的资料刊布过程中,由于经费、发掘周期的长短、发掘程度的精细与否,因历史局限,而失之过简。由于手工业生产活动会因产品和工艺的差别而遗留相应较特别的遗存,如果不相对全面地刊布资料,很可能会因发掘者知识体系的局限,遗漏当时难以准确判断功能的遗迹和难以定名的器物,甚至会因误认而对部分遗存未进行特别描述。宏观来看,冶铸手工业生产是先秦时期分工程度、工艺流程最为复杂的门类,在进入战国时期后又因为产品的商业化生产,而使其专业化程度和产品种类达到了中国手工业生产的高峰。以临淄城的冶铸产品生产为个案,可见同时期冶铸生产之一斑。因此,《报告》系统刊布全部资料,是有必要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所缺乏的,堪称中国首部古代城市手工业多学科综合研究报告,同时也足堪为铸造生产田野考古工作研究性报告的范例。作为考古报告,在遗存分述之外,对遗存的整体情况和多方面的特征作一概述,使得读者不必自己梳理统计,即可了解发掘所获遗存之概貌,是有必要的。《报告》在这一方面有较细致的工作。由于发掘和整理经典重读- 67 -者直接接触第一手资料,对遗存的认识较之读者往往更为直观全面,从亲历者的角度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往往是体现报告整理者“研究性”的表现。《报告》在整理过程中,对土质土色的描述,对遗物的类型学研究是有统一考虑的,描述的方式和遗物的分类秉持了统一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报告》的资料刊布能够做到统计数量的精准。这一方式,在尽量多地公布遗迹、遗物的标本的配合下,大大方便了读者。《报告》的图像资料的绘制也值得称道。《报告》线图绘制精细,对陶器内壁的麻点、手制印痕都进行了细致表达,甚至对残鬲足也有较准确和细致的绘图,从中可以知道发掘或调查区域曾经有过的不同时代的遗存。这非常类似于通过晚期单位中的早期陶片,知道该区域的时代沿革。对冶铸遗存常见的磨石、鼓风管、各类陶范、锈蚀严重的铁器等遗物,《报告》的线图绘制皆根据其特点和质感的差异,选用不同的线条或点表现质感。对瓦件的图像表现形式选择上,《报告》采用拓片直观表现器表绳纹和内壁衬垫痕迹,这种考量足见编写者已经注意到瓦件差异所蕴含的学术问题,因此从表现形式用最直观的方式予以精确表现。上述图像的种种细节,足见编者用心。问题导向下的精细发掘和报告撰写是突破报告编写机械化、套路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将考古工作推向深入的重要途径。从这个角度讲,发掘报告的“研究性”是发掘整理者问题意识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料刊布的角度和方式。《报告》中编26 篇研究报告大体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针对田野调查与发掘的技术性支持与发掘所获非冶铸遗存的分析,这些研究检测报告包括物探、碳十四测年、发掘所获人骨检测鉴定、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动植物分析检测、发掘所获的蛋壳蛋白质组学分析、木炭的分析、土壤及残留物检测、出土纺织品分析等。另一部分则是直接针对阚家寨等地点的冶铸遗存所进行的相关遗存的检测,包括铸镜作坊砂样、镜范及相关土样的成分与岩相分析、镜范的热膨胀与烧成温度、镜范植硅体的分析、临淄出土铜镜和其他铜器的检测分析、石范的微痕分析、齐故城冶铁遗物的分析检测,也包括镜范制作工艺的模拟实验报告、三维重建、出土铜釜的修复报告等。《报告》的这些综合研究,虽然与既往对铜镜和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铸造遗存的综合研究以及分析检测结果并无太特异之处。但必须强调,这些多学科分析是在临淄齐故城的战国晚期以降,传统被认为的历史时期考古遗址展开的。近20 年来,多学科综合分析研究共用于同一遗址,从多个角度复原遗址的社会发展水平和遗址使用者生活的方方面面情况,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但这些综合研究大部分是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展开,少量使用于青铜时代早期遗址,极少有对历史时期遗址的多学科分析研究。这其中固然有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大多集中在城址、宫殿、庙宇等大型建筑居址和墓地,极少有与一般人群日常生活相关或生产的遗存,因此尝试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效果往往不佳,更无法全面分析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部分历史时期遗址的发掘者关注重点,也多不在基层社会的面貌复原之上。阚家寨地点铸造作坊的发掘,在相关铸造遗存的专项分析之外,却试图尝试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讨论铸造生产者的日常生活和劳作生产细节。无疑是将单纯的生产技术分析,扩展到与之相关的人,探索了历史时期田野考古发掘从物到人的研究道路。报告的部分科技分析,类似对浮选植物遗存、镜范的材料与岩相,出土与采集铜镜的成分分析等,都采用不同单位与研究者分头进行。有的样品甚至采用“一件样品锯割分为多块由不同学术团队进行检测分析研究”的方式,比较不同学术团队的研究结果,进而获得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颇有随机分配样品进行“盲测”互校考量的研究趋向。比如,关于镜范样品的分析检测和研究,由于有的学者对以往的检测结果,如羼合料等材质、烧成温度、使用状况等多有不同看法,而不同学术团队的视角和技术手段有所不同,同一样品在不同科技分析团队的检测下,很可能得出未曾预想的分析结果。虽然本次科技分析的很多研究成果基本一致,但由不同的团队对同一类别的遗存进行研究,以便不同团队研究结果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补充,是极富胆略的学术实践。《报告》下编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分别对齐故城阚家寨地点的年代和性质、临淄齐故城的金属铸造业整体情况、钱币铸造业、铜镜铸造技术、铁器工业进行了综合分析。以认识总结的形式,将阚家寨地点的个案分析延伸到临淄冶铸业。从篇章布局和研究角度看,无疑是以点带面的方式,也起到了全书的收束作用。虽然发掘面积不大,未能完整地揭露阚家寨地点战国时期高等级建筑、西汉时期铸镜作坊、冶铁作坊或新莽时期的铸钱作坊,从聚落的布局或作坊的功能区空间分布研究,无疑是有遗憾的。但从项目的设定而言,搞清了阚家寨发掘地点的聚落性质和历时性变化,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项目的预期设定。而《报告》下编的综合研究,甚至已经超出了阚家寨本次发掘。无论是临淄城钱币铸造业、铸镜业和铁器工业的生产,研究者的视角多是从阚家寨的发掘出发,全面整合了临淄城的相关资料,将发掘所获的陶范与既往考古所见的冶铸产品相对比,视角已经触及到临淄金属冶铸业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历时性变迁的问题。可以说,这样有自身发掘材料反视既往发掘资料,并以科技考古多学科研究的视角更大程度获取信息的综合研究方式,不但起到了串联考古发掘资料的作用,也在更大的学术视野下,启发后续的工作,提升资料的效力。《报告》所反映出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团队组合和相关研究的展现形式,无疑与《二里头(1999~2006)》和《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 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十分接近。三部报告皆以田野工作为中心,以遗存的系统整理与相对全面的公布为目标,集中不同学科的分析优势,解决所处理对象的社会问题。从《报告》的最终展现来看,项目的策划者和工作的具体实施者、多学科研究团队的合作者,无疑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推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显示了运用多种科技手段提取遗存信息,在历史时期遗址中具有巨大的学术前景。
作为冶铸遗存,《报告》无疑需要探索新的编写、公布模式和观察视角,若与既往已经出版的同类田野发掘资料相比,《报告》尽可能全面公布资料的取向和多学科团队分析方式,无疑已经全面超过了既往的同类著作。综上,因为田野工作细致深入,主持者又不吝经费和精力,系统地刊布了这样一大批性质确定、年代关键的铸镜、铸钱和铸铁遗存资料,提供了大量翔实珍贵的信息,在多个方面增进了对战国秦汉时期大规模消费型日用铜器的生产及背后生产者的全方位认识。随着后续研究的深入,这批资料无疑还将持续增进对相关问题乃至齐临淄社会的认识。任何著述都不会尽善尽美,《报告》资料公布全面、翔实,意义重大,但也有一些需要指出的问题。首先,《报告》从第三章至第五章集中刊布阚家寨遗址B 区的发掘资料,但不同地点的差别是因工作的年度和团队的分工所决定的。所出的遗物亦采取了统一的标准进行类型学分析和描述。不同的三个地点间最大直线距离不超过150 米。由于发掘区临近、所获遗物性质、年代相近,因此对于发掘遗存的分期或年代学研究,本可以统一进行,而不用在每一章所讨论的区域单独进行。如果能有一章总结三处地点的共性问题,不但会使《报告》的篇章设置更具逻辑性,也能减少内容的重复或不协调。但《报告》目前的处理方式使性质相同的几章内容在设置上并不太统一。《报告》第三章第五节的小结中设置了“地层堆积的年代”、“发掘区中部主要遗迹的性质和年代”、“中西部主要遗迹的性质和年代”等部分,还专设一部分讨论“地层及遗迹所反映的历史发展情况”。但在第四章B 区II地点的小结设置的内容却分别为:“年代与分期”、“战国晚期铁工场遗存及铸铜遗存”、“秦至西汉早期的铸镜作坊及其他铸铜遗存”。第五章B 区III 地点的章节小结中又改变为“分期与年代”、“初步认识”两部分。从全书的整体性角度看,这样的讨论方式显然不太统一,分析深入程度也有差别,更不便于读者获得阚家寨地点的整体印象,似乎如能设置单独章节,全面总结阚家寨发掘地点的相关内容效果会更好。其次,《报告》的多学科分析十分全面,但对于分析检测如何更加妥善、有效,以及样品如何分配,有值得推敲之处。虽然不同科技分析团队的“盲测”互校会检验猜想的正确与否,也可以不同的研究取向探查分析的诸种可能。但每一种抉择必如硬币之两面。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时所划分的分区,只是工作区域,并非反映当时阚家寨铸镜作坊的不同主观功能区,成分分析亦无法完全替代对工艺流程的细节描述。因此,进行多学科分析时,如能整合样品,统一分析,进而将多学科分析结果进行定量研究,将更有利于对同一问题或同一类材料的深入探讨。对于不同分区同类样品的分头检测,会让检测的结论进一步“碎片化”,也会增加统计分析的难度。第三,从理论上讲,多学科分析是为某一学术目标的而共同服务的。从这个角度讲,多学科的分析选择的科目实际并无定式。除了常规的年代学、动植物分析和材料学分析之外,应该针对不同性质的遗迹设计有针对性的分析检测,并根据检测需要组建研究团队。《报告》的多学科分析检测,基本上涵盖了常规检测项目和大多数冶铸遗存常用的分析检测方法。但对于浮选时的重浮物,却未设计相应的多学科研究。对冶铸过程中形成的微小“渣”、“粒”的分析,在我国冶金考古领域研究十分薄弱,样品的定量统计研究更少。虽然重浮物分析难度较大,也更加耗时,但如果《报告》能对这一类遗物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甚至选取一部分单位的浮选样品进行分析,都将大大推动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问题,如有的遗迹平剖面图为平面与剖面,有的却是剖视,并不十分统一。个别遗迹图,如图5-12 存在剖点标识不明,平面未表现的遗迹在剖面中出现等问题。第三章将陶器、瓦当以外的所有出土遗物共同在一张统计表中统计列表,但第四、第五章却分开列表统计铁器、铜器和骨、角、玉器,前后的表现方式不太统一。同时,对于陶范的观察和线图表现还有一些疏漏,忽略了外范侧面的观察,对双合范和空腔器物外范的合范定位线或有无捆扎槽都未有详细观察与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说,临淄阚家寨地点铸造作坊的发掘与多学科研究是探索三代乃至秦汉时期手工业生产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国都城手工业考古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实践,其工作理念、研究细节,必将为后续同类工作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若干报告编写的疏失,在孜孜十年工作探求,斐然成果之前,已属末节。上文对田野工作和资料刊布的苛求,也是对解决重要学术问题的期盼。期待在后续的资料刊布和新的考古工作中继续关注上述问题,深入推进手工业考古的相关研究,进而更加细致地推进古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描述性认识工作。(作者: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