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伏俊琏等著《敦煌文学写本研究》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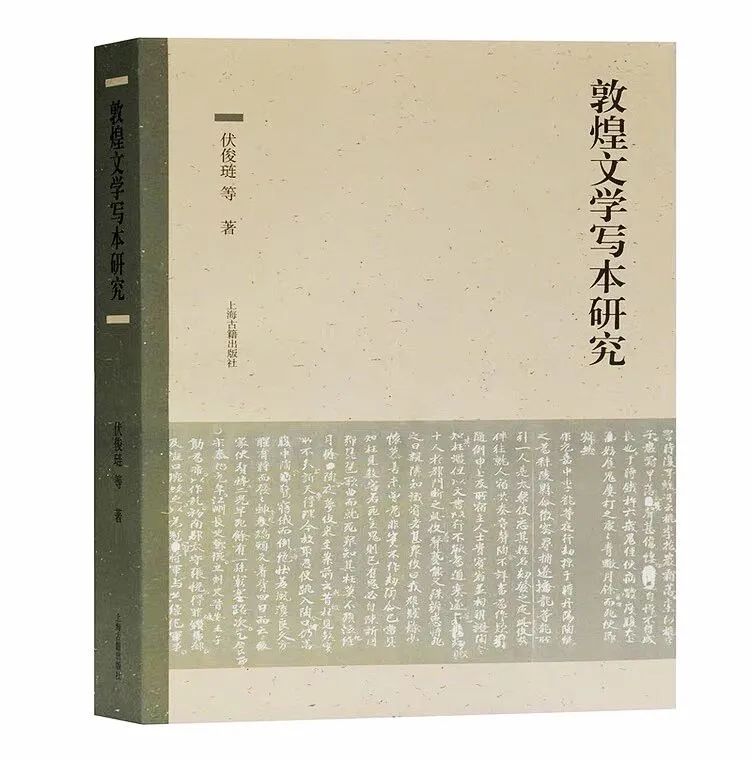

书名:敦煌文学写本研究
作者: 伏俊琏 等 著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的文字载体可分为写本、刻本和电子文本等多种形式。从时间上讲,殷商到唐宋之际,主要是写本时代。这一时期,早期有简牍(也有少数的帛),后来主要是纸本。《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① 说明殷商时期已经使用简册。在简牍之前或同时,有甲骨文和金文,稍后还有石刻。但甲骨文是写给神灵看的,内容以占卜为主,刻成之后即藏于石室金匮,或深埋地下。金文和石刻的作用是纪念碑性,为了先辈的功业传之不朽②。铸造在礼器上的金文,在祭祀仪式上,通过叩击钟鼎的声音和其中食物热气腾腾的馨香传递给神灵。它们都不是作为主要的社会交流媒介,不能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定的文字载体。简牍时代从商朝开始,直到东晋,才逐渐被纸本所替代。当然,这期间有简纸并用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而纸写本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一直到北宋初期,才逐渐进入刻本时期。因此,我国写本时代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纸写本时代也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③。
写本时期的大量实物重见天日,是近百余年的事。十九世纪末以来,大量的写本,从战国简、秦简、西汉简、东汉简,直到三国简、两晋简,都有出土。其中战国楚简、西汉简中有数量不少的文学作品。帛书虽然出土较少,但像马王堆西汉帛书,数量多,有关乎学术史、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纸写本文献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吐鲁番出土文献、日本等境外藏中国书籍及档案文献。而在宋代刻本大量出现之后,手抄纸本亦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写本作为辅助载体没有中断过,甚至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大型的集成性典籍也是写本形式,但这已经不是写本时代的“写本”了④。
简帛写本和敦煌吐鲁番写本发现百余年来,其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形成了“简帛学”和“敦煌学”这样的国际“显学”。但是,过去整理研究简帛写本和敦煌吐鲁番写本,有两个特点,从“写本学”角度看,也是两个不足:一是对写本中的文献进行分类,一般是按内容或文体进行辑录和校注,例如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主要移录其中的诗赋、曲子词、变文等,各归其类,而对于写本上的其他内容和信息,则有所忽略。如写本正背面抄写的其他内容、题记、杂写、涂画,还有写本的性质用途、装帧形式,包括纸质和书写工具等情况关注不够,也就是说对写本的整体观察有所欠缺。这种以作品为纲的整理方式势必要割裂写本,而且一个完整写本所保留的作品的性质及运用的情形等文化信息都将有所忽略。二是对同一作品的不同写本,主要是校其异同,定其是非,对其文本性质和文化情境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即没有考虑造成如此差异的深层原因。
传统文献学是建立在刻本书籍基础上的,且以官方经典和文人作品为主。按照这种文献学理论,面对一部作品,首先是确定一个稳固的“定本”,以及在“定本”基础上对“本义”或“正义”的探索,而同一篇作品不同刻本之间的差异,往往用讹误衍脱概括之。从《文选》以来,学者习惯于按文体分类文学作品,这也形成一种整理文学作品的传统。所以,当二十世纪大量的写本出土以后,学者还是习惯用传统文献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和研究。即按照既定的文体观念和标准,从写本中“别裁”出这一体裁的文章,作为完全独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世界,进行分析和研究,至于这些文章在写本中所处的位置,与前后文章的关系,则不再涉及。
写本与刻本是有较大差别的。从内容和格式上讲,刻本是定型的,而写本则是个体的,流动的,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不仅写自己习惯的异体字、错别字,还往往根据自己的知识、信仰和理解,增加、删削或者更改某些内容。这样一来,同样一部书,不同的写本就有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形制、内容、字体、格式等多个方面。每个写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或多或少地带着它所在的时代和写本制作者个人的烙印。而下层文人写本和民间文学写本,由于制作者对文学、文体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由于抄写的实用目的性,其个体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写本的特点归根到底是由其用途的个体性和制作的个体性决定的。李零先生曾经对写本和刻本的差别作过形象的说明:战国秦汉的古书好像气体,隋唐古书好像液体,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⑤。简帛古书离我们久远,出土时散乱不完整,很难恢复到当时它的最基本单位,我们对其很难把握,所以像气体。隋唐时期的纸写本,比较完整者相对要多,对一个写本作总体研究或对相关的几个写本作比较研究就容易把握,然而它又相对灵活随意,同一篇文章,不同写本呈现的是不同的样子,所以像液体。至于刻本,则是千人一面,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像固体。
文学作品的结集,是文学传播的最重要的方式。写本时代的一个写本,相当于后世的一部文集,一个文学写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集,其中包含着制作者丰富的情感追求和文学观念。所谓结集,就是把数篇作品编辑到一起。一般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结集是从刘向、刘歆校理群书开始的,根据《七略》删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其《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等,就是“别集”之滥觞。事实上,在刘向之前,司马迁已经有明显的“别集”意识了。司马迁是一位文学情结很浓的历史学家,他在人物传记中大量引录传主的作品,有些列传,其体制无异于该传主作品集的读后感。《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读传主某某篇章,观其行事,次为传,这是《史记》诸多传记的叙述方式。《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情绪激动,情感跌宕,是读其书有感而发者。《司马相如列传》收录了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书》《哀二世赋 》《大人赋》《封禅书》等八篇作品,字数占全篇列传的百分之八十,几乎就是司马相如的选集再加解题说明。后来的史学家,学习司马迁的方式,对有可观文章传世的作者,为其立记,总是要搜寻读其文集,甚至编为别集。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在叙述了诸葛亮生平重大事迹后,说:“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并详细罗列著作目录和字数。这是最为典型的史家读其书叙其事而“别为一集”者。总集始于《楚辞》,汤炳正先生经过深入研究,认为《楚辞》经过了宋玉、淮南小山、刘向、王逸四人的编集⑥。当然,如果我们把《诗经》也当作文学,那么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总集了。
简牍写本时代,文学作品集的部头一般都不大,以“篇”为“一个写本”或“一集”的单位,《汉书·艺文志》中以“篇”为单位者占四分之三。编联完整的“一件简”称作“篇”或“编”,把它卷起来保存,称为“卷”。《诗经》近四万字,如果按照出土的秦汉简牍的一般情况,则抄一部《诗经》要用1000多枚简⑦,显然是要分开编成很多卷的。十五《国风》、二《雅》、三《颂》在当时是分开结集编纂的。而实际流传的时候可能还要小。比如,今传《诗经》中有“组诗”的痕迹,郭晋稀先生认为《陈风》中的《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等篇皆写周室衰微,姬姓没落,当时娶妻,都愿附婚大族,即齐姜之子,故当为一组诗。《郑风》中《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溱洧》等篇、《萚兮》《丰》等篇、《东门之墠》《出其东门》等篇皆为组诗⑧。这些组诗,当时是作为“一个写本”或“一集”流传的。《小雅》中的《常棣》《伐木》《天保》,《大雅》中的《假乐》《民劳》《荡》《江汉》《常武》,都和召伯虎有关系,是他编辑的宣王中兴时期的一组诗,也应当以“一个写本”或“一集”的形式流传⑨。余嘉锡《古书通例》云:“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⑩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两篇,极为佩服,急切想知道作者为谁。说明韩非子的这两篇是作为一组(一集)传到秦国的。汉赋宏篇钜制,一篇就足以为一集。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说明《子虚赋》是单篇作为一集(一个写本)流传的。
到了纸写本代替简牍而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之后,作家的创作潜力得到极大发挥,中国文学的自觉程度极大提高。西晋傅咸《纸赋》写道:“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⑪纸的卷舒随意、伸屈自如、幽显因时,与魏晋文人追求个性解放、自然疏放的思想相契合。纸媒介使文人有更广阔的背景在作品中反思生命的有限性与情感的价值,在伸展自如的物体上表现自己对美的追求,绚丽多姿却又自然生动的六朝书法和文人花笺只有在纸的普及之后才为学人所追求。查屏球说:“作者突破了‘慎重落笔’的心理障碍,写作思维更加自然流畅,作者可以用最快的手段捕捉到瞬间的心理反应与创作冲动,其内在之‘意’向外在之‘文’的转换变得更加直接与方便,这除了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之外,更扩大了创作思维的自由度,释放了作者的内在情思。”⑫因此,纸写本比简牍写本更易于表现制作者的情感,给文学作品的结集带来了新的变化。《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集部著作,大多的是南朝编纂而成的,说明纸写本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结集。
敦煌文学写本是纸写本时代
珍贵的民间文学作品集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写本抄写时间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1世纪,跨越六百余年,是典型的纸写本时代的产物。要讨论敦煌文学写本,首先得明确敦煌文学。对于敦煌文学,各家有不同说法。我们认为敦煌文学包括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文学作品、文学活动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敦煌文学作品除了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说唱文学,例如变文、讲经文、曲子词、俗赋、通俗诗外,还有大量的民俗应用文、宗教应用文,尤其是佛事应用文等。敦煌写本中驳杂多样的文体形态,有很多我们是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传统文体学著作中找不到的。敦煌文学活动主要夹杂在民俗活动和宗教活动中,比如婚礼、丧礼、各种祭祀礼仪。佛事活动在当时的敦煌更是种类繁多,这些活动中都有与文学相关的仪式,蕴含着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敦煌文学活动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文学写本的制作,包括作品的汇集和抄录。和我们见到的简牍文学写本主要是官方或文人的正式抄本不同,敦煌文学写本中有下层文人自抄自用的,有民间仪式的主持者收集备用的,还有一些学郎的抄本。晚唐五代敦煌寺学中的学郎年龄大的不少,他们往往在农闲时去寺学读书,学一些实用的知识。这些文学写本抄录比较随意,所抄作品内容多样,文体驳杂。
我们可以通过写本的物质形态来研究当时的文学编集活动,比如通过字体判断是否为一人所抄还是多人抄写,是先抄后粘还是先粘后抄。通过其格式、抄写整齐与否和校勘情况判断是杂抄本,还是作为书籍保存流传的正式写本。通过写本正面和背面内容的对比,判断其抄写时间和抄写的文化情境。而写本的内容则是研究写本制作者的思想、情感、信仰、知识的主要依据。比如,通过研究大量的文学写本,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敦煌民众看来,文学主要不是作为案头读本,而是社会生活仪式的一部分,它附着在当时的民俗仪式、宗教仪式中生成、嬗变、传播着。
《文心雕龙·附会》:“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骾,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刘勰以人体喻文体,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必须具备精神世界、骨骾筋腱、肌肉皮肤、语言声气等要素。一篇完备的文章,也必须具备情感意志、题材事义、词语文采、节奏韵律等要素。而一个文学写本也是一个“生命体”。写本中复杂的情志内涵、所描写叙述的题材、语言词汇、节奏韵律等,构成了写本的神明、骨骾、肌肤、声气,这样完整的“体”,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文化生态。这个文化生态由不同的个体组成,每个个体之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维系者就是这个写本的制作者或抄写者。他通过写本的制作和抄录来透露他的个人身份、情趣爱好、思想情感、知识信仰,通过写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呈现他的文学思想,吐露他的心声,展示其生命的运动。所以,一个写本中完整的诗文之外,那些随意的杂写、涂鸦,也是抄手彼时彼地心理活动的真实流露。对文学写本的研究,就是对一个个文学个体的研究,对已经逝去的文学生命个体的感悟。摩挲千年前的写本,那些字里行间,有古人的脉搏和心跳,可以还原一幕幕历史场景。这些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宝贵信息,在刻本中是很难保留的。
在下我们通过几个写本的结集分析进行说明:
P.2555是最有代表性的敦煌文学写本。俄藏敦煌文献公布后,学者发现它与Дx.3871写本字体相近,内容相接,可以缀合⑬。缀合后的写本内容丰富,共抄录了诗212首,文4篇,是一部唐人编集的唐代文学选集,其中两篇文是编辑过程的阶段性标志。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正面第一部分:唐代边塞诗杂抄13首。有歌行体的长诗,如佚名《落花篇》、安雅(开元天宝时期人)《王昭君》、张渭(?-约778)《河上见老翁代北之作》等 ;有律诗,如佚名《客龄然过潼关》、岑参(715-770)《寄宇文判官》;也有绝句,如佚名《海边黛色在似有》等。这一部分,体裁比较多样,内容或写边塞风光,或写海边景色,或写离别,或写战争造成的家破人亡。
正面第二部分为七言绝句47首,内容以抒发别离之情为主。其中10首可以考定作者或诗题:有冷朝光(约开元年间在世)之《越溪怨》,高适(约704-765)的《塞上听吹笛》和《别董令望》,薛维翰(开元中进士及第)《春女怨》,王昌龄(?—约756)《长信秋词》,岑参(715-770)《逢入京使》等。显然是编者有意汇集成的七绝形式的离别诗。
写本的编者在此处告一段落,作为第一次编辑的部分,有一诗一文作为过渡标志:佚名的歌行体《明堂诗一首》和孔璋《代李邕死表》文。《明堂诗》不见于传世文献,诗的前八句写明堂的外形,次四句写明堂对四夷的震慑作用:“东夷百济闻倾化,西戎蕃国率皆然。南蛮稽颡俱言献,北狄胡王悉贡毡。”后四句祝愿李唐江山长久。明堂是一个国家政权和威严的象征。早在《诗经·绵》中,歌颂古公亶父迁岐定都,其中一章写道:“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修筑高大的城门,修筑庄严正大的宫门,然后修建祭祀土神的大社,戎狄丑虏吓得仓皇逃走了。建立神社怎么能使戎狄逃跑呢?因为社神是主管杀戳罪人的。战争胜利后举行献俘典礼、杀死俘虏的献祭典礼也要在神社举行。西周神社的功能由后世的“明堂”所继承。由此我们可以想到编者抄录这首《明堂诗》的深刻用意:此诗集编辑的时候,归义军政权正面临着回鹘的军事入侵,作者用这首诗为自己、为归义军政权壮胆。孔璋《代李邕死表》作于开元十四年(726)。《旧唐书》卷一九〇《李邕传》记载,开元十三年十二月,“玄宗车驾东封回,邕于汴州谒见,累献词赋,甚称上旨。由是颇自矜炫,自云当居相位。张说为中书令,甚恶之。俄而陈州赃污事发,下狱鞫讯,罪当死,许州人孔璋上书救邕曰(略)。”布衣孔璋愿替李邕就死,就是因为李邕“学成师范,文堪经国,刚毅忠烈”,有国士之用。李邕为人耿介磊落,不畏权贵,屡遭贬谪,晚年遭人暗算。编者在此表达的深意,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正面第三部分为咏物诗16首,题目完整或可考知者有球杖、笔、葵、箜篌、六甲、石人、绢、烛、钱等,这组诗多用双关手法,形同猜谜,诗中描述物品的性质、形态、功用等,题目为谜底。诗的语言通俗,格式比较呆板,第二首《笔》的末句为“平明点着墨离军”,用双关语,墨离在敦煌西,则诗为河西军中文人所写。它和初唐《李峤杂咏注》(见于P.3738、S.555等)相似,是当时普及知识的需求下产生的。这一部分作品应是产生在敦煌(或河西地区)的诗篇。由这组作品可以看出编者受当时文风的影响,以及他的生活爱好和情趣。
正面第四部分为陷蕃诗79首,前60首为一组陷蕃诗(学术界过去称陷蕃诗59首,按其中《首秋闻雁并怀敦煌知己》为两首不同韵脚的绝句)。后19首为刘商的《胡笳十八拍》再加上毛押牙的《胡笳十九拍》。60首陷蕃诗写作者从敦煌出发,向东南经过墨离海、青海、赤岭、白水,直到临蕃的经过。其中前24首是途中纪行诗,后36首是囚禁于临蕃时所作。这组诗学术界关注最多,讨论也最热烈。我们认为,这60首陷蕃诗的作者是“落蕃人毛押牙”,他也是该写本的编集者,他把记叙自己陷蕃遭遇的诗作汇集一起,并把刘商(?—807)的《胡笳十八拍》(作于大历初,即公元766-769年刘商官庐州合肥令时)抄录其后,悲愤之情难于自已,于是又续作了第十九拍。人生的不幸遭遇令他唏嘘不已,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举起了酒杯,人生短暂,何必悲伤不能自拔呢?他想起了曾读过的刘长卿(约726—约786)的《高兴歌》,于是又一口气抄录了刘长卿《高兴歌酒赋》。“醉眠更有何所忧,衣冠身外复何求。但得清酒消日月,莫愁红粉老春秋。”抄录《高兴歌》,正是他此时此刻的心理写照,
正面第五部分,是闺怨诗、宫怨诗19首汇抄。其中有郑遂初(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即公元696年登进士第)的《画屏怨》,上官昭容(664-710)的《彩书怨》,颜舒(天宝时进士及第)的《珠帘怨》,李元纮(?-733)的《锦词怨》,王諲(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737年登进士第)的《闺情怨》,孟浩然(689-740)的《闺情》,刘希夷(约651-约680)的《白头老翁》。佚名氏《思佳人率然成咏七首》和《奉答二首》更是一组凄苦相思之作,前七首写登楼望故乡而思念佳人,泪沾情书,不知昼夜秋冬,形容枯槁,精神恍惚,乾坤无色,是用男性的口吻。后二首以女子口吻奉答,写自己不贪图金钱,只是一往情深,因相思而日渐消瘦,希望爱人不要因此失望。这组诗再次表明,作品的汇编者是一位滞留敦煌的文人,与故乡道路阻隔,与家人天各一方。因思念家乡、思念妻子,他自然想到家乡的山水田园,于是又情不自禁地抄录了描写乡村风光的《早夏听谷谷叫声,此鸟鸣则岁稔》二首和《过田家二首》。谷谷鸟在青山绿水间鸣叫,预示着秋天的丰收,乡间美丽恬静的情景则让滞留边塞的作者暂时忘记了忧愁,暂时沉浸在诗意的愉快之中。
然而,诗人在田园的沉思中蓦然抬起头来,却看到了先前抄录的《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此文把吐蕃入侵河西的硝烟战火又一次描摹展示在人们面前。作者窦昊,生平不详。据戴密微考订,该文作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⑭,正值吐蕃大军逐渐占领了整个陇右,并逼近凉州、肃州的危急关头。文章通过对唐蕃历史关系的回顾,警告吐蕃统治者,希望“罢甲兵于两疆,种柰桃于原野,止汉家之怨愤,通舅甥之义国”。骈散并用,写得很有气势。本诗集的编辑,以这篇散文作结,也是意味深长的。本卷诗集的第二次编辑至告一段落。
写本背面与正面为同一人所抄。背面的内容可以分这样几类:第一类杂抄18首诗。考虑到这组诗中作于成都的较多,而当时西川(今成都)和敦煌的交流也较为频繁,所以我们认为这组诗是从西川流传到河西的。其中《江行遇梅花之作》,原写本署名岑参,为一首岑参的佚诗。诗写作者独行在外的思乡之情,为大历初(766)岑参在成都所作⑮。《冀国夫人歌词七首》,闻一多《岑参年谱》判为岑参所作,并考定诗中的冀国夫人,为裴冕夫人。廖立《敦煌残卷岑诗辨》、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刘开扬《岑参诗编年笺注》等都认为,冀国夫人是西川节度使崔宁妾任氏,而非裴冕妻⑯。那么这组诗也作于成都。《闺情》三首、《宫怨》二首,都是编者偏爱的题材。
背面第二类是陷蕃诗12首。在陷蕃诗之前抄有一首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王重民认为马云奇就是陷蕃人,是以下12首陷蕃诗的作者⑰。我们认为,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与下文抄录的12首陷蕃诗无涉,而写本汇集者把它抄到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写本汇集者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我们看该写本字体秀美优雅,就知道他是勤于书法的文人;而在写本背面,当他抄写到疲惫困倦之时,曾顺手临帖习书四行,与前后诗为同一人所书,行楷,前半段:“尚书宣示孙权所求,诏令所报,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冀良方,出于阿是。”为三国魏钟繇《宣示表》开头。其下“恩同骨肉,罔然所厝,奈何奈何,不具,王羲之白”,为王羲之佚札。这样一个书法爱好者,崇拜怀素,经常吟诵赞颂怀素的诗,并把它抄录下来,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其二,或许有人会问,给怀素赠诗人很多,据载有“赠之歌者三十七人,皆当世名流”⑱,包括李白、颜真卿、张渭、戴叔伦这样的名家。为什么偏偏抄录马云奇的这首诗呢?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写于大历四年(769)左右⑲,与写本中可考定写作时间的刘商《胡笳十八拍》、刘长卿《高兴歌》、岑参《江行遇梅花之作》等作品的创作时间接近。这一组8世纪60年代的诗歌,从西川传入敦煌的可能性最大。敦煌写本中流传的唐诗大多是盛唐时期的,说明唐前期中原和河西地区的交流是非常畅通的。吐蕃占领河西之后,这种交流基本中断,而西川与敦煌的交通还在通行。张议潮建立归义军政权后,敦煌和长安的交流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随着归义军管辖范围的缩小,敦煌和中原的交流时断时续。唐末五代,敦煌和关中的交流基本中断,敦煌要接受中原文化,主要是通过西蜀取得相关资料。因为西蜀当时不仅社会相对稳定,而且唐末战乱中大量的中原士人避难西蜀,尤其是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西蜀接纳的中原人士最多,形成了五代时期中国文化艺术中心。
抄录者至此,显然是告一段落。他最后用较大的字抄录了《御制勤政楼下观灯》。这首诗陈祚龙《李唐至德以前西京上元灯节景象之一斑》考证是唐玄宗的作品⑳。饶宗颐说:“字大如钱,十分韶秀,有蝉联映带之美。……此诗为玄宗上元之夜于勤政楼观灯所咏。”㉑唐勤政楼,玄宗开元年间所建㉒。唐玄宗上元夜勤政楼观灯事,《旧唐书·玄宗本纪》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有记载。这首诗所宣示的盛唐太平祥和的气象,正是编者所向往的。作者以这首诗为本集做结,表达了对李唐王朝的深深怀念。
作为一部诗文集,P.2555采用的是分体、类编的形式。分体类编,是《文选》以来编辑总集的基本方式,唐代文人编的总集,大都是分类编的。像刘孝孙(?-632)编辑的《古今类聚诗苑》,释慧净(577-645)编辑的《续古今诗苑英华》,李吉甫(758-814)编辑的《丽则集》,顾陶(783-856)编辑的《唐诗类选》等。《文选》先按照体裁分为赋、诗、骚等39体,每体又按题材内容分为若干类,如赋类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等14类,诗类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燕等23类,不仅反映萧统的世界观,也反映他的文学观,包括文学发展观、文学价值观、文学道德观等。而P.2555作为编者自己阅读保存的诗文集,其分体类编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编者心目中文学主题的孰重孰轻,而且可以从结集分类内容感受到编者思想情感的变化:(写本正面)边塞风情→离愁别恨→气壮山河→怀念英雄→生活情趣→痛苦经历→思乡怨恨→怒火燃烧→(背面)西蜀来诗→书法情怀→同病相怜→缅怀盛世。尤其是不同类型之间的过渡,编者借用不同的作品表达他此时此刻的思想和情绪,更是对其心灵世界的展示。
作为纸写本时期典型的文学写本,Дx3871+P.2555对研究下层文人编辑集部有重要意义,对研究纸写本时期文学的传播也很有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学的传播就是一个作品不断结集的过程。上层文人结集作品,或有政治用途,或为传之不朽,或为自抒情志。而在社会下层,文学的结集主要是社会生活的实用。通过文学写本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写本时期的文学集部是如何制作的,其中体现者制作者怎样的知识、信仰、思想和情感。这是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传播史的珍贵材料。
我们再通过P.2492+Дх.3865缀合写本阐述写本时期别集的特点。
P.2492+Дх.3865拼合册子本无编者署名,存诗22首。可分为三部分:首抄元白唱和诗一组,白乐天《寄元九微之》和微之《和乐天韵同前》。其后抄诗19首,其中17首为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第16首与17首中间夹有《李季兰诗》1首。所抄《新乐府》皆无小序。最后抄岑参的《招北客词》,未完,下缺。计抄白居易诗19首,元稹诗、李季兰诗、岑参诗各一首。
这个写本的性质,学术界有《白香山诗集》(别集)和《唐诗选集》(总集)两种意见。自从发现Дх.3865可与P.2492缀合之后,《唐诗选集》的意见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从选集者的个人编集意识讲,我更倾向于别集说,即认为本写本是《白居易诗选》。但写本时代的“别集”与刻本时代的“别集”是不同的。下面说明我的理由。
缀合写本中抄录了白居易(772-846)19首,而元稹(779-831)、李季兰(?-784)、岑参(715-770)诗各一首,可见编集者的重点是白居易的作品。因为选录了白居易的《寄元九微之》,所以附录元稹的《和乐天韵同前》,这是合乎古人编集情理的。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说:“唐人诗集常以和作附原作后。”㉓岂止唐人诗集,写本时期的诗文集多是如此。因为古人是为了求得事情的原委。比如《韩非子》有《存韩篇》,但收录的除了韩非的《上秦王政书》(《存韩》)外,还收录了李斯《上秦王政书》《上韩王安书》两篇,这主要是为了说明韩非《上秦王政书》之后秦廷出现的情况,用后世别集的眼光看,后两篇是附录。
而《李季兰诗》,抄在白居易《盐商妇》和《叹旅雁》之间。《盐商妇》写不劳而获,享受荣华富贵的盐商妇。《叹旅雁》借旅雁喻人心难测,彼此相食者时有发生。季兰曾出入宫中,优赐甚厚,而一经战乱,即为刀下冤鬼。所以,编者在此插入季兰诗,是一种警醒和关注。作为一种过渡,表达编集者彼时彼地的心情。而岑参的《招北客词》,实际上是一篇招魂词,表达一种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心情。编集者在这里是作为结束的标志,是一种呐喊,也是一种呼救。而写本《招北客词》存双行小注,标注音训,说明编者是很在意这篇作品,悠悠涵泳,低沉吟诵,长歌当哭!
我们认为,写本的编集者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文人,吐蕃攻占领河西以后,他有家难回,流落敦煌。他集录白居易的诗,是表达对下层劳苦人民的关注。中间插入李季兰的诗,是表达对人生无常的感悟,对战乱频仍的忧虑,而下篇接着抄白居易的《叹旅雁》,就是通过白氏对淮西兵变的担忧,来呼应他此时的心情。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编者本来是集录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却偏偏在《盐商妇》《红线毯》(二首皆《新乐府》之一)中间,夹抄《李季兰诗》和不是《新乐府》的《叹旅雁》。
写本所集白居易《新乐府》17首,次序与今本不同,题目也多与今本相异,而且没有今本的小序。说明敦煌本《新乐府》不是按照白氏编定的《新乐府五十首》抄录的。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说:“此小册子,盖据元和间白氏稿本。白氏诗歌,脱稿后即传诵天下,故别本甚多,即白氏所谓通行本也。然其价值,当仍在今行诸本之上。”唐宪宗元和初,李绅首唱《新乐府》20首(已佚),元稹和12首,白居易在他们的基础上创作了50首。这50首,并不是同时创作的,大约经过五六年的时间。元和十年(815),白居易第一次编定自己的诗集十五卷,他把《新乐府》放在150首“讽谕诗”内。《与元九书》写道:“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这个时候流传的《新乐府》,大致还没有经过细致的编排,也没有写序。王重民谓敦煌本根据“元和间白氏稿本”,说的应当正是这个流传的本子。王重民《叙录》又说“此敦煌小册子,似即当时单行之原帙”,这也是他的卓见。但王生生说的单行原帙,主要指白居易新乐府的单行本,像明代流传的《白氏讽谏》二卷那样。其实,写本时代,大多数诗文是以“一个写本”的形式流传,“一个写本”就是一卷,可以抄一篇文章,也可能抄录数篇文章,短小的诗可能抄录更多。
写本中的白居易、元稹诗皆署“乐天”“微之”字,不署名,这在敦煌写本中也是比较特殊的。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大约当时元白诗传播社会,冠以“乐天”“微之”之名。而且写本的款式很严格,题目单列一行,遇到应当表示恭敬处皆空格,说明写本是作为正式的诗集抄写的。
该写本的编集时间,前辈学者因为疏忽或没有看到俄罗斯藏Дх.3865写本,判断有误㉔。写本所抄之诗,以白居易《叹旅雁》创作时间最晚,作于元和十年(815),这是写本编集的上限。此时,敦煌正值吐蕃统治时期。我们认为,从写本编集所表现的情绪看,也应当结集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黄永武推断白居易《新乐府》“完备的诗题与小注,可能是白氏亲手编定前集、后集、续集时所加”,而唐写本大多题注缺失,抄写“或许在他(白居易)自编成集之前”㉕。这也仅是一种推测。白氏一生曾七次编集过自己的诗文集,从元和十年(815)到会昌五年(845),每一次编集的文集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广为流传。敦煌本应当是这流传广泛的文集中的一种。
以上两种是比较纯的文学写本。事实上大部分敦煌文学写本是抄录比较杂乱的,各种文种,尤其是文学作品和一些应用文章杂抄在一起。
P.2633,前残,正面抄写: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