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
世界遗产大会的学术解读|记忆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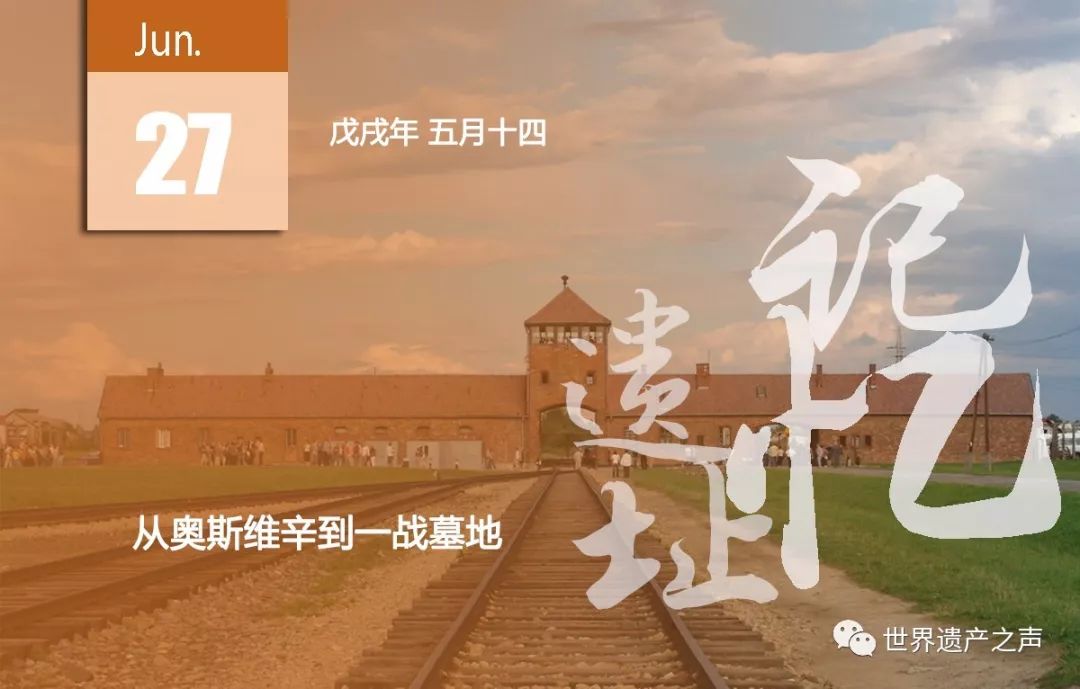
“We speak so much of memory because there is so little of it left.” -- Pierre Nora一、sites of memory
巴林,麦纳麦,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巴林正在进行。几天来,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在大会的正式会议、边会、以及与会者的闲谈中——sites of memory。
 当地时间6月27日中午举行的“记忆遗址”边会
当地时间6月27日中午举行的“记忆遗址”边会
什么是sites of memory?它的中文应该怎么翻译?这又是一个全新类型的世界遗产吗?这还要从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说起。
1978年,波兰政府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为申报项目,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是推迟一年再审议。虽然官方说法是波兰申报的项目太多了(3项),但根据参加了讨论过程的波兰官员回忆,主要原因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很多国家并不认为,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遗迹能够具有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评定文化遗产的6条标准中,标准(ⅵ)要求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标准(ⅵ)的初衷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灾难。
 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波兰的努力下,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再度申请,并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不过,这并非为此类遗产在今后的申报树立了范本,反而设立了更高的门槛。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这种战争遗产有一个作为代表就够了,不能放水太多,同类型的遗产不能再申报。而且,明确要求标准(ⅵ)不能单独使用,必须要和其他标准一起才有效。
40年后,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上面的决定做出了反思。让更多的战争相关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一种可能。
奥斯维辛集中营,和众多与战争有关的遗址,便是今天所说的sites of memory。我们暂时将其翻译为——记忆遗址。
二、difficult heritage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下,记忆遗址特指那些展现“战争记忆”的遗址。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再比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同时也涉及一些体现人类历史上残酷一面的记忆,比如酷刑实施地和监狱。这里的记忆,和我们耳熟能详的记忆又有所不同,它并非泛指所有记忆,而是特指那些可能令记忆者产生“冲突”的记忆。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
在学术界,这种记忆还有一个专门的概念——difficult heritage。
之所以difficult,是因为要准确诠释这种记忆,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作为战争或灾难的见证,这类遗址对于交战双方、对于受害者及其后代、对于没有经历过的普通人,所呈现的记忆碎片注定是不同的。这种记忆往往成为当代民族国家所抢占的话语高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不相让。因此,世界遗产领域此前极少介入此类遗产,毕竟这是一个不讨好的议题,分歧远远大于共识。
随着对战争的反思力度的加强,对于difficult heritage这个此前的概念禁区,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近年来开始尝试突破。今年早些时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门发布了《关于评估近代战争记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的讨论报告》,讨论与战争有关的遗产的申报标准与阐释方法。
“报告”坦诚承认处理这类遗产时的困惑:“如果承认历史从来不是中立的,那么战争同样不是——有胜有败,对于与负面记忆有关的记述也会有所偏颇。难道要让《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给近代战争中胜利者歌功颂德以及展示胜利者视角的工具?”
 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地
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地
“报告”列举了目前在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中的记忆遗址。截至目前,有三处近代战争记忆遗址入选世界遗产—— 1979年入选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1996年入选的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以及2010年入选的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地。
在“预备名录”上的遗址则反映了以下几种近代战争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斯洛文尼亚、比利时、法国、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墓及纪念地(西线战场),比利时和法国(已提名)
–阿尔卑斯山至亚得里亚海和平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遗产,斯洛文尼亚
–恰纳卡莱(达达尼尔海峡)和盖利博卢(加里波利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土耳其
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国和俄罗斯联邦
–1994年诺曼底登陆海滩,法国
–马马耶夫山岗“斯大林格勒战役英雄纪念建筑群”,俄罗斯联邦
反种族歧视战争 – 安哥拉
–奎托夸纳瓦莱自由独立地,安哥拉 – 安哥拉及古巴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战争纪念建筑
内战 – 卢旺达系列遗址
–种族灭绝纪念地:尼亚马塔、穆拉比、毕塞罗、基加利、卢旺达
酷刑实施地和监狱 – 阿根廷、坎波韦尔迪、印度
–酷刑中心-秘密拘留、折磨和种族灭绝地,阿根廷
–塔拉法尔集中营,佛得角,被用作种族灭绝的集中营
–蜂窝监狱,安达曼群岛,印度,政治异见者监狱
本次大会上,比利时和法国共同申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墓葬和纪念地(西线)”被推迟审议,决议草案明确要求,在此类遗产申遗前,必须“全面反思是否以及如何处理与最近的冲突或其他负面的、造成不合或分裂的记忆相关的、可能与《世界遗产公约》的目标和范围相关的遗产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都是战争遗迹。那么,和战争无关的遗迹,就没有记忆冲突了么?
当然不是。实际上,记忆遗址的英文sites of memory,出自法国学者皮埃尔·诺阿(Pierre Nora)的经典概念——les lieux de mémoire,因为lieux可以泛指场所,大多数中文将其翻译为“记忆场所”。 在记忆场所理论中,Nora认为,真正承载鲜活记忆的“环境”(milieux de memorie)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残存下来的某些物质载体去装载和塑造回忆。面对这些载体,人们有选择性的赋予其意义,并创造出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记忆”。
 皮埃尔·诺阿(Pierre Nora)
皮埃尔·诺阿(Pierre Nora)
所以,尽管记忆场所表达的不仅是战争的记忆,但它仍旧是一个不同人群为了实现自己当下的利益而各自解读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战争)记忆遗址是记忆场所的一种特殊形式,世界遗产在面对战争遗址时产生的困惑,又何尝不是每一个世界遗产地所共同面临的纠结呢?
Nora曾说:我们今天总是在谈论记忆,那是因为根本没有剩下多少记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去记忆而已。至于这些记忆是不是真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按照那样的方式发生,并不那么重要。
那么,sites of memory到底翻译成记忆场所,还是记忆遗址呢?其实也不重要了。毕竟在世界遗产语境中,场所和遗址这两层含义,都已经蕴含在这个概念中。
重要的是,这个概念一旦为世界遗产体系所认可并推动,未来会有许多战争相关的遗迹将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时,中国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中国的战争遗迹应该如何纳入到这套话语体系之中?Sites of memory的提出和实践,究竟会解决问题,还是会为濒临四面楚歌的世界遗产带来更多的问题?标准(ⅵ)会不会能够单独使用?在这样标准下的世界遗产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让我们积极介入,把握自己的记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正在翻译《关于评估近代战争记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的讨论报告》,敬请关注。
(文字未标明出处的照片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