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延伸阅读 | 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在胡济图河的日子(节选)
编者按
4月14日起,“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塞北”线上展览陆续推出,展览编制了考察队经历塞北高原的系列图片,沿着袁复礼先生“西行”与“东归”的踪迹,穿越百年时光,走进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万里征程。
作为延伸内容,我们特推出著名探险家、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先生所著《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中第一卷第三章“在胡济图河的日子”(节选),以飨读者。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第三章 在胡济图河的日子(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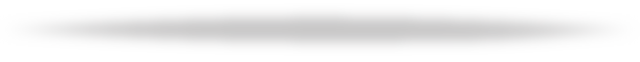
文 / 斯文·赫定
营地
眼下,我们的队伍已汇齐了18名欧洲队员和10名中国队员,这也是整个旅行探险期间所有队员齐聚一处的唯一一次机会,而且不过才持续了几天。
我们这个小村社的21顶帐篷沿着胡济图河岸从西向东排开。最西边是拉尔生的帐篷,紧挨着是我的,一面瑞典国旗在门前的旗杆上飘扬;我的东邻是赫默尔大夫,他也是自己一个帐篷,因为他得有个地方放药箱子处理患者,及存放各种动植物标本。只有当生瑞恒在大本营时,才临时与赫默尔大夫搭个伴儿;再往东是那林和贝格曼的帐篷,挨着他们的一排帐篷住着德国队员;这排帐篷的东边是米纶威的帐篷,里面堆着一个个装满银元的箱子使它显得更为独特。因为队里一下要买很多骆驼,价钱都很高,所以我们得尽快用温火来融化这些银元;再下一个帐篷里放着三四个结实的三角架,那是用来支电影摄影机和普通照相机用的。李伯冷住在这里,他的任务就是用那些感光胶片和大约20英里长的胶卷记录下我们的驼队穿越亚洲沙漠的情形。
长长的帐篷阵营的中间,立着一顶淡绿色的大帐篷,那是我们的餐室。它比所有的帐篷都高,里面排着一张长桌子,每顿饭大伙儿就在里面用餐。早餐不定时,随时可用;午饭是下午1点。下午5点用午茶,晚餐在晚上8点。
紧挨着餐室的是伙房和汉族随从的帐篷,那是一顶白色的大帐篷,不过白得都已经发灰。它的东边是几顶中国队员住的蓝色帐篷;最东的,是中国学生住的大号蓝色帐篷。
在太阳底下,这一长串帐篷就像喜马拉雅山的蓝色山脉一般错落有致。缝在篷顶上的白色饰物在帐篷的尖脊两边奇怪地抽打飘动着,仿佛是提醒人们注意山峦前那终年不化的积雪在熠熠闪光。但那绝不仅是些没有意义的装饰,实际上它们具有很深的含义。我帐篷顶上的装饰比别人都要多些,在帐篷长边一侧两个稍矮些的角上,缝着寿星的图案,它代表长寿。而在篷顶的中间,同样的图案又组成了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圆圈。环绕着它的是5只张开双翼正在飞翔的蝙蝠,它代表着福气。在帐篷顶脊略下边一点,也绣着一只蝙蝠,它的翅膀下,还飘浮着象征吉样的云彩。
从这条帐篷街往外偏南一点,我们又搭了几顶帐篷,一个用来存放探空气球,晚上,它还是洗相片用的暗室;还有一顶是蒙古包,再就是郝德博士的帐篷,里面及外边的四周堆满着各种仪器箱。
郝德博士在帐篷外边立起了一根高高的杆子,杆顶的木笼里安着气象测量仪器。这东西就像个真正的圣物一样被严密地保护起来了,以防被来自远方那些过分好奇的蒙古牧民们偷走。另外,我们还竖起了两根大约10米高的金属杆,上边装着无线电天线。通过天线的时标信号,可以确定居住地的准确海拔高度——只要下边的干电池还工作。
在这几顶帐篷和帐篷街之间,堆放着队里的给养箱子和行李。
当你站到南面的山坡上俯瞰我们的营地时,无疑会感到此情此景是多么的壮观和令人难忘。
我们在伙房的外边搭了一个真正的铁灶,炉子上的烟囱直指天空。只要生瑞恒一回到这儿,伙房的这摊事以及饭菜的安排等就都归他了。他不在时,随队的夫役们再接过去。赫默尔每天都要检查伙房,如果他发现有一条餐巾不干净,有一个盘子或茶杯没有好好洗,他都要对伙房里的人大发雷霆。不过没几天,这位精力充沛的大夫也认识到了这种检查的徒劳。事情只好就这么过去了,况且也没有人因此而生病。
蒙古驼工们住的大账篷足可以容下22个人。他们在账篷外面又修了一个非常轻巧的小火炉,火炉下边并排挖了3个小坑,坑与坑互相连通着。中间的灶眼用来烧水,两边的坑一个用来烧干粪,一个用作通烟道。
晚上,蒙古驼工的大帐篷里传出了歌声,歌声悠扬地飘向天穹。
拉尔生在几位蒙古朋友的陪伴下,到附近和远些的地方,看看在哪儿能买到骆驼。他在蒙古已住了35年,比任何欧洲人都更了解这个地区和这里的人。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骆驼,并能讨个合适的价钱与蒙古人做成这笔生意。
尽管探险队中的大多数人并不闲着,但队里的绅士先生们首先还是要锻炼自己的耐心。一有时间大家就出去打猎,这还能丰富我们的餐桌。
从包头到胡济河的旅程,揭开了我们8年探索考察的帷幕。当时,探险队的主体还是一支统一的驼队,而以后,在我们从胡济图河继续向前走时,探险队被分成了几部分,直到抵达乌鲁木齐以前,就再没有聚集到一起过。

西北科学考查团营地及驼队
(中略)
骆驼暴动
突然一声大喊从蒙古随从那边传了过来:“拉尔生的骆驼!”他们指着西北方向的草场。转瞬间,这群蒙古骑手们催动坐骑,如一阵旋风般疾驰着斜插了过去。他们要阻止那9峰骆驼向东逃窜。其中一峰背上还驮着行李,另外两峰也架着鞍子——剩下的几峰什么也没驮。
不难猜出发生了什么事。这9峰骆驼惊了,挣脱缰绳窜了出来。往远看,只见又出现了一群起伏跃动的骆驼,我们分辨出大约有15峰以上的样子,正在天边的地平线尽处似一阵狂风般地向北刮去。更可怕的是,危机并不一定仅限于这几峰骆驼,而这已经占了整个驼队的六分之一。
此刻是8点20分。我们在等待着拉尔生的消息。狄德满博士和我登上了最近处一个小山头,用望远镜向西扫去。两公里外,大约有50峰骆驼正在悠闲地吃着草,那是一个汉族客商的驼群。极目西望,可以看到一串小亮点(显然是已经甩掉了的行李包)和一条黑色的暗线,很可能正是我们的那帮畜生。在左边的西南方向上,有一峰白骆驼在驮着行李飞奔,紧跟在它后面的是一个骑骆驼的蒙古驼工。他很快就抓住了逃犯,赶着它向最近的集结地走过去。骆驼挣扎着不愿听命。赫默尔和狄德满赶快过去帮着那驼工卸下驼背上的行李,把它赶进营地。这时,先前看到的那9峰骆驼也从东边被抓了回来。那匹白骆驼的左胁下被行李箱子的边刮得血肉模糊。驮着行李当然不适于高速奔跑,如果它们老实走路,行李箱本不会碰到身体。回来的9峰骆驼中还有两峰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
华志赶快察看了事故的现场,然后跑回来告诉我说:
“看来情况糟透了,行李包扔得到处都是,大概有100多峰骆驼逃跑了。”
“那么,拉尔生怎么说?”
“他说想喝上两桶水。他认为在新营地得重新组建骆驼队。”
华志骑的骆驼立在一群驮着大米的骆驼之间。突然,不知什么原因,又有一峰骆驼惊了起来,这家伙一头扎进驼群中间,暴跳着甩掉了身上的米袋子,就好像身上扎满了刺。接着它又闯进了还没完全拆光的营地,所到之处引起一片骚乱。一转身,它又冲回骆驼群里,这股疯狂的劲头多少也传染了其他骆驼。好歹最后它算是被逮住了,驼工们把它牢牢地拴了起来。
赫默尔陪着我步行去查看拉尔生遭遇的这次事故的现场。到他那儿大约有4公里远。
还离着很远,就能看到草场上到处乱扔的行李鞍子,有的乱堆成一团,有的还用绳子捆着(有一个蒙古式的鞍架,上面是用6块长方形的毯子包着行李,然后再紧紧地绑在两侧的木架子上,木架的两头又用绳子捆到一起)。这条路的远近各处都可见扔下的箱子、包袱、行李、帐篷杆、垫子和其他杂物,一切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不过在新的宿营地,恐慌情绪已经减轻,我们忙着问候见到的所有人。
大约有50峰骆驼被用绳子穿过鼻子拴在这里,周围用一圈行李紧紧地围着它们。比较来看,行李倒还没散捆,但不少骆驼的身上都留有血痕。拉尔生走了过来,神情还是那么平和内向,不过你还是能看出他有点激动。他嘴里不住地念叨着什么耶路撒冷、滑铁卢大灾。终于他还是抑制住了感情,简单地说了句:
“我简直渴死了!”
“等一下,我们带来了水!”
同来的骆驼被招呼卧下去,有人卸下一个木桶放在地方。拉尔生扑上去猛饮起来。我不知道他喝了多少,后来赫默尔和我也都跟着喝上了水。水真是美极了,在这干燥的夏日更给人这种感觉。
拉尔生叙述起事情的经过:一开始,他就注意到骆驼群有点骚动不安,看上去很紧张,望着天边的地平线不住地晃头。驼队走得很慢,时常要停下来看看行李安放得是否合适。三支梯队在行进中互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离开营地大约5公里后,他的队伍已由三支变成了五支。他们齐头并进,慢慢地就挨得有些太近了,这时拉尔生发现,再想让骆驼保持平静已经很难,他立即决定就地扎营。但是,骚乱还是发生了。当时整个驼队正好处在一条小溪边的凹地上,考虑到如果下大雨,河水可能泛滥,拉尔生想让队伍再往前走一点。前方200米外的一块斜坡地就是块更好的宿营地。如果他们当时一直呆在凹地里,暴动也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但厄运到底摆脱不了,队伍尾部一个狡猾的家伙弄松了驮着的行李,突然窜进了前边的同伴堆里。
它跑得越来越快,背上的箱子颠得叮当作响。显然是受到了声音的惊吓,它更猛烈地窜跳着。离着它最近的几个家伙也跟着惊了,接着又传到整个驼群。这下可一片大乱了。如果受惊的驼群有规律地成队向西跑,驼工们或能追上去止住它们。但实际上驼群是绕这圈跑,绝大部分骆驼还边跑边跳,想把背上的行李甩掉,结果行李扔得到处都是。它们东冲西撞,强健的骆驼看上去就像是游动的火焰。时而传来刺耳的冲撞和撕裂声,就像建筑物倒塌——身处这场风暴的中心,无疑有踏伤甚至伤胳膊断腿的危险。拉尔生立在那儿,一只手牵着自己那峰骆驼的缰绳,另一只手提着根蒙古驼鞭。那鞭子足有一码来长,粗得像跟棍子。他不住地用鞭子狠命抽打着那些疯狂的骆驼的最敏感部位——鼻子。骆驼的鼻腔是软骨组织。这突然的一顿猛揍,抽得这群畜类安静了下来,不再乱跑了。它们只要一有窜跳的征兆,鼻子马上就会挨上一下打。拉尔生终于治住了大约20峰狂暴的骆驼。他想再多制服几峰,但突然又有一群狂奔的疯骆从眼前掠过,这下又刺激了右侧已经安静下来的骆驼。结果只剩下几峰还呆在他身边,其余的又逃之夭夭。米纶威战斗得更是勇猛,拉尔生很欣赏他表现出的力量与心计。但他唯一的错误就是贪心不足,想抢回大多数的骆驼。

骆驼暴动
结果150峰骆驼跑得只剩下了13峰,余下的就像一阵风似地不见了。有个大家伙背上还驼着两口大箱子,足有220公斤重。箱子搭在它脊梁两边,看上去它像是只羚羊。拉尔生以前曾带着驼运羊毛的驼队在蒙古草原上走过,也曾遇到过骆驼骚动的情形,对付这类小麻烦他已很有经验。但他绝没想到会发生7月22日这么大的驼群暴动,所有的骆驼都发了疯。他嘴里不停地叨叨着:
“我会教训你们的,这帮无赖!我要你们每天走80里地,驮上400斤的东西连走8天——这你们就没精神闹了!”
蒙古驼工一个个不错眼珠地盯着那只招来灾祸的元凶。这孽障此时正卧在那里,背上被加上了更多的重物,用这来调理它的脾性。至于其他骆驼,几个蒙古驼工向我担保说,灾难绝不是由于骆驼养得太肥、喂得太好、休息得太多带来的,也不是因为受惊的缘故,那不过是骆驼愿牺牲自己,以供奉营地附近的土地神灵的一种自然结果。我心里禁不住向他们求饶道,牺牲点儿别的什么值得奉献的东西就行,就别拿逃跑的骆驼和丢失的箱子作贡品。
李伯冷非常沮丧,怨自己当初没跟拉尔生一道走。对他来说,那种场面如果要拍成电影一定是天字第一号精彩的,值得花上50倍的时间等这么一个镜头。接着他又自我安慰说,在登上前往噶顺淖尔之路后,还会有别的机会的。我也尽力劝慰他,并说,当时如果他真的处在暴乱的地狱之中,这会儿恐怕都成肉酱了,而且连摄影机也得被踏得粉碎。
我问拉尔生,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当然,”他说,“丢了两个装银元的箱子,大约有4000块银元。现在正尽力寻找,但到目前还杳无踪迹。米纶威刚刚又出去找了,要是钱真丢了,我们怎么办?如果土匪或贼发现了这笔钱,咱们就再也甭想要回来了。4000块大洋对咱们来说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
“好了,听天由命吧,我也不能再派人去北京取钱了。”
傍晚7点,一个驼工带着15峰骆驼回到了营地,有几峰骆驼身上还驮着行李。“啊!”拉尔生高声叫道:“丢的钱箱找到了!”
我们就像是沉船上的水手正拼命地向岸边游,不管有个什么都要抓住。显然,我们又得在这儿至少呆上3到4天;情绪不稳的骆驼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平静下来,而且,拉尔生也需要有更多的人才能重建一支大驼队。他想再雇10名汉人给队里的蒙古驼工当帮手。他已经派人到附近的村庄招人去了。
*注:本文节选自斯文·赫定著《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一卷第三章“在胡济图河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