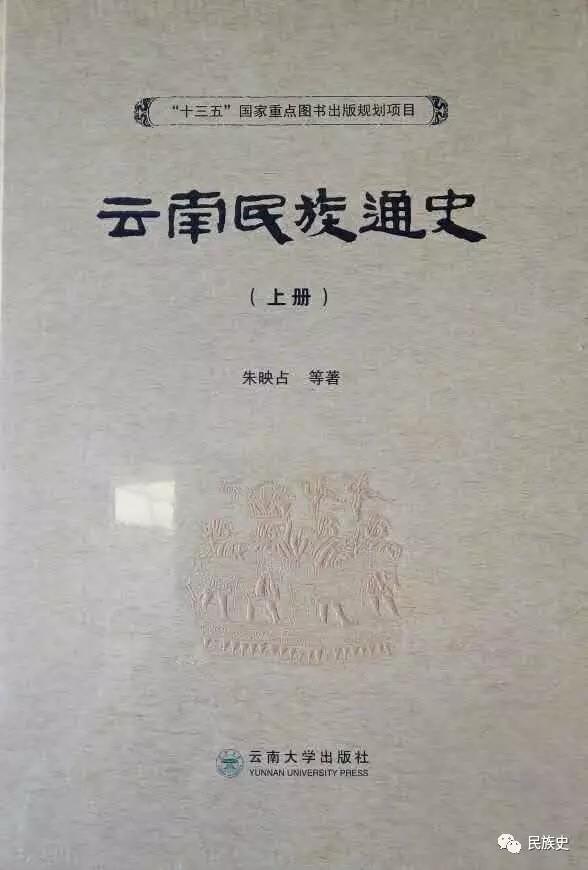书籍资料库
云南民族通史
内容简介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先秦时期云南的民族
第一节 云南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一、云南的古猿
二、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一)元谋人
(二)昭通人
(三)西畴人
(四)丽江人
(五)蒙自人
(六)昆明人
(七)姚关人
三、旧石器时代云南的古人类遗址
(一)江川县甘棠箐文化遗址
(二)塘子沟文化遗址
(三)富源大河遗址
第二节 云南的新石器文化
一、滇池地区——石寨山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二、滇东北地区——闸心场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三、滇东南地区——小河洞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四、滇南、西双版纳地区——曼蚌囡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五、金沙江中游地区——元谋大墩子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六、洱海地区——马龙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七、澜沧江中游地区——忙怀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八、滇西北地区——戈登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九、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第三节 云南的青铜文化
一、洱海地区以剑川海门口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二、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
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的青铜文化
四、澜沧江、怒江中下游青铜文化
五、云南青铜文化的特点与族属
六、北方青铜文化对滇国青铜文化的影响
(一)武器
(二)装饰品
(三)礼乐器
(四)陶长颈壶
(五)服饰
(六)丧葬习俗
七、青铜时代云南古代民族创造的铜鼓
(一)铜鼓的起源问题
(二)铜鼓的创造者
(三)铜鼓文化的流布及影响
第四节 外来族群与云南本地族群相融合而产生的云南早期民族
一、与西北氐羌系统有源流关系的云南早期民族
(一)何为氐羌民族
(二)氐羌民族向西南的迁徙
二、与东南百越民族有源流关系的云南民族
(一)何为百越民族
(二)滇人与越裳
第五节 关于云南是否存在“百濮”的讨论
一、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三大族群说
二、对云南古代没有百濮的论说
第六节 先秦时期云南民族关系中的主要事件
一、杜宇与云南
二、庄蹯入滇
(一)关于庄蹯入滇的记载
(二)关于庄蹯入滇的学术争论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云南民族
第一节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治理与政区设置
一、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治理
二、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政区设置
第二节 秦汉时期处于分化与融合过程中的云南民族
一、《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其对秦汉时期西南民族的识别
二、与氐羌民族有源流关系的云南民族
(一)焚人
(二)昆明人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云南民族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云南民族
第五章 宋代的云南民族
第六章 元代的云南民族
第七章 明代的云南民族
第八章 清代的云南民族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云南民族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云南民族
大事记
附录
后记
绪论
一
云南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
和云南的历史相比较,云南作为一个行政区的概念出现比较晚,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设置的益州郡,治滇池县(今云南晋城),当时由于对云南的治理刚刚开始,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益州郡之下设置了二十四个县,其中就有云南县(地在今天祥云县),对于为什么要称为“云南县”,《续汉书•郡国志》的注解释说:“(云南)县西北百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一,郁泉高峻,与云气相连接,因视之不见。其山固阴冱寒,虽五月盛暑不热。” 显然就是因为汉武帝设置的云南县在这座山的南边,所以叫做云南县。这是云南概念的第一次出现。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以云南县为基础设置了云南郡,这是云南的概念第一次在内涵上发生变化,由县变为郡;公元738年唐玄宗封南诏国的皮罗阁为云南王,这是云南的概念第二次在内涵上发生变化,由郡名变为王国名;公元1274年,元朝设云南行省,云南的概念第三次在内涵上发生变化,成为了云南省的省名,至今不变。
从文化的角度,文人对云南概念的使用也有不同,例如唐朝人樊绰写的《蛮书》,也叫做《云南志》,显然是把整个南诏国称为云南,又例如到了大理国时期还有部分文人把大理国叫做云南,当时的四川峨眉县人杨佐明明是到大理国买马,但是却写了一部《云南买马记》,等等。由此可见云南概念在世人心中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同时也说明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在政治上云南就成为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云南概念出现得很晚,但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文明出现得很早,再加上云南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所以作为一部通史我们也对生存在云南的古猿进行了一些介绍,当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把新石器晚期作为研究云南民族的开端,因为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云南已经有大量的文化遗存,表明当时生活在云南的人类已经在向着民族的方向发展;而今天云南的民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民族识别产生的,所以云南民族通史的时间下线涉及到了21世纪初年。
云南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曾经在云南存在过,但是现在已经消亡的民族、以及经过几千年来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到现代通过民族识别最后形成的彝族、藏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基诺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苗族、瑶族、蒙古族、满族、回族、汉族等二十余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对上述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构成云南民族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云南在中国先秦时期被当时的地理学家认为属于九州之一的梁州,因此从文化上看云南在先秦时期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和发展到现代的各民族,都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贡献,故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就是中国民族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而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也是多民族分布的地区。云南的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等15个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都居住在云南,他们当中的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生活繁衍在云南。汉代,少量汉族开始进入云南,藏族、普米族、蒙古族、回族、苗族、瑶族等民族的先民是8世纪以后陆续从我国其他地区迁入云南,或者是因为政区划分而成为云南民族的。至于在人口普查当中出现的高山族、东乡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的极少数人,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云南工作或者是临时在云南工作的,所以他们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云南就有众多的远古人群分布,并分别与西北、东南沿海的远古人群联系密切。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西北甘青高原为中心的氐羌系统民族和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百越系统民族,其分布都一直延伸到云南各地。属于氐羌系统民族的人们,多散居在云南的北部、东北部和西部、西北部;属于百越民族的人们,则散在今云南的东部、东南部、南部、西南部。 此后,孟高棉民族的部份先民也进入云南南部。而苗、瑶民族的先民进入云南的时间相对较晚,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元明清时期进入云南的民族还有蒙古族、普米族、回族、满族等民族的先民。
具体来说,古代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有秦汉时期的靡莫、劳浸、僰人、昆明、白马、摩沙,有南北朝后期的乌蛮、白蛮、羌人诸部,有元明清时期的罗罗、白子、麽些、窝泥、栗些、俅人、怒子、西蕃、倮黑、峨昌等,他们发展到今天,成为了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基诺族、景颇族、独龙族、阿昌族、普米族等民族;古代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有秦汉时的滇人、勾町、漏卧、滇越、哀牢,唐宋时期有僚人诸部、白衣、金齿、银齿、绣脚、绣面,有元明清时期的摆夷、侬人、沙人、仲家、土僚等,他们发展到今天,成为了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族、傣族、水族、布依族等民族;秦汉时期的云南还有苞满、闽濮,唐宋时期的朴子蛮、望蛮,有元明清时期的蒲蛮、崩龙、卡瓦,他们发展到今天,成为了南亚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德昂族和佤族。
由于民族众多,其语言属系也多,除汉族、蒙古族、回族外,大致可以将云南民族的语言属系分为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及其下属的4个语族、11个语支。汉藏语系除汉语外有藏缅语族的藏语支(藏语)、羌语支(普米族)、彝语支(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白语支(白语)、景颇语支(景颇语、怒语、独龙语)、阿昌语支(阿昌语);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壮语、傣语、布依语)、侗水语支(水语);苗瑶语族的苗语支(苗语)、瑶语支(瑶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有佤语支(佤语、德昂语)、布朗语支的(布朗语)。云南的回族使用汉语,蒙古族改操彝语、汉语,满族也基本上使用汉语。
总之,云南成为多民族地区,并不始于近代。从先秦到汉晋时期,云南已经生活着许多民族群体,到元明清时这些民族群体基本形成了现代民族的雏形,云南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到元明清时期也基本形成。
二
云南民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其发展的方向、规模都受到地理生态环境的制约,地理生态环境是云南成为多民族的成因之一,同时也是云南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因之一。
地理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条件。对于大部分云南民族而言,地理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此,自然生态环境和由生态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程度等构成了云南民族发展的背景和基础。与此同时,在民族生存发展的许多客观条件中,地理生态环境也是最为重要的,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对民族特征的产生有制约作用,是形成这一民族而不是那一民族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云南省地处高原,东边是云贵高原的西部,主要是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和丘陵,西北部是横断山纵谷区,高山大河相间,与青藏高原相连。地势西北高,南部低,地形错综复杂。在这两大类地区之中,有1400多个盆地(云南人叫做坝子)。从气温、降水等自然因素而言,云南南部优于北部。全省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地占了94%。广大的山地大致又可分为滇东高原、滇西高原、滇西南高原和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云南的民族就分布在这以山为主的空间之中。
从总体上看,云南大致以元江河谷、云岭山脉东侧的宽谷盆地一线为界,把云南分为两大部分,该线以东是一块边缘破碎、中部较平坦的大高原,西部为山高谷深、山川并列的高中山山地。①这种地理条件使云南各民族的交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区更是如此,这对民族的发展也同样造成了限制,民族只能在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与发展,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②即在“西南夷”地区有众多的民族存在,很显然,这种情况几千年来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地理阻隔应该是主要原因。
元江——红河一线不但是云南的一条地理分界线,它还反映民族分布情况。从民族分布的角度看,元江——红河流域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的接触区,呈犬牙交错状态,向北走则壮侗语族的民族越来越少,仅仅在金沙江两岸有少量的傣族、壮族和布依族,向南走则藏缅语族特别是彝语支的民族也呈递减的趋势。
此外,山多且海拔变化大导致了云南民族的立体分布格局,从而有了苗族住山头,傣族、布依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这样的说法。这种立体分布的格局除了历史上的政治原因外,与气候及地形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民族的立体分布,肯定就有立体农业或者说云南各民族的立体经济,即东部滇东高原、滇西南高原的农耕经济较为发达,而以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为主的地区则是畜牧经济所占比重大,这一现象也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早就有过描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西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综上可见,云南民族分布格局是云南地理生态环境的一个反映,反之也可说,云南地理生态环境决定着云南民族的分布格局。
如果以上的认识没有失之偏颇的话,我们认为:迄今为止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从明中叶开始,云南的坝区几乎都是汉族分布,到清代以后这一情况更为显著,所以汉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二半山区或山腰有少数民族同汉族杂居,或者是同汉族聚居区相联结,或者是交通要道上的少数民族(如白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基本与汉族相同。但由于云南的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4%,大江大河对地形的切割非常严重,所以稍稍离县级以上城市远一点的地方,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就相对缓慢。
同样是因为云南各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各民族为了生存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生态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物质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精神文化。
地理原因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云南各民族的治理也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最早是汉王朝在云南设置了益州郡,但益州郡并未将所有的云南民族纳入直接统治,哪怕改土归流后,也还有“江外宜土不宜流”的特殊政策,这客观上又延缓了云南民族的融合程度,反而加大了各民族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虽然云南山多,但是云南的各民族与周边的民族交往是存在的。历史上云南地区维持与内地交流的通道主要在滇东,有两条重要的通道,一条是从四川成都向西南,经过邛崃、清溪、越嶲 、沪津诸关的川滇西道,与云南中部的姚安、祥云相接;另一条是出成都南下戎州,经石门关、昭通的川滇东道。
在云南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通常是以有湖泊的盆地为民族的发展中心,最大的民族发展的中心有两个,一个是滇池地区,另一个是洱海地区,这两个地区在云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地位重要,当中央政府对云南行使上下统属的政区关系时,云南的行政中心地就在滇东,例如两汉的益州郡、西晋的宁州、元明清时云南省的行政中心都在滇东地区;反之,当云南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云南的政治中心就有可能在滇西,南诏国、大理国就是如此。
在地理和历史的双重作用下,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居住在平坝的民族发展快于山地的民族,处于交通沿线的民族发展快于交通不便的民族;与汉族接触较多的民族其生产水平高于与汉族接触较少的民族;较早纳入郡县统治的民族发展快于较晚纳入郡县统治的民族。 由于上述原因,各民族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甚至连同一民族内的不同支系,也有很大的差距,如滇中彝族、滇东南彝族与大小凉山彝族、滇东北彝族在经济发展上就有差距。
历代政府也看到了这种不平衡性,他们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云南是“蛮荒之地、化外之地”;从经济的角度认为云南是“不毛之地”;从生态的角度认为云南是“瘴疠之地”,所以在云南这一边疆地区采用了特别的统治方式,即历史上的羁縻制(如封滇王,句町王等)、土司制(如宣慰使、安抚司等),这些制度虽然适应了云南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但也扩大和加深了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全国相比较,这种不平衡性更加明显,所以才有阎红彦的“云南边疆特殊论”,才有云南省情特征的“四高四低论”。反映到社会领域,便有了“云南是社会发展活化石”的比喻,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有理论上的缺陷或认识上的偏差,但它明显地表现了云南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基本事实。
总之,云南民族社会发展极大的不平衡性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继续存在,特别是在省内中心城市快速发展之后,这种不平衡性更显得突出,例如国家特别关注的发展极为缓慢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云南就有7个,国家级的贫困县、特困县更是数以十计,这些都是不平衡性的表现。
三
从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看,往往是先有地区性的局部统一,然后才逐步向统一多民族国家过渡,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在云南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云南多高山大河,海拔高而纬度低,各种不同高度的气候与生态条件都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这里是人类诞生的摇篮之一,开远古猿(距今1400万年)、禄丰古猿(距今800万年)、元谋古猿(距今800-600万年)和保山古猿(距今800-400万年)的化石就发现于云南,加之云南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等远古人类及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表明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应从云南翻开,表明云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国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云南发现的元谋人、丽江人等都具有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这说明了云南的远古居民与中国大地上的其他远古居民在种族来源上是一致的。
郡县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汉武帝时,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东汉比西汉又有加强,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又将益州郡中的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等六个县加上另设的哀牢、博南两县,设置了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完成了对今云南西部和西南部边疆的全部统一,把西汉时期益州郡西部和西南部界外的今云南德宏州、保山市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都全部纳入了东汉的版图之中,所有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民族也同时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这样的民族情况基本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一直成为云南民族发展的主流,奠定了云南现代民族发展的基本格局。
云南民族发展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其主要表现为:民族众多,有自己长期的活动空间,一些民族唯云南所独有,如怒族、独龙族、等;各民族的关系除唐、宋时期是南诏国、大理国政权和中原汉族政权的关系外,主要表现为整个云南非汉族与汉族的关系、非汉族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南诏政权强盛之时,其所控制的地区不仅局限于今云南,而是到了今天的缅甸西北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及今天老挝、泰国、缅甸三国的三连接地带,对东南亚的历史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与这些地区的民族发生过诸多联系。
云南的绝大多数民族从族源上讲虽然来源各异,但都算得上是土著,是历史上各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云南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武帝元封二年以后,汉王朝通过开路、设置郡县、移民等措施,汉民族开始进入云南,强大的汉文化以巴蜀为基地进入西南夷分布区,但结果却是汉武帝始料不及的,部分汉文化得以保存下来,但汉族人口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融入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这种民族间的分化与融合趋势和特点一直到明代才有所改变。因此,可以说云南民族的融合在明以前是汉族融入云南民族,以单向融合为主,而明以后的融合则是双向融合,由此形成了包括汉族在内的云南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
魏晋时期云南民族的融合很有特点,主要是汉族大姓爨氏在割据的情况 下,逐渐夷化,到隋唐时最终融入到云南少数民族之中。
唐宋时期,南诏国、大理国与唐宋的交往多以矛盾冲突和文化交流的双重形式进行,例如唐与南诏的天宝之战,南诏派遣南诏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汉文化、或通过交换获得汉文化典籍。因此,汉民族与南诏大理国辖境内的民族融合就很少。
元明清三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并且越来越巩固,云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在经历了南诏国和大理国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后,最终又融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来,本时期云南民族的融合有两个特点。
第一,汉族吸收少数民族,其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动地、不自觉地融入汉族;二是在大汉族主义的背景下,部份少数民族在民族传统上有所保持,但为了避免遭受民族歧视而称汉族,实际上这种现象只是一种民族的假融合。
第二,明代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因为通婚的原因,也有部份融入边疆民族之中。总之,由于民族分布地域的变化,民族聚居的状态被打破,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的变更,云南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在元代以前表现同源异流,在元代以后既有同源异流,也有多元合流(少数民族融入汉民族)和异源异流(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
秦汉以后,云南民族的发展和汉民族的发展还有一种互动性,即当统一多民族国家强大之时,汉民族及中原内地政府与云南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就紧密,相互之间的互动就加强,反映在文献上的记载也就十分丰富,例如《新唐书˙南蛮传》有上、中、下三卷,《元史》《明史》《清史稿》中有关于云南的“地理志”,有云南的“土司传”;而当统一多民族国家分裂、民族纷争之时,史书对云南民族的记载就少,甚至产生错误,如《宋史》将“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之中,而且只有不足千字的内容。
总之,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云南各民族如果说在秦汉以前与中国内地只是一种文化联系的话,那么到汉代云南相当多的民族已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宋时期云南虽然出现了独立发展的南诏国和大理国,但南诏国和大理国独立发展的几百年间却为元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元代的统一则把前代所有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的云南各少数民族,全部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明清以后经过改土归流和郡县制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统治更加深入,①云南各民族都全部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特别是1840年以后,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云南各民族已经完全成为中国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
作为一部云南民族通史,是必须要研究近现代云南民族史的。
1840年以后,云南民族的发展历史和民族关系与古代相比更加错综复杂,在原来云南各民族与封建统治的矛盾、与大民族主义的矛盾之外,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从清朝的道光皇帝(1821至1850)开始,中国民族的发展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美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英法对云南的入侵,给云南各民族造成严重的后果,使各民族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冲击,经济开始萎缩,作为中国有机组成部分的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也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两大矛盾中,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鸦片战争对其直接冲击似乎不太大,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是帝国主义的矛头直指之地,而且帝国主义对云南的染指还是打开中国后门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占领印度后并不以此为满足,派遣西姆士出使缅甸,之后在他的《使缅记》报告中指出:滇缅之间存在着大宗的棉花贸易。另一个英人海勒姆•考克斯也对缅甸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报导了更为详细的情况。之后英国人便订下了借助缅甸打开中国后门的计划,故入侵云南就成了英国对华战略的目标。道光四年英国发动了侵缅战争,强占了缅甸南部。光绪二年,英国借口马嘉理被杀,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取得了在云南的许多特权。光绪二十年,英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约》,光绪二十三年,英国再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约附款》,夺取了中国云南的大片土地,取得了英国驻蛮允领事馆移驻腾冲,在思茅、腾冲设立海关的权利。宣统二年,英国出兵侵占了片马、古浪、岗房等地。
对云南的侵略,法国也不甘落后。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占领越南后,便以越南为基地,将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挑起了中法战争,侵占了云南猛乌、乌得等地。而腐朽的清政府妥协退让,不败而败,从1884年起,先后和法国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中法新约》、《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续议商务专条》等4个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使法国获得了在蒙自、蛮耗通商开埠和日后修筑进入云南的铁路等权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又和清政府签订《中法商务专条》附章,约定将蛮耗关改在河口并在思茅设立海关。
在上述重大变化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云南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国家主权行使受到干扰,领土不再完整,云南成了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各民族成为英、法两国掠夺的对象。因此上升到中华民族的高度,则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此决定了云南民族近现代历史在政治方向上发展的基本势态。从马嘉理事件、刘永福抗法斗争、七府矿产事件、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云南各民族的反帝斗争精神都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道光以后到中华民国时期,云南的民族关系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之前民族关系主要是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关系的内容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但此后随着英、法帝国主义从越南、缅甸的进入,则增加了与英、法帝国主义的关系,关系的内容是领土主权、是民族危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云南的事情已经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云南发生了极为深刻、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推行土改,在民族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实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领主经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引进先进的生产力、传播现代教育、卫生知识、宣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尽管如此,并不是云南所有的民族都融入了云南整体经济的发展之中,如怒族、独龙族等民族,他们对工业化、信息化的认识与了解,就大大落后于中心城市和坝区的民族,他们所接触到现代化的事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如汉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他们正面临现代化的浪潮和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五
对云南民族历史的研究是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关系到中国国家的文化建设,是中国国家发展历史文本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开始,云南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有效地从政治上治理在云南少数民族,就成了史家对民族历史特别关注的一个政治动因,这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第一次对云南民族有了详细记载。
除各朝正史中有关于云南民族的历史记载之外,历代官家编纂或私人著述的各种类书、丛书、方志、游记、笔记中,也有许多关于云南民族的记载,较为重要的如常璩的《华阳国志》,樊绰的《蛮书》,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李京的《云南志略》,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无名氏作的《土官底簿》,郭松年的《大理行记》,龚柴的《云南考略》,肖石斋的《乌蒙纪年》,无名氏的《乌蒙秘闻》,刘彬的《永昌土司论》,魏源的《西南夷改流记》,无名氏的《招捕总录》,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余庆远的《维西见闻记》等。
此外,云南的地上和地下还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民族历史的遗存和遗物,如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云南楚雄万家坝遗址,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大理太和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和遗物为研究云南民族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可弥补史料之不足。历代遗留下来的摩崖碑刻也保存了许多十分可靠而又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如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南诏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等,这些特殊载体的文献,可与史料相印证。
真正对云南民族历史进行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如果从时间上划分,二十世纪的云南民族史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十年为第一个阶段,后五十年为第二个阶段。
二十世纪云南民族史研究的前五十年,部分成果是在实地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911年至1914年间,两次到云南和四川凉山地区进行调查,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等论文;1928年,中山大学教授杨成志到云南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调查,后来有论著《《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发表 ;1935年,民族史学家方国瑜对滇西进行实地考察,到云南大学任教后,根据调查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和《界务交涉纪要》等著作;李拂一对西双版纳的傣族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并于1933年出版了《车里》一书。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云南的外国传教士,有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汉名邓明德,或译为邓保禄),被称为“撒尼通”,他在深人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先后发表和出版《云南罗罗文字研究》《法倮字典》。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外国人在云南民族地区的探险考察活动的,还有沙尔雅考察队在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保尔•博厄尔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
法国人巴克(Bacot)于1907年、l909年,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成为西方东巴教研究的最早开拓者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okogorov, 1887-1939年)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进行云南人类学调查 。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的约瑟夫•洛克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上下卷、《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上下卷)《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著述,在洛克研究的同时和之后,又有昆亭•罗斯福(Q.Rooseveldt)、顾彼得(Peter Goullart)对纳西东巴文化进行了研究 。
此外,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云南的相关记录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云南民族史方面的内容。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官员戴维斯(H.R.Davies)1894年到1900年间多次到云南调查,除地理方面的内容外,着重搜集民族学资料。其著作《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链环》,根据对彝、苗、藏等民族的语言、习俗调查资料写成,于1909年出版,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甚至影响到云南民族的分类和基本定位。”
抗战爆发后,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向西南地区转移,主要集中在昆明、重庆、成都、贵阳。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结合文献记载,进行民族调查。昆明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主要的学术研究中心。西南联大设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出版了《边疆人文》三卷。云南大学建立了方国瑜等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丛书”。
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也结合自己的专业,通过调查研究,完成了多学科综合的民族史研究论文,如罗常培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又如闻宥发表了《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么些象形文字之初步研究》。这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研究云南民族史颇有价值,弥补了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问题。
20世纪后50年是云南民族史研究的第二阶段。云南民族史研究虽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出现过短暂的停滞,但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以后,云南民族史研究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1950年,中央访问团访问了西南民族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并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了慰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 。西南访问团是中央派出的第一个访问团,访问团由中央二十多个单位120多人组成,加上地方补充的人员,访问团又分为三个分团,分别赴西康、云南、贵州访问。访问结束后,访问云南的第二分团先后整理和出版了《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其中包括攸乐人(今基诺族)的情况、《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等成果;访问贵州的第三分团先后撰写和出版《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兄弟民族在贵州》等成果 。
1959年云南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南民族史专门化”(专业方向),后来改为“云南民族史专门化”,同时建立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 这些机构和课程的建立和设置为云南民族史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持续进行打下了基础。
1980年后,云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1982年江应樑著的《傣族史》、1984方国瑜所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彝族史稿》、1984年尤中著《中国西南民族史》、1987年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1994年尤中的《云南民族史》、1998年开始出版的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这些专著或者是史料都是云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阶段,而且还把研究向近现代云南民族史的研究领域推进,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六
从云南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云南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其形成与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其中有无规律可以寻找?对此,我们的基本认识是:
第一,云南民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其发展的方向、规模都受到地理生态环境的制约,所以地理生态环境是云南成为多民族的成因之一,同时也是云南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因之一。
第二,云南民族的发展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云南民族的发展是中国民族发展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在汉武帝元封二年以前,云南各民族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之中,与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群体主要是以文化交流、经济联系为主,汉武帝元封二年以后,云南在政治上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云南民族开始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同步;因此,云南民族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呈现出了这样一个趋势,即越往近现代发展,对云南民族的记载与认识就越来越具体、细致,例如在秦汉时期,我们仅仅知道有昆明人、叟人、僰人等等,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出现了众多的民族名称,而到了元明清以后,云南的民族名称可以数出数以百计。
第三,从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云南民族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民族融合,具体表现为分化与融合,所谓分化,就是同源异流,例如来自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群体,到了云南之后,在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产生了民族的分化,与云南的本地民族群体融合,产生了昆明人、僰人、叟人等等;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民族群体的发展又出现了异源同流,例如乌蛮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来的昆明人、叟人、僰人等成为乌蛮。
第四,云南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分化与融合相互交替的过程当中发展变化的,例如乌蛮到了元明清以后,又开始出现更大规模的民族分化,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许多民族就是由乌蛮分化而来的。
第五,对云南民族历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关系到中国国家的文化建设,同样是中国国家发展历史文本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没有云南民族历史的研究历史那么中国国家发展历史当中文化建设内容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