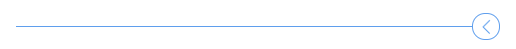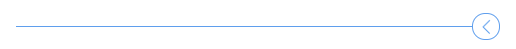✪ 新华视界
【导读】编者按:
如果没有1929年春四川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在自家院子附近挖水沟时意外发现玉石器,神秘的三星堆不知何时才会向世人开启大门。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组织考古队在已发现疑似玉石器“窖藏”的附近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发掘,共出土文物600多件。从此,三星堆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12平方公里。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三星堆祭祀区开展发掘,在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截至目前,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三星堆遗址历次考古出土的文物数量已超过5万件。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被确认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过去30多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已被解决。
本篇“我在现场”由三位进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下了珍贵现场资料的新华社记者为您讲述镜头里的三星堆故事。

自2021年至今,我有幸参与了三次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重大发现的报道,近距离观察、感受到了考古工作者是如何进行考古发掘的。2021年3月1日,早春的四川广汉,路边满是大片盛开的油菜花。我第一次来到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采访报道这次必将震惊世界的考古新发现,心中满是兴奋与期待。通过安保人员把守的铁门后,眼前的整个发掘区上架起了高大的全封闭考古大棚。走进考古大棚能看到4个大小不一的玻璃房子相连坐落于一边,另一边则是数个连在一起的白色房间——现场保护实验室。考古大棚里铺设了木制通道,其余部分基本都被灰色的毯子覆盖。这4个玻璃房子就是保护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舱,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身着白色防护服的考古工作者们忙碌的身影。在我的印象中,考古工作者们大多在野外风餐露宿,工作条件很是艰苦,若遇到天气变化,他们就得迅速停下手中工作去保护已经暴露在外的遗迹和文物。眼前的情景与我想象中的考古发掘现场很不一样,大有“鸟枪换大炮”之感。我忙换上防护服、发套和鞋套,进去一探究竟。
↑1986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受限于当时的条件,现场裸露在空气之中,没有被完全封闭保护起来(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4个大小不同的考古发掘舱(2021年3月10日摄)。
彼时,考古发掘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3号“祭祀坑”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青铜器物;4号“祭祀坑”里的玉琮和玉凿也已经露出;5号“祭祀坑”里,考古人员在清理金面具残片;6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在研究论证进一步的发掘方案;附近的7号、8号“祭祀坑”尚处于发掘的初步阶段。我抓紧拍摄着眼前的场景,甚至有些紧张。因为我知道,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眼前所见都不会复现,这些文物在“祭祀坑”中的位置、状态等,无不蕴藏着重要信息,都是值得记录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此时的现场尽可能记录下来。之后,我又去了几次三星堆,那些曾经被泥土覆盖的文物,都露出了它们本来的面目,有的是象牙、有的是青铜器、有的是玉器……尽管只显露出“冰山一角”,依然美不胜收。

↑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尊(上图:2021年3月10日摄;下图:2021年3月16日摄)。

↑在5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在清理新发现的金面具残片(2021年3月1日摄)。
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在考古发掘舱内拍摄的图片受制于现场光线条件,整体气息稍显“冰冷”,所以一直期待能有不同寻常的光线条件。2021年3月16日,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那天下午,我再次来到三星堆遗址计划拍摄,但突然被工作人员告知3号“祭祀坑”要进行三维扫描,无法拍摄。而扫描结束恐怕要到夜里了。当时,央视直播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节目近在眼前,整个考古发掘现场很快就要进入整体清理封闭阶段,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拍摄机会。我心一横:等到深夜我也要再拍一次!我便先到其他“祭祀坑”边继续工作,时不时观察着3号“祭祀坑”的扫描情况。数个小时过去,我发现那边进行扫描的工作人员换了一拨人,所使用的仪器也有所不同。于是,我试探着询问是否能在他们扫描的同时拍摄图片,我得到了允许!而这一次,他们要用高光谱成像扫描仪对新发现的文物进行光谱拍摄,因此需要用一盏合乎要求的灯照亮“祭祀坑”的内部,与以往不同的光线条件也由此出现了!
↑在3号“祭祀坑”,考古人员用高光谱成像扫描仪对新发现的文物进行光谱拍摄,以识别文物的材料和属性(2021年3月16日摄)。

↑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器局部(2021年3月16日摄)。
以上是我与三星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那片神秘的区域就时不时浮现在我脑海,吸引着我想要再去一睹它的“芳容”。
↑青铜顶尊人像(画面左侧)(2021年5月14日摄)。
时间到了2022年,当得知将要公布新一轮的考古发现时,我感到很兴奋,因为之前几轮考古发现都集中在3到6号“祭祀坑”,7号和8号“祭祀坑”始终像是个谜。尤其是8号“祭祀坑”,是这6个坑中最大的一个,其中到底还藏着怎样的稀世珍宝,对我的想象力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与挑战。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提前进入考古大棚拍摄的权限。
↑考古人员在8号“祭祀坑”内工作(2021年3月17日摄)。

↑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左)与考古工作者任俊锋一起清理铜神坛(2022年6月1日摄)。
时隔1年多后,8号“祭祀坑”的象牙层早已被清空,露出琳琅满目的器物层,其中数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而7号“祭祀坑”中发现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 被考古学家称为“月光宝盒”,更是前所未见,引发在场所有人的无限联想。我屏住呼吸,镜头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些稀世珍宝。
↑在7号“祭祀坑”拍摄的龟背形网格状器(2022年6月1日摄)。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猪鼻龙形器(2022年6月1日摄)。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立人像(2022年6月1日摄)。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局部(2022年6月1日摄)。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巨型神兽(2022年6月1日摄)。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龙(2022年6月1日摄)。
在这些珍宝之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8号“祭祀坑”中的铜神坛。在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看来,铜神坛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器物,它描绘的是一个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人对世界的理解。因此在我看来,对这尊神坛的研究,将可能会给三星堆研究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发现。我蹲在8号“祭祀坑”边,不断寻找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条件,随着考古工作者手持小刷子等工具一下一下地清理,从神坛台基上的青铜小人像尚在泥土之中,到整个神坛的造型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我拍摄了大量关于这个神坛的图片。
↑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在清理铜神坛(2022年6月1日摄)。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2022年6月1日摄)。
就在拍摄的过程中,我突然感到整个考古大棚发生了剧烈的晃动,听到头顶的钢架发出大声的异响。手机弹出的信息显示: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地震……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2022年6月1日摄)。
这是此次三星堆采访中我拍下的最后一个画面。之后,我就和同事王曦连夜驱车赶回成都,投入地震报道中。虽然不能继续拍摄三星堆,留下了些许遗憾,但现在每每回看那些画面,心中依然是激动与震撼,久久无法散去。每次当我结束了一天的拍摄,拖着摄影器材箱走出三星堆遗址时,心中都会升起不少感慨。当我或蹲或趴在“祭祀坑”边,通过镜头凝视那些尚淹没在泥土中的文物时,无论露出多少身影,它们无不散发着来自遥远时代的气息与光辉,它们虽然无言地躺在那里,但仿佛想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正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所说,通过三星堆奇特的新发现可以看到,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所表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中华其他区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与它们相对,就是与文明和历史相对,会再次勾起我对一些诸如“我们从哪里来”这样问题的畅想,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这些出自三星堆的文物,它们自身就会成就照片。而我能做的,只是躲在镜头后面,默默“聆听”它们的召唤,轻轻按下快门,并为它们背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所感动与自豪。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拍摄的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2021年9月2日摄)。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从2021年3月三星堆遗址新一轮最新考古成果公布至今,已进行了4次集中发布。我作为摄影记者,有幸参与了其中3次采访拍摄。从青铜顶尊人像到完整的金面具、神树玉琮再到龟背形网格状器和铜神坛,三星堆一件件国宝级文物,都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也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深受震撼。截至目前,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文物层层叠叠,让人眼花缭乱。
↑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左一)在和工作人员交流(2022年6月1日摄)。
相比于我想象中“拿着毛刷和铲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现场,三星堆考古工作的环境和使用的设备,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每个“祭祀坑”都有恒温的透明玻璃室覆盖,考古工作者在里面穿着防护服,操控着各种高科技的考古设备。即便是夏天,考古工作人员在这样“密闭”的室内工作也十分舒适。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面具(2022年6月1日摄)。
由于每次在坑边拍摄的时间有限,我恨不得将“祭祀坑”的每个角落都扫描一遍,除了找到合适的角度拍摄已挖掘出的完整文物之外,也不放过一些大型文物构造复杂精美的局部。这些被填土包裹、丰富多变,精巧绝伦的细节,让我能用相机回溯到这些文物“诞生”的瞬间,也能有机会走近古老的三星堆人深邃遐远的精神世界。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2022年6月1日摄)。
在目前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6月最新公布的铜神坛。铜神坛由低到高分三个部分,底部是带镂空花纹的台基,台基上平台的每一面正中心分别坐着一个人,五绺立发,身着飘带彩衣,脚蹬云头鞋。它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器物,更重要的是它描绘了一个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人对世界的理解。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兽(2022年6月1日摄)。
每一次深入到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穿上头套、鞋套、白大褂时,瞬间就有一种考古工作人员“上身”的感觉。虽然考古工作人员拿的是手铲毛刷,而我手中的是相机,但我们都是与千年文物面对面的一群人,都是整个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记录者、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者。
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在此之前,我和同事已经前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进行采访。
↑在7号“祭祀坑”拍摄的龟背形网格状器边框上的龙首(2022年5月31日摄)。
这是我第一次去真实的考古发掘现场。很多年前,我的理想也曾是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如今,身为记者,从另一个角度去旁观真实的考古发掘现场,感觉既兴奋又忐忑。三星堆本轮考古发掘利用了许多业内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将文物保护前置到发掘现场,因此并不像考古纪录片里常见的露天田野那样,三星堆这里的考古队员是在搭建好的方舱里穿着防护服进行挖掘,看起来很具有科技感。我们也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措施,开始拍摄。
↑在8号“祭祀坑”,考古队员在进行挖掘和记录工作(2022年5月31日摄)。
我几乎想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都装进相机:脚边的深坑里满满都是琳琅满目的青铜器,镜头随意对准的一只,也许就是未来的国家一级文物。每每思及于此,我就忍不住将相机背带在手腕上再绕一圈,心里惴惴不安:可千万不能把相机掉下去了啊。坐在坑边拍摄,偶尔帮考古队员搭把手、递一递头灯、再接过装在袋子里的三千年前的土。看他们一点一点拨开泥土,我的心也渐渐静了下来,用镜头默默观察这历史与现在交织的时光。拍摄完毕回到住所查看照片时才发现,持续一天的“激情式快门”几乎让内存卡都装满了,但也由此让我得以看到许多肉眼难及的细节——被戏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边框上的龙首、神坛上神兽脖子上的铜绳......翻看着照片,那个很久远的“考古梦”终究还是在我内心激荡起了涟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考古队员在谈到他们亲手抚开尘土与那些青铜面具、青铜头像对视时,脸上总会浮现出一种幸福和骄傲。一位考古队员说:“我是三千年后,它第一次‘看到’的人。”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挖掘过程中的铜神坛局部(2022年5月31日摄)。
我拍摄过很多博物馆里的文物,它们总是“亭亭”立于精致的展柜里、“沐浴”在考究的光线下,精美而端庄。而这些七歪八斜随意堆在坑里的“破损”的青铜器,却似乎将3000年的时光真真切切地凝结在了出土的那一瞬间。每每看到自己拍下的这张在泥土中初露真容的神坛,都觉得我和古蜀先民好似只有咫尺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