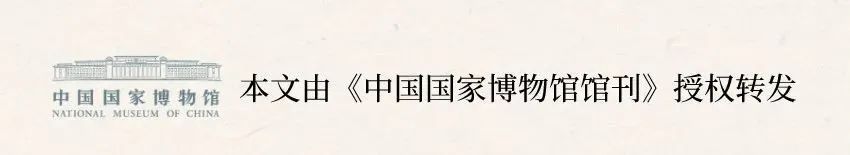书籍资料库
王小文 高心源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21年钜鹿故城出土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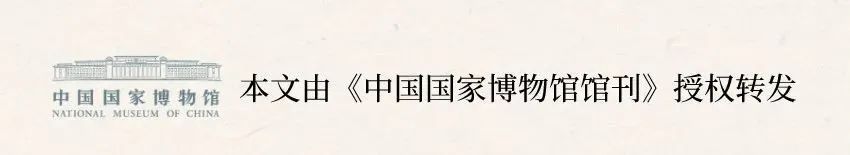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钜鹿出土瓷器是20世纪20年代钜鹿及周边区域盗掘风潮中唯一一批经由考古发掘、流传有序的出土文物。原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1年委派裘善元等人前往钜鹿故城调查、发掘,并获得陶瓷杂器200余件。这批文物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即国立历史博物馆)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的成果,在此后百余年间始终没有得到全面详实的发表。经整理后发现,多数1921年钜鹿出土瓷器为北宋晚期典型器,少数器型可能早到英宗、哲宗之际。此外,出土文物中有小部分为大观二年(1108年)洪灾之后(金元时期)混入之物。1921年7月裘善元等专家的钜鹿之行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发掘了宋代董、王两处民宅,此次工作中引入了地层概念。《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以下简称《记略》)一文中提到“厥土分三层,最上层为地面之浮土,中层为褐色土,最下层为黑焦土”。并且简略说明“共获瓷陶杂器二百余件”[1],此后百余年间,这批文物的整体面貌始终没有全面详实的发表。钜鹿故城遗址出土的“钜鹿器”特别是其中北方民窑瓷器,刷新了海内外对于宋代陶瓷器的认知,直接推动了对于当阳峪窑、磁州窑等一系列北方窑口调查与研究。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2],“钜鹿宋城器物”当时于第二室(发掘品展厅)陈列展览(图一),共计214件,但并未说明是否为全部出土器物,且这一数字尚包括发掘图片等辅助展品,因此可能不够确切。图一 北平历史博物馆内陈列钜鹿宋城展品,采自1930年《图画时报》第634期
通过查阅早期账册可以发现钜鹿发掘品一类中存在大量“一号多件”的情况,举例而言,有中瓷碗1对算作1件、板瓦6件算作1件、崇宁铁钱20件算作1件的现象。另外,当时统计中也将“钜鹿县三明寺碑拓片”“三明寺大悲院碑拓片”“三明寺在钜鹿县之位置图”“钜鹿县图”等辅助展品纳入文物账册。更为重要的是部分器物(特别是王、董二姓碗等瓷器和家具类文物)于20世纪30年代初随故宫文物南迁,这使得实际出土文物数量统计更为复杂。历经20世纪30年代文物南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文物调拨、中国通史陈列未用文物归还原收藏单位等等历史沿革,国家博物馆现藏有1921年河北钜鹿故城出土文物共计103件,其中102件为国家博物馆原始馆藏,1件白釉盖碗为上世纪30年代南迁文物,后于1959年调拨入馆。上述103件文物中共有瓷器20件、陶器15件、石器9件、金属器12件、钱币20件、漆木器5件、骨角器4件、建筑构件16件,另有发掘时采集地面和土层标本各1件。此外,馆内尚藏有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制作的发掘相关地图2幅。现将遗址出土文物报告如下并结合馆藏瓷器进一步探讨“钜鹿器”的年代、面貌与内涵。馆藏钜鹿出土瓷器现有20件,以白釉瓷为多,另有黑釉、青白釉和少量青釉瓷等。馆藏瓷器大多基本完整,少部分残缺者在日伪时期曾进行修复。白釉盖碗 1件,系南迁文物,后于1959年调拨入馆。碗尖唇,芒口,深腹,腹壁近直稍内敛,直圈足,挖足过肩。内底有三处支钉痕。白釉,釉色莹润。胎色近白,胎质细腻。盖呈拱形,边沿上翘,子口内敛,单饼桥形钮,钮的饼突起近圆柱形。胎釉情况与碗相近。底足内有原登记号“左一”“缶”字样。口径12.6、足径5.8、通高11厘米(图二)。图二 白釉盖碗
白釉侈口碗 1件,原名宋瓷碗。碗侈口,尖圆唇,弧腹,高圈足外撇,修足不甚规整。内底有5处三角形支钉痕,较明显。胎色灰白,稍粗。白釉,施化妆土,釉色不甚莹润,内满釉外半釉,土沁明显。口径16.8、足径6.2、高8厘米。内底有墨书原登记号“钜”字、底足内有“左五”“盌”字样(图三)。1.白釉侈口碗 2.白釉侈口碗碗心
白釉唇口碗 1件,原名宋瓷碗。圆唇,口微侈,腹壁斜直,有明显拉坯痕迹,高圈足外撇,修足较规整,内底有五处支钉痕。整器变形较为明显。胎色灰白,稍粗。白釉,施化妆土,釉色不甚莹润,内满釉外施釉近底,土沁明显。口径16.7、足径5.7、高8.3厘米。胎色灰白。内底有墨书原登记号“钜”字、底足内有“左五”“盌”字样。葵花式白瓷碗 共2件,原名宋瓷碗。两碗器型一致,仅尺寸略有差别。尖唇,卷沿,六出葵花式口,腹部略深,曲腹,高圈足微外撇,器身压印六道竖线纹,内底有5个极细小支钉痕。胎呈灰白色,较细腻。白釉,因施化妆土而略显黄色,足部部分露胎。尺寸一为口径12.1、足径4.3、高5.3厘米;另一为口径12.2、足径4.5、高5.6厘米。底足内有原登记号“左四”“盌”字样。白釉瓷炉 1件,原名宋瓷豆。圆唇,直口,宽平沿稍下斜,腹较短,从剖面上看近似正方形,喇叭形高圈足,足上分为多层台,底部外撇,内壁可见拉坯痕迹。胎色灰白,胎质稍粗,较坚致。白釉,局部有细微开片。口径7.6、足径10.5、高17.2厘米。底足内有原登记号“斜二”“豆”字样(图四)。图四 白釉瓷炉
白釉酱斑执壶 1件,原名瓷壶。喇叭形口,长颈,丰肩,长弧腹,腹部隐现拉坯痕迹,由肩部出短流,流对侧为三棱形把手,隐圈足。灰白胎,稍粗。白釉,稍粗糙,施釉近底部,流及把接口处有褐绿色釉装饰。口径10.1、足径6.5、高25.5厘米(图五)。图五 白釉酱斑执壶
白釉瓷瓶 1件,原名宋瓷瓶。侈口,卷唇,长颈,折肩,下腹内收,矮圈足。白胎略偏灰色,较细腻。白釉,施化妆土,较莹润,内满釉外施釉至下腹部,下腹露胎处可见明显修坯痕迹。口径6.2、底径5.2、高15.5厘米(图六)。图六 白釉瓷瓶
白釉四系瓶 1件,原名瓷瓴。敞口微外撇,溜肩,肩部原应有四带状耳,已有1个脱落,下腹内收,平底。胎呈黄褐色,较粗糙。黄白釉,暗淡无光。口径10、底径11、高36.8厘米(图七)。图七 白釉四系瓶
青白釉刻划牡丹纹葵口碗 共2件,原名宋影青瓷碗。两碗形制、纹饰、修补情况均一致,故择一介绍。碗整体粘和修复,敞口,尖唇,口作六出葵瓣式,浅斜腹微曲,圈足浅挖,底足有明显垫烧痕迹,内底边缘有一圈凹痕。器物内壁刻划有精美牡丹纹饰,间有篦划装饰。碗灰白胎,胎质细腻,青白釉釉色较为纯正。口径18.3、足径6.2、高6.5厘米(图八)。图八 青白釉刻划牡丹纹葵口碗
青白釉盖碗 共2件,原名宋瓷盖罐,形制相同。盖覆盆形,叶形纽。碗敛口,尖唇,深弧腹,下部略鼓,高圈足。底足及盖内有明显垫烧痕迹。灰白色胎,胎质细腻,青白釉较莹润。尺寸一为口径11、通高10.8、足径4.5厘米;另一为口径11.1、通高11.2、足径4.5厘米(图九)。图九 青白釉盖碗一对
青白釉瓜棱执壶 1件,原名宋瓷瓶。瓶细喇叭状颈,斜弧肩,瓜棱式斜弧腹,平底,有4块大小不等垫烧痕。瓶颈肩分界处有凸弦纹1道,腹中上部有细线纹5道。瓶口缘、流、把均为20世纪30至40年代修复,其形制与近年景德镇凤凰山窑址所出类似器物差别较大[3]。灰白胎,青白釉较莹润。高23.2、底径8.3厘米(图一〇)。图一〇 青白釉瓜棱执壶
黑釉酱斑碗 2件,原名宋中瓷碗。两碗器型基本一致,仅釉色略有区别。尖圆唇,沿折侈,因烧造缺陷口部呈不规则圆形,曲腹,圈足外直内斜,挖足过肩。两碗胎质一致,均较细腻,略呈黄白色。釉色一为外酱釉内黑釉,内壁以酱斑装饰,外壁近口部似因流釉隐现一圈黑釉;另一为内外黑釉,内壁以酱斑装饰,酱斑较前者少小。外酱釉内黑釉碗,口径13.1、足径4.6、高6.2厘米;内外黑釉碗,口径13、足径4.4、高6.5厘米。底足内均有发掘后所书“左二”“盌”字样(图一一)。1. 黑釉酱斑碗 2. 黑釉酱斑碗碗心
黑釉梅瓶 1件,原名瓷壶。小梯形口,折沿下斜,短束颈,溜肩,长鼓腹,裹足刮釉。棕色胎,较细腻。褐绿色釉,内外满釉,肩部有一圈无釉,应为叠烧痕迹,上腹部似因缩釉导致釉色不均匀。瓶为一次拉坯而成,腹部隐隐可见瓦棱纹。口径6.3、底径12、高35厘米(图一二)。图一二 黑釉梅瓶
黑釉鸡腿瓶 1件,原名瓷甀。直口,宽唇沿,无颈,深腹,小卧足。黑釉,内外满釉,肩部因叠烧而有一圈露胎。腹部有明显瓦棱纹。黑褐色胎,较粗糙,近缸胎。器身有窑粘及缩釉多处。口径4.8、底径7、高26.9厘米(图一三)。图一三 黑釉鸡腿瓶
青釉印缠枝花草纹敞口碗 1件,原名宋青瓷碗。敞口,圆唇,深斜腹微呈弧型,矮圈足,挖足较浅。整器有较明显变形。内壁口部一圈素面,腹部模印牡丹花纹,纹饰饱满流畅,内底部藏一“吴”字款。外壁口部刻划有弦纹一道,腹部装饰不甚规整的密集竖线。灰胎,稍粗糙,青釉微偏黄,釉面有细小杂质。口径24.4、足径6.5、高9.7厘米(图一四)。1.青釉印缠枝花草纹敞口碗 2.青釉印缠枝花草纹敞口碗碗心
青釉碗 1件,原名宋青瓷碗。侈口,口沿外斜,斜弧腹,矮圈足。胎釉与青釉印缠枝花草纹敞口碗近似,土沁明显。口径19.2、高8.7、底径6厘米。共15件,多数较完整,部分灰陶器工艺精良、质地细腻。灰陶瓦纹折沿盆 1件,原名宋瓦盆。灰陶,质地较细腻。直口,卷唇,斜弧腹,平底。外壁有瓦棱纹。高12.8、口径33厘米(图一五)。图一五 灰陶瓦纹折沿盆
灰黑瓦纹陶瓶 1件,原名宋瓦瓶。泥质灰黑陶,质地略粗。侈口,短细颈,弧腹微鼓,平底。腹部有轮纹。高16.5、口径6.6、底径10厘米。小陶罐 1件,原名宋陶罐。夹砂灰褐色陶,器内局部施褐釉,较薄。直口,圆唇,短颈,弧腹微鼓,圈足,足端不甚规整。外壁可见较明显刮削痕。高8.7、口径7.7、足径6.2厘米。灰陶盏托 共2件,原名宋瓦器。灰黑陶,质地略粗。形制相同,尺寸略有差别。敛口,圆唇,中部伸出盘形宽檐,足部内收,平底。底部有拉坯痕迹。尺寸一为高5.4、口径7.8厘米;另一为高4.7、口径7.4厘米。灰陶瓦纹扑满 1件,原名宋瓦罐。泥质灰陶。圆尖顶,鼓腹,平底。顶部有长4.3、宽0.6厘米的长条形孔,下部有对穿的2个圆孔。器身有瓦棱纹。高12.5、底径7.4厘米(图一六)。图一六 灰陶瓦纹扑满
灰陶鼓形器座 1件,原名瓦鼓。灰陶,质地较细腻。口微侈,圆唇,束颈,直腹,平底。颈及腹部有瓦棱纹,颈部有2处空洞,用途不明。高9.6、口径19.7厘米。灰陶簸箕 1件,原名宋瓦簸箕。泥质灰陶,质地细腻。前部似扇形外敞,口呈铲状,后部上翘,内底微凹。内部有仿编织痕迹的小凸起,似柳斗纹,中间有突起脊线两道。长11.5、宽6.5厘米。底部有墨书“程子□先生”及“□□□七月二十三日”字样(图一七)。1. 灰陶簸箕 2. 灰陶簸箕背面墨书
澄泥砚 1件,原名宋石砚。澄泥质地,灰胎表面为黑色。抄手式,内椭圆外方形,砚底挖空,两边作为墙足。长13.5、宽8.1、高2.3厘米(图一八)。图一八 澄泥砚
灰陶觚形残器 1件,原名残瓦器。灰黑色陶,质地细腻,烧成温度较高,质地较坚硬。器物残断,断裂处外撇,器体中部内收,有弦纹一道,足部外撇,平底,底部有密集旋纹,4个小圆孔相对排列。高14.8、底径10.5厘米。底部有原登记号“右五”“残瓦”字样。残陶器 1件,原名残瓦器。泥质灰陶,质地较坚硬。仅存近底一部分,以现存部分看下部收敛,有凸弦纹一道,平底,底部有密集旋纹并6个小孔。现存高7.8、底径9厘米。底部有原登记号“右五”“残瓦”字样。灰黑残器盖 1件,原名宋瓦釜盖。灰黑色陶,外部黑色,内部灰色,质地较坚硬。盖整体近似覆钵型,顶部有直口小柱型纽。通体有明显瓦棱纹。高12、口径4.3厘米。黄彩小陶人 1件,原名宋瓦小人。红陶胎,施黄彩。光头,全身用绳绑紧,绳索共3道,结于前身,腿部也用绳绑紧,结于膝前,双脚有脚环。高8厘米(图一九)。图一九 黄彩小陶人
黑圆棋子 共210粒,原名围棋子。直径约2.5厘米,为一种颜色很深的黑色胎土烧制,无釉。以素面无纹为主,另有少量单面模印纹饰、双面模印纹饰者。纹饰以网格纹为主,未见文字戳记(图二〇:1)。1. 黑圆棋子 2.白圆棋子
白圆棋子 共150粒,原名围棋子。直径约2.5厘米。为类似瓷胎的白色粘土烧制,余与黑圆围棋子近同(图二〇:2)。石研磨器 1件,原名石乳钵。钵呈八角形,上部向内收缩,顶部内凹,下底平。顶部圆形凹面内呈墨色,应为使用时加工痕迹。器壁有密集、杂乱划痕。器底石面较粗糙,未经细致打磨。石捶为八角形,两端有突出圆面,上小下大。通体多处磨损痕迹。整器可见八角中有五角各有1字,另有1角有3字,可明确识读一“好”字,余漫漶不清。外径20.7、内径16.5、捶长15.7厘米(图二一)。图二一 石研磨器
石铫子 1件,原名砂温器。口缘修复把断粘合,器身有裂纹。直口微敛,深腹,圜底。把断面为方形,有流。外壁及外底呈常年过火后的黑褐色,应为实用器。高9.5、把长15.4厘米。石温器 1件,原名砂温器。流残缺,把粘合,器口微残。敛口,深弧腹,圜底。器把雕刻为龙首形状,有流。外壁及外底呈常年过火后的黑褐色,应为实用器。高8.4、把长11.7厘米(图二二)。图二二 石温器
石狮 1件,形作蹲伏状,首微上仰,背贴尾上翘,下有长方形座。石灰岩,制作较粗。高7.3厘米(图二三)。图二三 石狮
石兽 1件,原名石虎。形似虎,作蹲伏状。首前视,首后有多条竖向刻划纹,似长毛,下有长方形座。石灰岩,制作较粗。高7.1厘米。石镇 1件,原名宋石镇纸。盝顶,长方形,下半部微向内敛。一角侵蚀,有轻微剥落。通体磨光,呈灰黑色,密布黑色圆点。高2.3、长5.3、宽3.7厘米。桃形石锤球 1件,原名宋石器。近似桃型,顶尖,底部呈较规整球形。球体有三孔,相互贯通。用途不明,可能原先是作为器钮。高6.2厘米(图二四)。图二四 桃形石锤球
石锤丸 1件,原名石球。近圆形,表面磨光,密布细小黑色斑点,与石镇类似。石磨 1件,有上下两扇,上扇平面圆形两侧外凸,其中一端凸起中有一孔,可能为插入手柄用。顶部下凹呈碗型,其中共三孔,居中一孔较大可能为固定用,两侧两孔较小可能为进料孔。下扇平面呈圆形,表面磨齿分四区刻有密集斜线纹,有磨损痕迹。上扇最长处49、最短处38.7、厚12.5厘米。下扇直径35.2、厚7厘米(图二五)。图二五 石磨
双耳三足铁釜 1件,口沿外侈,双方耳,直腹,足扁平呈长方形,仅一足尚存,圜底。足残断缺,裂,缘残缺一块,双耳残缺一耳剥落。釜底可见明显烟熏痕迹,应为直接置于火上的实用炊器。现存高13、口径34厘米。铜匜形铫子 1件,原名铜炊器。敛口,口沿略宽且外折,圜底,有流。内壁有三半圆形环,原先应做吊挂使用。铜铫底部可见明显烟熏痕迹,应为直接置于火上的实用器,很可能是烹茶所用茶器。现存高9、口径16厘米(图二六)。图二六 铜匜形铫子
铜箸 1件,铜质,长条形,绿锈明显。此箸长而细,且一段较尖细,另一端圆钝,很可能是一件香箸。残铜器 4件,分别为纺锤形残器、残铜片、残铜钩与半圆形铜件,具体难以辨别。铜权 1件,方钮,身圆柱形,束腰,下部为不规则凸起。铜饰件 2件,铜条截面呈方形,两端呈钩状内折,近似C型,两端有小孔,原先可能是某些器物或家具上的把手。长5.2厘米。残铜钗 2件,均只存上半部,锈蚀严重。残长分别为4厘米和4.3厘米。亚字形铜镜 1件,原名葵式镜。圆钮,内区似牡丹纹,狭边,斜平缘。纹饰被红褐色铁锈掩盖,不甚清晰。直径18.8、厚0.6厘米(图二七)。图二七 亚字形铜镜
长命富贵铜镜 1件。桥钮,有“长命富贵”四字,外凸弦纹一道,卷缘。直径11、厚0.5厘米(图二八)。图二八 长命富贵铜镜
铜镜残片 1件,以残存形式看,原先可能是葵式宽沿镜,花纹处锈蚀较严重,可能为龙纹。残长11.5厘米。包括熙宁重宝2枚、元丰通宝5枚、元祐通宝1枚、崇宁通宝10枚、政和通宝2枚。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钱币中有政和通宝铸造于大观二年洪水之后,这批钱币或钱币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出自原《发掘记略》中“其外古钱土坑,亦复痕迹显然”中的古钱坑中。木珠 1件,近似鼓型,一侧平面较小,另一侧较大,中有一孔。直径2.1厘米(图二九)。算盘子为早期引起学界关注的巨鹿出土文物之一,被视为北宋算盘的实物证据。但因只存一件,似不能断定为算盘珠,且就整批钜鹿出土文物面貌而言,在缺乏可靠类型学研究前提下,即使将木珠视为算盘子,也不能排除为晚期地层所出的可能。图二九 木珠
木匙 1件,已残。通体有刮削痕,把呈弧形下弯,勺呈椭圆形,较浅。现存长12.7厘米。木梳 1件,已残。梳背呈半椭圆形,梳齿宽扁呈倒锥形,较密集。梳长10.3、宽5.8、背厚0.9厘米。木箸 1件。一端为方形较粗,另一端较尖。长20.2厘米。残漆器底 1件,原名漆器底残片,原断为两块,粘合修复。木胎。原为内底一侧朱漆,外底一侧黑漆。外底有朱漆书“辛大郎祖铺”,行草字体。“辛”左上尚有一字,未能释读。直径10.3、厚0.7厘米(图三〇)。图三〇 残漆器底
柱状骨把 1件,原名柱状骨器。圆柱形,中有孔,未穿透。有孔一端磨制较光滑,有四道弦纹及斜线纹装饰。无孔一端磨损痕迹较为明显。用途不明,从开孔情况判断,可能是某些器物的把。长7.5、直径1.5厘米(图三一)。图三一 柱状骨把
骨饰件 1件,似扁叶形,极扁平,可能为某种镶嵌饰件。长3.8、厚0.1厘米。蚌壳 1件,长26.2厘米。内部无使用痕迹,用途不明。绿釉琉璃鸱吻 1件,原名瓦鸱吻。残断,两块粘合,仅存头部。胎红色,较细腻。绿釉,有较大片剥落。外观整体做兽头状,雕刻生动。鼻孔贲张,上有反八字形阴刻线。口内上、下各有2个三角锥状獠牙,上部10个、下部6个锯齿状尖牙,长舌上卷,中有压印痕。嘴缘有3至4条凸起的腮肉,腮后腮翅外翻,饰有平行排列的阴刻弧线。双目前视,眼眶明显,眼珠后1/3处有两道圆形阴刻线刻划兽目。双耳在眉角之间,近椭圆形而后部有尖。角贴近头顶,呈S形,角尖上卷,整体极为生动。残高28厘米(图三二)。图三二 绿釉琉璃鸱吻
绿釉陶佛像背光 2块,原名磁制佛光。缸胎,火候较高,胎质坚硬。绿釉较暗,近褐色。以现存形状推测,应为佛背光。中部光平,有四方形孔,外有两条凸起线构成一凹槽,其上饰灵芝草,草间另有纹饰难以分辨。外层为火焰形纹饰。长87、宽46厘米。回纹滴水瓦 2件,两瓦形制接近,唯前端装饰稍有区别。泥质灰陶,表面较平整仅个别处有残留布纹。瓦长方形向上弯曲,前端下折。其一前端装饰为水波形,有凸条纹1道,条纹上下各有方格纹。另一前端装饰为弧形,印有回纹。一件长38、宽25.4、厚2.5厘米;另一件长37、宽22、厚2厘米(图三三)。图三三 回纹滴水瓦
板瓦 共6件,形制接近,仅大小有别。泥质灰陶。长方形,有弧度,下面光平,上面一端有布纹,其余部分尚光平。在一边缘中间有凸出小块,可能是固定瓦所用。大者2件,长37.5、宽27.5、厚约2厘米;小者4件,长29、宽19.5、厚1.6厘米。莲花纹带当筒瓦 1件,原名瓦当。泥质灰陶。内面有布纹,一端有子口,一端有圆丸当,瓦当面为莲花纹,外有凸起弦纹一道。长31、宽15.5、厚2.2厘米,当直径15.2厘米(图三四)。图三四 莲花纹带当筒瓦
兽面纹瓦当 1件,原名瓦当。泥质灰陶。圆丸当,面作兽首形,周身饰水波纹,外有一圈连珠纹,外层素平缘(图三五)。图三五 兽面纹瓦当
筒瓦 1件,泥质红陶,半圆形,内面有粗布纹,外面原先似有绿釉,大部变为银白色或灰绿色。一端子口,一端母口。长32.2、宽15.3、厚2.2厘米。长方形砖 2块,素面,形制相同。长42.5、宽24.6、厚5厘米。木房梁 1段,表面龟裂。长160、直径22.6厘米。土 3筐,即《发掘记略》附录中“厥土分三层,最上层为地面之浮土,中层为褐色土,最下层为黑焦土”的实物证据。因年代久远,土已胶结均呈土黄色(图三六)。图三六 出于不同地层的三筐土
地图 2幅,分别为钜鹿县图及三明寺在钜鹿县城之位置图。两图均以光绪《钜鹿县志》所载舆图为底本,绘制规整,但囿于原图所限,仍保留县志中县城南北短、东西长的比例,与县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但从图中我们仍能辨认出王、董二姓住宅的发掘地就在明清三明寺西墙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钜鹿出土瓷器是20世纪20年代钜鹿及周边区域盗掘风潮中唯一一批经由考古发掘、流传有序的出土文物。但囿于时代限制,相关发掘工作不尽科学。虽有对自然地层的初步关注,却并未能确指文物出土层位,因此需要对这批文物中部分典型器物年代做系统讨论。白釉盖碗胎釉精良、做工精细,为磁州观台窑仿定器物中的佳品[4]。类似器物在窑址见于第二期前段、后段(即宋神宗熙宁以后至金海陵王以前),可做参考。这件器物于20世纪30年代因应时代局势随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相关文物南迁,至1959年复由南京博物院调拨入馆。葵花式白瓷碗造型与磁州观台窑XA型白釉碗较为接近[5],这类器物在观台窑第二期前段、后段均有烧造,尤以二期后段即北宋晚期较为普遍。但观台窑所烧花口碗多为垫饼支烧,垫饼绝大多数为三足,五足者极少,且支钉痕鲜有如此细小者。结合支烧工艺与胎釉情况,不能排除这是两件白瓷碗河北其他窑口甚至山西地区产品。白釉瓷炉与磁州观台窑XIV型1式炉基本一致[6],发掘报告认为这种形制的炉年代为第二期后段即北宋徽宗朝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到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这一断代应是比较可靠的。黑釉酱斑碗造型与磁州观台窑VII型1式黑釉碗较为接近[7],这类器物在观台窑第二期前段、后段均有烧造,以器型论可能早至北宋英宗、神宗时期。需要指出的是,这件黑釉酱斑碗胎质稍粗、胎色稍深,也不能排除是周边窑口仿烧产品。黑釉梅瓶与磁州观台窑VII型1式黑釉瓶造型基本一致[8],这类器物自第二期前段(宋神宗熙宁年间)出现,持续烧制到第三期即金代中后期。另外磁州彭城窑也曾烧造同类器物。青白釉刻划牡丹纹葵口碗与景德镇湖田窑Aa型侈口碗基本一致,发掘报告指出这是湖田窑三期后段[9],即北宋徽钦二朝新出器型。同型器物在湖田窑第四期仍延续生产,但综合考虑此碗釉色莹润、发色纯正,比较接近北宋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此碗口部有一近半圆形残片为脱落后粘合修复,残损处下部有长短不一冲口三道,断裂两侧及冲口处有密集金属锔钉痕迹(图三七)。据文物账目记载:“锔印出土时即有,可能为宋时所锔。”图三七 青白釉刻划牡丹纹葵口碗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钜鹿出土的青白釉碗是较为少见的出土于汉地农耕生活区平民生活遗址的锔补瓷器实例,特别是馆藏两件青白釉碗均有锔补痕迹,这种修补无疑体现出使用者对青白瓷的偏爱。青釉印缠枝花草纹敞口碗与合葬于北宋哲宗绍圣元年的冯京夫妇墓所出I式碗[10]、宝丰清凉寺汝窑址所出豆绿釉印花碗[11]基本一致,推测为北宋晚期临汝窑产品。白釉四系瓶是典型金元时期器型,产量极大,北方大小窑口均有生产。这件器物的存在说明1921年的发掘限于当时技术条件,对地层控制并不精细,混入了大观二年洪水以后文物。国博钜鹿发掘品中尚有2枚政和通宝也可说明这一事实。长命富贵铜镜则与上海明墓出土明镜类似,年代可能晚至金元以后[12]。总之,多数1921年钜鹿出土瓷器为北宋晚期典型器,少数器型可能早到英宗、哲宗之际,但也可以确定钜鹿出土文物中有小部分为大观二年洪灾之后(金元时期)混入之物。因之,对于钜鹿出土有明确墨书器物、木桌椅等可视为北宋末期重要纪年文物,但算盘珠及其他一些形制变化不明显或研究尚不充分的文物不宜一概认定为北宋标准器。通过整理可以确认,钜鹿故城中瓷器来源较为复杂,磁州窑产品在其中占据优势,也存在较为高档的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河南临汝窑仿耀州窑青瓷。与此同时,部分传统上被归为磁州窑的白釉、黑釉器物在工艺细节、胎釉特征上与典型磁州窑瓷器存在一定差别,不排除是河北其他窑口或山西、河南地区产品。钜鹿出土瓷器的多元窑口与丰富面貌,无疑记录了宋代制瓷业的高度繁荣,展现了当时北方民窑的激烈竞争,反映了繁荣的民间贸易交流。国家博物馆藏1921年钜鹿出土文物来源可靠,但年代上并非全为大观二年洪水之前产物,需要注意有后期混入文物;相关瓷器窑口绝不拘泥于磁州窑及周边地区窑口,还有湖田窑青白瓷、临汝窑青瓷及可能来自山西、山东窑口的器物;未来,对于钜鹿宋城遗址的深入发掘与阐释,必将大大推进宋代陶瓷器使用功能、社会属性、审美价值的研究工作。[1]佚名:《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年1册。
[2]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93页。
[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浮梁县博物馆:《江西浮梁凤凰山宋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
[4]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52、261-262页。
[5]同[4],第188-190页。
[6]同[4],第110页。
[7]同[4],第59页。
[8]同[4],第214-215页。
[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编著《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80、469页。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2]何继英:《上海明墓出土“长命富贵”铜镜》,《上海文博论丛》第6辑。
作者:王小文 高心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4年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