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付承章丨《唐代金银器研究》述评
《唐代金银器研究》述评
付承章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2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齐东方教授著《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此书早在1999年5月就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唐研究基金会丛书”一种),是我国近年来隋唐考古、古代物质文化史和丝绸之路研究等领域的杰出成果。时隔二十多年再版,虽然在内容上难作大的改动(参看再版后记),但今日重读,觉得书中一些观点仍有其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参考。
众所周知,金银器因其原料珍贵、制品精美、社会地位显赫,往往为其他质地器物所不及。而在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史上,唐代可称之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重大变革时代。一方面,唐前期金银器集前代金银输入品之大成,体现出多种文化的融合,后又逐渐摆脱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日益凸显出本土化的特色;另一方面,金银矿的普遍开采为金银器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中央、地方及私营的金银器作坊在唐中叶之后趋于齐头并进,使得唐代金银器的造型、纹样、制作工艺进一步多样化,为后世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唐代金银器研究》的序言部分不难看出,作者立足于考古学分期、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对其发展过程、来龙去脉及文化渊源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唐代金银器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书由三编组成,每编七至八章不等。第一编《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共分七章。第一章简要记述了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作者首先按照遗迹的性质对考古出土的金银器加以梳理,并对俞博(Bo Gyllensvärd)、马尔萨克(Б. И. Маршак)、桑山正进、韩伟等学者的研究作了独到的评述,指出过往研究在材料运用、年代分析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以下二至五章是关于唐代金银器的基础性研究,目的旨在从考古学的角度准确考订出每件器物的制作或流行时间。第二章梳理了唐代金银器中所谓的标准器物及标准器物群,为器物的比较分析乃至断代提供了清楚的年代参考。第三至五章则分别从器物形制、纹样特征入手,将唐代金银器皿的发展变化分成飞速发展时期(唐代8世纪中叶以前)、成熟时期(8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普及和多样化时期(9世纪),并与历史发展相联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第六章,作者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唐代金银工艺进行了分析,这是金银器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一编的最后一章是对唐代金银器所作的区域性研究,作者探讨了带有特殊风格且能够显著反映社会背景变化的南方地区金银器,认为唐代金银器的南北差异主要出现在中晚唐时期。
第二编《金银制造业的发展》亦有七章。前三章主要是按汉、北方民族和西方系统对唐代以前的中国金银器所作的全面论述。作者将唐代金银器纳入到中国古代金银器发展史的框架之内,目的在于对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有所明确,其结果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唐代金银器所处的发展阶段。例如,8世纪中叶以前的唐代金银制造业受外来影响最为强烈,反映在唐代金银器中出现了大量带有域外风格的仿制品,这种现象的存在多少与南北朝时期输入的域外金银器有关。因此,对唐代以前外国输入的金银器加以梳理,有助于明确输入品与仿制品的差异,从而对唐代金银器中的“西方特征”“唐代创新”有更清晰的认知。
第四至七章是对唐代金银器兴盛原因的深层探讨。一方面,社会上层对金银器物的喜好及其引发的进奉、赏赐之风,为唐代金银器的制造发展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金银采矿、冶炼、征收、作坊等整套完备组织和制度,是唐代金银器得以蓬勃发展的保证。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外来金银器的输入对唐代金银器物制造所产生的刺激作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器物形制、纹样装饰及制作工艺的多样化上。
第三编《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为全书最具特色的重点内容之一,共八章。第一章是将“外来文明”细分为萨珊、粟特、罗马—拜占廷三个系统及其他文化因素,作者并未对不同的系统加以严格定性,而是特意强调了各个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合,显示出作者对国内外相关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情况是颇为熟悉的。例如,马尔萨克早在他1971年出版的《粟特银器》(Согдийское серебро,Москва,1971)一书中就指出了粟特同萨珊、拜占廷艺术的关系;又如,美国学者冈特(Ann C. Gunter)和杰特(Paul Jett)在《塞克勒和弗里尔艺术馆藏古代伊朗金属器》(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中论述了部分萨珊器形的罗马源头。作者之所以能够敏锐地注意到不同系统金银器之间的关系,正是得益于对上述材料的充分参考。
粟特银器与唐代金银器的关系最为密切。以下四章,作者不惜笔墨,详细讨论了粟特银器输入中国、并与唐代金银器相互借鉴的过程。其中尤为突出的贡献,是对李家营子、沙坡村、西安西郊出土银器的个案研究。过去,研究者多将它们归入唐代银器的范畴(如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30—32页)。作者广泛征引国内外的相关文物资料,并结合对遗迹性质、交通路线、传播人群、历史背景的考察,认为这几件银器均为粟特银器,极具创见。而在探讨粟特与唐代金银器的关系时,作者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通过分析数件碗、盘、带把杯的风格归属,对马尔萨克所制图表中涉及粟特银器与唐代的关系部分作了较大调整,这一调整往往为学界所忽视,但却是作者研究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萨珊、罗马—拜占廷系统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在第六、七章中,作者分别以多曲长杯、高足杯为切入点,考证了唐代金银器与这两个系统的关联。纵观以往研究,诸如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218—223页)、桑山正进(《一九五六年来出土の唐代金银器とその编年》,《史林》第60卷第6号,1977年,77—79页)等学者都对相关问题有过重要论述。作者则在充分吸收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就特征演变、传播过程等方面作出了相当程度的推进。例如,孙机曾认为萨珊长杯均为横向“分层”式,而作者利用其掌握的资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合理的修正。
本编最后一章是对唐代墓葬壁画中的金银器皿加以辨析,指出唐墓壁画中描绘的一些器皿与西方器物关系密切,且已成为高官贵族生活中的日常用具,这对于探讨唐代金银器的使用方式、适用人群等问题颇有裨益。
唐代金银器毕竟是个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本书的学术价值虽然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但可以商讨的问题也仍然存在,特别是涉及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的关系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东西方学者多年来对相当于唐代及稍早的外国金银器研究有不少贡献。本书作者虽然参考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但对于萨珊、粟特银器的关注往往只局限在波普(A. U. Pope)的《波斯艺术综述》(The Survey of Persian Art,New Edition, Ashiya, 1981)和马尔萨克的《粟特银器》当中。以下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1. 第二编第三章讨论唐代以前外国输入的金银器时,认为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银盘属萨珊器皿,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银碗为印度或伊朗东部作品,但这样的判断显然有待商榷。就前者而言,除了作者提到的夏鼐、马雍(参看《文物》1983年第8期,5—12,39页)的论文外,至少还应参考美国学者哈珀(P. O. Harper)的研究(“An Iranian Silver Vessel from the Tomb of Feng Hetu”,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4, 1990, pp.51-59)。就后者而论,马尔萨克(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 Metallkunst des 3.-13.Jahrhunderts und ihre Kuntinuität, Leipzig, 1986, p.245)和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146页)都认为这是一件受到粟特或萨珊影响的中国制品,但他们的观点并未得到作者的关注。
2. 第三编第一章除了提出与唐代金银器密切相关的三大域外系统之外,还提到了印度、贵霜—嚈哒和大食文化因素。例如,作者认为何家村莲瓣纹弧腹银碗上的尖瓣装饰与嚈哒器物的装饰意匠接近,故有贵霜—嚈哒之说。由于没有利用马尔萨克在《东方银器:3—13世纪的金属工艺及其后的发展》(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Metallkunst des 3.-13.Jahrhunderts und ihre Kuntinuität, pp. 29-36)中对相关器皿的考证,导致作者对该问题的论述较为薄弱。据马氏研究,嚈哒银碗上的装饰布局应该是吸收了萨珊特征。因此,嚈哒器物是否曾对唐代金银器产生过影响,还需要仔细研究。同样,对于所谓大食文化因素,作者并未举出任何关于唐代金银器受到阿拉伯影响的例证,致使这一推测显得牵强。实际上,大食金银器皿在发展初期应属“后萨珊金属器”,英国学者格雷(Basil Gray)对此早有梳理(“Post-Sasanian Metalwork”,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5, 1991, p. 59),值得重视。
3. 第三编第五章关于唐代金银器对粟特银器的影响问题,是作者试图在本书中予以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其中,作者认为粟特带把杯中出现的桃形双重花瓣装饰是受到了唐代带把杯的影响。这个看法与马尔萨克对粟特银器中流派C的划分不谋而合,当无争议。但作者据此将圜底碗形杯体看作是7世纪至8世纪唐代的创新形制,则不尽然。据笔者所知,深井晋司(《ペルシアの古陶器》,株式会社淡交社,1980年,216页)和马尔萨克(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Metallkunst des 3.-13.Jahrhunderts und ihre Kuntinuität, pp. 85-88)在各自的论著中都曾列举过多件带有萨珊、粟特风格的圜底碗形带把杯,其年代或有早于唐代带把杯的情况。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李家营子银器“很可能是旅行者弃藏的遗物,所有器物的年代、来源应是相同的”(322页)。考虑到金银器是丝绸之路贸易中常见的奢侈品,笔者认为不应将其来源问题作简单化处理。例如,孙机曾赞同作者对胡瓶、圆盘、椭圆形浅杯的来源判断,但认为其中的折肩银罐属突厥特有(《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263—268页)。再以李家营子出土猞猁纹银盘为例,作者认为这件银盘为粟特地区产品,但文中所举例证或为带有萨珊风格的粟特银盘,或为与萨珊银碗装饰相近的花剌子模银碗,不具有代表性。实际上,在盘心饰动物、周围留出空白的作法更流行于萨珊银器(参看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p. 139)。另外,萨珊和粟特银器上虽未见猞猁的形象,然波斯人最善于调教猞猁。波斯语中又用siyāh gōš一词指代“猞猁(黑耳朵)”,其读音接近婆罗钵语šagr(狮子),而非粟特语šrwɣ(狮子)。可见,李家营子猞猁纹银盘亦有可能产自伊朗。
本书附有详细的英文摘要,内容涉及撰写缘由、资料选取、主要创新等,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国外学者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与利用,且翻译较为准确、流畅,值得表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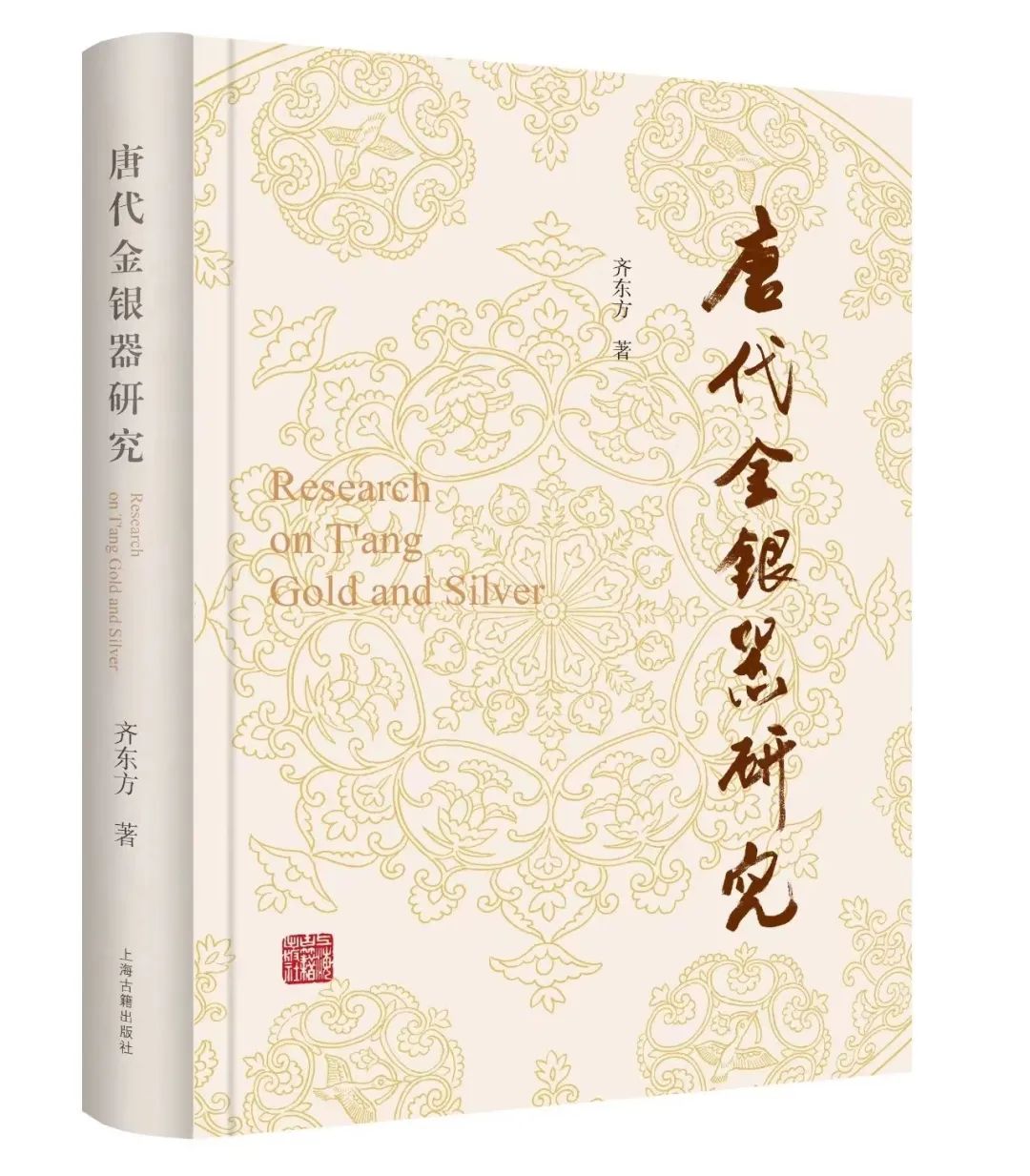
编者按:原文引自付承章:《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三十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23年,页195~199。(待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