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徐维焱丨黄文弼早年学术与实证主义
黄文弼早年学术与实证主义
徐维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引言:实证主义进入中国
实证主义(Pragmatism)兴起于19世纪中叶,其内涵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也注重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实证主义的奠基人是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他的学说成熟于19世纪30年代,而半个多世纪以后,严复通过译介西方的科学、哲学著作,将实证主义引入了中国。严复是清末新学的代表人物,他把实证主义概括为“实测内籀之学”,提倡通过“实测”个别现象,“内籀”总结出普遍规律。此后的数十年,实证主义在中国迅速找到了适合生长的土壤。在实证主义的原旨之中,形而上学应当被摒弃和批判,然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哲学家王国维、胡适等人都曾努力地在科学方法和形而上学之间寻找平[1]。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急于中国寻求出路,对自然科学无比渴求,同时也是由于“格物致知”和乾嘉朴学的经验主义传统所提供的思想基础。
在东西思想交锋和融合的旋涡中,青年黄文弼也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之路。从早年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到后来为人称道的考古学研究,黄文弼的学术转型中体现出了实证主义的取向。虽然黄文弼本人在学术论著和访谈中都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实证主义作为一股强劲的思潮,对五四前夕的中国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几乎所有接触过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都免不了受到实证主义方法的洗礼。在黄文弼早年的著作中,实证主义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哲学思想的改良和应用,二是在考古学、民俗学的领域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科学方法。
一、黄文弼早年改良主义的哲学研究
黄文弼于1893年生于湖北汉川,十五岁考入汉阳府中学,中学期间的黄文弼对当时的经学大师刘师培无比崇敬,一度梦想能够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亲耳聆听其教诲。1915年,黄文弼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产生了兴趣。大学时期的黄文弼首先被佛学所吸引。从刚入学开始,他就经常和顾锡五结伴前往广济寺,听取张克成讲课,风雨无阻 [2]。但黄文弼并没有在佛学之路上走得太远,而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知识。五四之前的北京大学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和兼容并包的精神。在沙滩红楼的校园里,黄文弼开始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北京大学哲学门开设的课程涵盖了东西哲学,包括希腊哲学、逻辑学史、伦理学史、近世心理学、社会哲学史等。黄文弼的主攻方向为中国哲学,选修了中国名学钩沉、儒家玄学与二程学说三门课程,其授课教师分别为胡适、陈汉章和马叙伦 [3]。在三门课程上,黄文弼完成了《孟子政治学说释评》《二程子哲学方法论》等文章,这是他哲学研究的试水之作,体现出敏锐的思辨能力和重视实证的精神。在《孟子政治学说释评》中,黄文弼表达了对于孟子治国理念的理解,以及对当时中国政治改革方向的构想。在阐释孟子的观点时,黄文弼并不盲从权威,而是直接向自己的老师胡适发起了挑战。在《中国哲学史》里,胡适将孟子的政治理念概括为“妈妈政策”,相应的,孔子的理念则是“爸爸政策”。所谓“爸爸政策”即“父性政策”(Paternalism),强调教化与道德;“妈妈政策”即“母性政策”(Maternalism),重视满足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欢愉。在胡适看来,孟子不谈论孔子的“仁义”,而是将其发展为“仁政”,其含义便是“乐利”,是向百姓布施恩惠,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求。黄文弼对胡适的论调不以为然,他认为,孟子的核心诉求是人道主义,平均土田、开放利益都是实现人道主义的途径,而非最终目的:
而第六事(人道主义)则为其目的之所在也。欲增进人道,非土田平均不可,此为孟子唯一主义。故对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不惮再三言之,岂如某氏所云,孟子为“妈妈政策”哉[4] ?
此番言论在旁观者看来显得夹枪带棒,而事实上,学术观点的分歧并没有影响黄文弼对业师的尊重。黄文弼在毕业之后曾多次登门拜访胡适,关系十分融洽。胡适在日记里写道:“黄文弼君送我一部罗钦顺的《困知记》,嘉庆四年补乾隆二十一年翻明板刻的。黄君有志搜罗陆、王一派的遗书,已收得王心斋集与莫晋刻的《王龙溪集》,他今天来借我的明板《龙溪集》去校勘了一次。”[5]而在整体认知方面,黄文弼认为,孟子的政治哲学与伦理观念紧密相连,可以称作“政治伦理学”。孟子将国家分为人民、土地和政事三个要素。执政者不仅要对人民施以恩惠(黄氏称为“保民主义”),还要尊重人民追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权利。“与民同乐”的主张更是接近于当时最为先进的“民主主义”。虽然人民仍旧归附于君主和政府,但却不是胡适口中“衣帛食肉”的附庸,而是能够在政治上能够发挥主体作用。对于土地,孟子主张恢复井田、泽梁无禁,实行“均田主义”,同时提倡“关市讥而不征”,保障商品和财富的流通。政事方面,应当任用能臣贤士,即所谓“尚贤主义”。黄文弼同时注重孟子政治学说的现实意义。与现实问题相关联的过程,也是“实证主义”的另一分支——“实用主义”的具体表现。针对土地和财产问题,黄文弼从“文王治岐”中的井田制度中提炼出“限产主义”的主张。黄文弼意识到,以“绝对平均主义”主要思想的井田制会催生惰性,阻止社会的流动和发展,但另一方面,放任土地兼并又会带来流民、战乱、饥荒等问题。为了在二者中寻求平衡,黄文弼主张政府应当抑制过分的财富集中,采取调查、组织、均计等方式,使地方豪强“财产不过百万、田亩不过百顷”,既能保障社会活力,也能避免危及百姓的生计。在哲学门期间,黄文弼的另一篇课程习作是《二程子哲学方法论》,此时的他仍然沉迷在佛学之中[6]。1923年,黄文弼将旧稿作为前半部,再行增补,并更名为《明道与伊川之哲学及其方法》,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次年,又重新改回原名,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此文主要探讨程颢、程颐二人的哲学思想,较少关注现实问题,故本文不再多及。1918年,黄文弼以乙等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进入创建之初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担任助教,开始整理古籍,他的主要成果是校勘《太平御览》。次年,黄文弼参与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工作,并在实践中编写了《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在文科研究所里,黄文弼的另一项研究是《文心雕龙》。为此他经常求教于黄侃,并与黄侃的学生黄建中过从甚密。1925年,黄建中赴英国留学,黄文弼因而委托他从不列颠博物馆东方图书馆晒印敦煌写本《文心雕龙》残卷[7]。此时的黄文弼肯定没有想到,数十年后,自己会因为一部子虚乌有的“《文心雕龙》唐写本”而被卷入一场暴风骤雨之中[8]。有学者指出,正是文科研究所的工作经历,促成了黄文弼从传统哲学向实证研究的转型[9]。
二、全面抗战初期西北联大与四川大学治学环境对比
1920 年,黄文弼又在《唯是》上发表《中国婚制研究》,这篇文章在黄文弼的学术历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相较前揭两篇课程作业,《中国婚制研究》从材料、方法等各方面都显得更加成熟,展现出了扎实的文献功力和严谨的研究态度。更重要的是,黄文弼采用了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19 世纪末,以严复《天演论》的译介为先导,林纾、魏易翻译德国人哈伯兰的《民种学》(原名 Volkerkunde,即《民族学》)为开端,人类学正式进入中国。在吴定良等先驱者的推动下,人类学的观察方法与中国丰富的传统文献和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开启了本土化的进程。《中国婚制研究》采用了人类学标志性的观察法,并且运用了田野调查的成果。首先,黄文弼对比了中外各地的不同婚制,并将其分为家族式、宗教式、法律式三类:
世界婚制可分数类,自仪式言之,为家族式、宗教式、法律式三种。若中国、日本、朝鲜皆行家族式者也……宗教式者,欧美诸国皆然……再自其态度言之,行家族式与法律式者,仪式多繁重而尚礼节。行宗教式者仪式多简约,以男女之爱情为主。家族式与宗教式态度虽不同,各以地理历史之关系而异,本无可轩轾于其间也。
3年由钱智修翻译,题为《世界婚制考》,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黄文弼采摭了华屈德的部分调查,放置于《中国婚制研究》的附录部分,作为中外对照的坐标。在观点的层面,《世界婚制考》中屡屡提及家族、宗教及法律的作用,不难看出,黄文弼的“三分法”也是受到了该文的直接启发。例如,《世界婚制考》说道:“日本人结婚,通常无法律及宗教之仪式”[10];《中国婚制研究》则曰:“中国、日本、朝鲜皆行家族式者也”。[11]另外,黄文弼研究也并非都是舶来品,也有部分来自传统的典籍和民俗材料,客观上说,这也是人类学方法中国化、本土化的一种实践。例如文中提到的苗人与黎人的婚俗:
东方苗族之结婚亦类此。苗童之未娶者曰罗汉,苗女之未嫁者曰观音,皆髻插鸡翎,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而归,然后议聘。聘用牛羊,牛羊必称双数。闻之琼州土人言黎人,结婚亦如是。殆古俗未化者欤?[12]
此说出自于《峒溪纤志》:“苗童之未娶者曰罗汉,苗女之未嫁者曰观音,皆髻插鸡翎,于二月群聚歌舞,自相择配,心许目成,即谐和好。”[13]和《孟子政治学说释评》类似,《中国婚制研究》的落笔仍旧是现实。黄文弼主张改良中国的婚姻制度,废除童婚、门第和奢侈的制度,以男女自由恋爱为基础,同时以家族、法律作为准绳。在国家层面,政府也应适当介入,统计适龄男女的数量比例、健康状况,并提供法律保护,拒绝来自双方家长的干预。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着眼,《中国婚制研究》都可以被视作黄文弼历史研究科学化和实证主义中国化的开端,这种方法一直伴随他终生。1924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研究室和古物调查委员会更名为“考古学会”,黄文弼也开始向考古学之路迈进。据他的终生好友顾颉刚所言,当年黄文弼就已经和在他谈论考古学会的前景:“仲良招至考古学室,谈研究所发展计画。”[14]1926年,考古学会从古董商人手中购得来自稷山县小宁村兴化寺之南壁的59方壁画,引起了包括叶瀚、马衡在内的金石学家的重视。在当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的“考古学专号”上,黄文弼发表了《山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考证这批壁画为元人所绘,其七佛名称分别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与释迦牟尼佛,对其余的声闻、菩萨、天人等像,黄文弼也一一考证其名相。这篇文章也显示出黄文弼不同于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重视田野调查和收集一手资料,这是考古学和金石学的重要分野。在研究这批壁画的过程中,黄文弼虽然没有亲至其地,却通过李济的实际探访了解到壁画的原始形态,从而确定其具体位置和准确年代:
今夏清华教授李济之君,亲至该寺,调查佛像。见所绘壁画,尚有未剥离者。后院北墙并题有“时大元国岁次戊戌仲秋蓂生十四叶□工毕”诸字。按元有三戊戌,一为太宗十年。一为大德二年,一为至正十八年。太宗时尚无国号,此直题大元国岁次戊戌,疑为太宗时所绘也。
……
今所绘既为佛菩萨之像,是必绘于内院者。如李济之君所云,益信此说不诬。据云,该寺有三院……[15]
其次,黄文弼还为佛教图像的形态演变建立了谱系,这也是考古类型学的题中之义:唐代所绘菩萨像,与元代所绘其装饰虽相同,而姿态则稍异……是佛菩萨飘逸之姿,出于印度。今观印度古时,造像与唐画多同。至元代梵式西来,乃趋于严谨……至所绘容貌,唐与元亦不同……总之,唐画缛丽,元画精巧,各臻其极也[16]。
以《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为发端,黄文弼的考古学事业开始走向成熟。1927年,黄文弼参加了“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既是黄文弼学术生涯的里程碑,也是他一生之中的高光时刻。5月9日,黄文弼与中外团员一行27人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踏上了长达三年多的蒙新考察之路。在内蒙古,黄文弼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陶器、文书、碑刻,先后探查了姥弄苏木(今敖伦苏木遗址)、秦汉长城、黑流图汉代兵营、额济纳河、天仓古堡等遗址;在新疆时,又单独率队考察了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罗布淖尔地区,寻访了明屋遗址、龟兹古城、克孜尔千佛洞、喀拉墩遗址等重要的考古地标,为后来“三记两集”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7]。除了考古成果外,黄文弼还注意记录当地的民情民俗,他的调查不仅十分详细,而且具有体系性,颇具人类学家之风。这一点在与其他团员考察日记的对比中更加明显,例如徐炳昶《西游日记》、斯文 · 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袁复礼《蒙新考察五年记》、贝格曼《新疆考古记》,以及新近面世的《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等。与其他团员相比,黄文弼并不满足于考察途中的耳闻目见,而是常常主动询问牧民、喇嘛等居民和过路的商人,以便了解当地和周边人群的饮食、服装、婚礼、葬仪等情况。例如,通过《蒙新考察日记》中对内蒙古、新疆等地蒙古族婚俗、葬俗的部分记录,可以看出黄文弼过人的专业程度:
1927年8月26日
乌拉蒙人婚丧仪节,犹沿古昔。据云,若育女子至长未嫁,而有孕生子,乃向蒙古包前马桩上叩头,意以为与马桩配婚。倘有外人骑马至,即系马于桩,当系马时,必合抱其桩,义取于此地。婚前男先至女家,与女同回男家,拜马桩,又拜来宾,即成婚姻。丧事,人死后即用马挽至荒野,遗弃地点,先由喇嘛勘定。当弃时,喇嘛念经、孝子在后。如弃时仰面,则子孙大笑,以为先人升天堂。如俯面,则以为入地狱,乃大哭。弃后三日,如鸟兽未食,以为此人罪恶甚大,复请喇嘛念经。必至兽食尽而后已[18]。
又如:
1928年8月10日
又调查维民风俗……婚礼极简单,当女至十二三岁时,男至十五六岁时,即结婚。男家为女家作一身新衣、一头羊。及期,女家送至男家,有阿訇为之证婚。阿訇先向八郎子说,你愿娶她吗?答:愿娶她。又问女方,你愿嫁他吗?答:愿嫁他。乃以面包一个,分为两半,沾盐少许,各食一块即散。娶妾之风亦甚,女子无生育即重娶,仪与前同。奴婢以钱买亦可,约在百两左右。贫家致有赠送女子作奴,不取分文者。夫妇不和亦可离异,惟在6个月内所生之子,应归原夫[19]。
而科考团的其他成员或因专业隔阂(如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记》[20]等),或因事务繁多(如徐炳昶《西游日记》),在这方面的记载较少。刘衍淮记载有询问之事,但多为只言片语:
1927年8月20日以后铜匠之配钥匙者来了,问了他些关系风俗的事俗。他说:此地蒙古人不大与汉人通婚,套里蒙人能与汉人通婚,大半为汉人所同化[21]。1928年1月4日蒙人婚姻,早者十五六岁时,迟者廿上下,夫妇年龄多是男比女大个一二岁,间有同年者,女长于男者无。夫死,妻多嫁其夫之兄弟,弟多兄少,有子女者多不能嫁,夫妇不和,则找媒人说可离异,婚姻多定于父母,倩冰人说合之,男家向女家拿聘礼,多寡不等,视女家之贫富而定。兄弟皆有妻室,不能同居一室——或蒙包——平常弟妇在兄面前就不能脱靴子。遗产长子所得恒优异,承继法一如汉人[22]。
遗憾的是,黄文弼并没有为这些田野调查成果发表独立的论文或专著,仅有1930年的一次演讲略及一二。当年9月,西北科考团第一阶段考查结束,黄文弼应北京大学校长之邀,为全校师生介绍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辉煌成果。由于考古资料未遑整理,他主要讲述了新疆的民族分布情况,包括蒙古、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族)、缠族(维吾尔族)、甘回(回族)和汉族的历史沿革、分布现状、生产方式等,部分涉及文化、信仰、文字等问题。同年11月,该演讲稿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除此之外,黄文弼也有意识地将人类学方法运用在考古学研究中。在1943年发表的《考古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中,黄文弼对考古学和其他相结合方法做出了总结:“考古学为新兴之科学,包涵以往人类全部活动之遗痕,其范围至为广大。则其关涉于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者必多。”[23]随后,黄文弼列举了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其中“人类学”亦占据一席之地。黄文弼所谓的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方面。黄文弼认为,两者在考古实践中同样重要,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在新疆的考察中主要运用的是后者:
故吾人欲研究考古学上之遗物遗迹,属于何种人类所遗留,必有藉此与同时发人骨之研究,方能明也。又就人类现状论之,由人类形状之差异,可推论其为何民族之人。由其同时方土之器物,即可明瞭民族与器物之关系。例如余在新疆罗布淖尔发见一僵尸,断发披及□画眉,革履,不着一衣,一望而知其非中国人,文化不高之民族。同□发见之器物除毛织品及草履外,再无他物。由其形貌之研究,可以断为本地土人。据其所用器物,则当时土人文化之劣等可知也[24]。
我们同时也该注意到,这篇文章暴露出黄文弼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某些价值取向方面的偏差。如所周知,人类学在强调田野调查和实证方法外,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便是文化的去中心主义,即所谓的“文化无优劣论”。中国人类学先行者之一的陈映璜在1918年的著作《人类学》中即指出:“要之各国人民,社交上之风俗习惯,皆因其社会组织异同之结果,原不足异。如以某民信偶像、某民无夫妇之别,或噉生肉,或焚杀魔巫,或牺牲子女,似此蒙昧之习惯,恒不恤诽谤而骂詈之,徒以自尊自大之偏见,侮辱他人种,适自形其浅陋,且与研究人类学之本旨相刺谬也实甚。”[25]当然,这并不足以掩盖黄文弼将人类学引入考古学的努力和建树。
在青年黄文弼走进北京大学的校园时,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激荡,传统的伦理道德和重视“形而上”的学术方法遭受到来自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的剧烈冲击。黄文弼和许多青年才俊一样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在学术方法上弃旧从新,推动了金石学向考古学的飞跃,也为历史研究扩展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新视野。在政治观点方面,黄文弼则秉持改良主义,主张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用新道德和新制度改造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解决社会弊病,改善人民境遇。通过回顾黄文弼先生早年的学术转型,揭示实证主义对中国哲学、考古学乃至人文学科的重大影响,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黄文弼的学术道路,也是对五四前后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内在逻辑的一次管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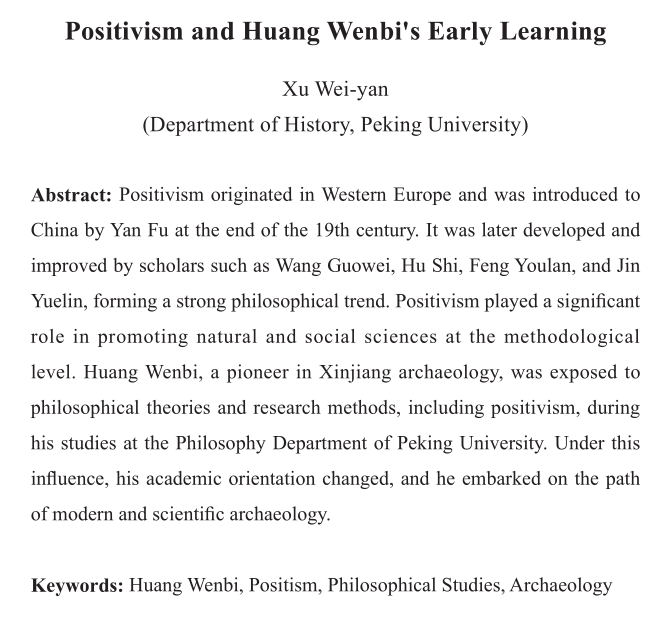
编者按:原文引自徐维焱:《黄文弼早年学术与实证主义》,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9月,页181~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