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郑玄礼学的延伸——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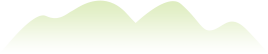
华喆
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出土《论语》郑注残卷内容的分析可知,郑玄《论语》注具有尊用《周礼》、参用《仪礼》、《礼记》的学术特点。《论语》郑注是郑玄礼学的延伸,对研究郑玄的经学有重要意义。
郑玄以《周礼》为中心构建礼学体系,又以其礼学为中心遍注群经,其经注中对礼的阐述是郑玄的一大特色。其实郑氏三《礼》注最先成书,郑玄对于经学的整体思考在其动手注经之前,想必已经形成。刘知几《孝经注议》引郑玄《自序》,自述其注经次第为三《礼》、《尚书》、《毛诗》、《论语》、《周易》。[2]今天郑注《尚书》、《论语》、《周易》均已亡佚,以往学者对郑玄《毛诗笺》中的礼学因素最为注意,比如陈澧《东塾读书记·诗》认为:“郑君专于礼学,故多以《礼》说《诗》”[3],今人梁锡锋则有《郑玄以礼笺〈诗〉研究》,专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但郑注《尚书》、《论语》、《周易》均已亡佚,只能依靠辑佚成果窥其一端,整体面目已经无从考知。虽然如清人张惠言对汉《易》用功极深,也有“郑氏言礼,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4]这样的断语,可是毕竟只是基于印象的推测而已,并非建立在充分材料基础上的论述。郑注《尚书》、《论语》、《周易》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学者并无充分了解。
至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转变。随着西域考古风潮的涌动,敦煌和新疆地区陆续有数种唐写本《论语》郑注被发现,当时学者如罗振玉已经注意到了《论语》郑注中以《礼》注经的现象,在其跋文中说:“郑君此注,多根据《礼经》。”[5]但彼时中国学者能够见到的《论语》郑注写本并不很多,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研究。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出土了唐中宗景龙四年卜天寿写《论语》郑注长卷。此后,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的金谷治先生的《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一书将郑注《论语》残卷搜罗完备,为推动学者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极大的助力。1991年,北京文物研究所的王素先生针对全部唐写本《论语》郑注进行了录文和校勘,并附以相关研究论文,结集出版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从《为政第二》至《宪问第十四》共13篇。台湾陈金木先生围绕唐写本《论语》郑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成果结集为《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三大册,1996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经过几代学者努力,郑玄《论语》注已经十见其六,可以了解其大体面目。通过对这些残卷的阅读,我认为郑玄尊奉《周礼》、“以礼注经”等特点同样存在于其《论语》注之中,《论语》郑注可以视为其礼学的延伸。本文即准备对《论语》郑注的这些特点进行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引用《论语》郑注,均据王素先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的录文,凡唐写本经文有残缺处,均依阮刻《论语注疏》补正,郑注文字则在王素先生整理的基础上做出。
郑玄将《周礼》奉为礼学圭臬,依据《周礼》确定周礼,成为其礼学的核心,也是他注经时主要的文献依据。《论语》郑注中也多次依据《周礼》设解,其中有明引《周礼》,也有暗用《周礼》。先举明引《周礼》之例,譬如《论语·雍也第六》: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郑注】儒主教训,谓师也。子夏性急,教训君子之人则可,教训小人则愠恚,故戒之。《周礼》曰:“儒以道德教人。”[6]
——吐鲁番阿斯塔纳184号墓12/1(b)-12/6(b)号写本
此处郑玄据《周礼·天官冢宰·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名”中“四曰儒,以道得民”,将儒引申为教学之意。郑玄在其《周礼》注中认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7],与《论语》此注正相呼应。孔安国对此的理解与郑玄全然不同,《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云:“君子为儒,将以明其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也”,[8]仅将“儒”理解为其字面含义,孔子对子夏所作的不过是一般性的告诫。郑玄这种独特理解使得孔子整句话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成劝告子夏要注意教学对象。在郑玄看来,子夏名列孔门四科之中,已是贤人,没有必要对其作君子小人之分,而他之所以认为“子夏性急”,有可能是因为《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有“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9]所以孔子是想告诫子夏教化不可操之过急,恰好与《周礼》之义相符。
郑玄亦以《周礼》为度量计算的标准,同在《论语·雍也第六》: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
【郑注】子华,孔子弟子公西华赤之字。为孔子使,其母居家而粮乏,冉子以为人有事者,必当食之,犹仕有禄,故为赤母求粟于孔子。是时孔子仕鲁。六斗四升曰釜也。
请益。曰:“与之臾。”
【郑注】臾,《周礼》作庾。庾,凡器名,实容二觳,厚半寸,唇厚一寸。子华为师使,义也,与仕者异。少与之者,抑冉有之言。
冉子与之粟五秉,
【郑注】以为孔子与之少,更(中缺)十六斗曰(中缺)秉,五秉合为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
【郑注】非冉有与之粟太多。[10]
——吐鲁番阿斯塔纳184号墓12/1(b)-12/6(b)号写本
郑玄此处有“臾,《周礼》作庾”,直接引用《周礼》,对经文进行说明。此举用意究竟何在呢?其实在上段注文中,郑玄提到“六斗四升曰釜”已经是在使用《周礼》中的经说。《周礼·冬官考工记·㮚氏》“量之以为鬴”,郑注“鬴,六斗四升也”,贾《疏》解作“此量器受六斗四升曰釜,因名此器为鬴,故云以其容为之名也。”[11]同样的注文,在《周礼·地官·廪人》和《冬官考工记·陶人》也出现过。既然在前面已经使用了《周礼》对度量进行解释,后面自然继续参用《冬官考工记·陶人》“庾实二觳,厚半寸,唇寸”,从“凡器名”以下直接使用了《周礼》的经文。之所以要在前面特别指出“臾”、“庾”的不同,是因为《陶人》郑注有“玄谓豆实三而成觳,则觳受斗二升。庾读如‘请益与之庾’之‘庾’。”[12]《论语》此注正与《周礼》相呼应。郑玄注意到底本与《周礼》不一致,故此在注中作了说明。
有趣的是,郑玄对冉有给粟的问题做了非常周密的计算。如果我们将“釜”、“庾”等概念换算成常用的“斗”、“升”等计量单位的话,孔子一开始只打算给公西华的母亲六斗四升小米,而在冉有的要求之下,又在“釜”的基础上增加了“庾”。庾是二觳之量,一觳斗二升,庾就是二斗四升。也就是说,孔子最后决定给公西华的母亲八斗八升小米,而冉有给了多少呢?一共五秉。五秉是多少斗呢?该写本至此有残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文字恢复出来,因为《仪礼·聘礼·记》中说:“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13]郑玄认为五秉为八十斛,应据此文而发,那么五秉就是八百斗,远远超过了孔子八斗八升的预期,所以孔子才认为冉有给的太多。
郑注依据《周礼》对计量单位进行解说,逻辑十分严密。但何晏在编辑《论语集解》时,却在“庾”的单位上不取郑说,反而引用了包氏“十六斗为庾”。包氏的依据在哪里呢?《史记·鲁周公世家》言“许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裴骃《集解》引贾逵说“十六斗为庾”。[14]贾逵没有为《史记》作过注,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十六斗为庾”出自贾逵的《国语》注。然而今本韦昭《国语注》却没有收入贾逵此注,仅在《国语·周语中》“野有庾积”下记“唐尚书云‘十六斗曰庾’”。[15]按此“唐尚书”当为丹阳唐固,《三国志·吴书》有传,史称:“著《国语》、《公羊》、《榖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16]韦昭在此又有自注云:“《聘礼》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似乎与今本《仪礼·聘礼·记》“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仅有一字之差,不知道是否郑玄所执经本与诸家不同,才有解说上的不同。西晋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仍有“庾十六斗”之说。[17]从汉代的贾逵、包氏到孙吴的唐固、韦昭,一直到西晋的杜预,都认同“十六斗为庾”之说,而唯独郑玄据《周礼》将“庾”定为二斗四升,由此可见《周礼》对郑玄的意义与众不同。
以上郑注中均明确提到了《周礼》一书,我们将其视为明引,那么暗用的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论语·八佾第三》: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郑注】倩兮、盼(中缺)容貌。素(中缺)成曰绚。言有好女如是,欲以洁白之礼成而嫁之。此三句《诗》之言。问之者,疾时淫风大行,嫁娶多不以礼者。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
【郑注】绘,画文。凡绘画之事,先布众彩,然后素功。素功(中缺)诗之意,欲以众彩喻女容貌,素功喻嫁娶之礼。(中缺)后素功,则皆晓其为礼之意也。
子曰:“起予者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郑注】(前缺)云“绘事后素”,时忘其意以素喻礼。子夏云“礼后乎?”孔子则觉,故曰:“起予者商。”商,子夏之名也。[18]
——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8/1号写本
此段郑注解释的核心在于“绘事后素”。子夏所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引逸《诗》。前两句见于《毛诗·卫风·硕人》,是赞美庄姜容德兼美之意。后一句不见于今本《毛诗》,而《仪礼·聘礼》有“皆玄纁系,长尺,绚组”,郑注云“采成文曰绚”,贾《疏》“郑注《论语》‘文成章曰绚’,与此语异义同。”[19]所以这句诗的字面含义就是在称赞庄姜美貌且衣着得体。明明在说女子容貌穿着,孔子却将此概括为“绘事后素”,将话题转向了绘画技法,这正是比喻的说法,由此而引出了子夏的“礼后”之说。郑玄为了说明孔子的用意,以“先布众彩,然后素功”作解。这里出现了“素功”一词,提示了我们郑玄暗用《周礼》的经说。《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说“凡画缋之事后素功”,郑注“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不言绣,绣以丝也。郑司农说以《论语》‘绘事后素’。”[20]这样就为“绘事后素”找到了经典的依据,突出了“后素”的意义。
郑玄暗用《周礼》的例子很多,这里再举一例,也涉及禄制的计算问题。比如《论语·雍也第六》: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
【郑注】原思,孔子弟子原宪之字。时孔子仕鲁,以原思为家邑臣。与之粟者,禄也。九百者,九百釜,为米五百四十釜。岁班禄,人食三釜,中士食十八人,米五十四釜,乃为仕十月。禄太多,非其数。(中缺)字之误也。
辞。
【郑注】辞让不受。
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郑注】毋者,止其辞让者。君子仕,辞位不辞禄。与尔邻里乡党乎,可以施惠于恩旧。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万二千五家为乡,五百家为党也。[21]
——吐鲁番阿斯塔纳184号墓12/1(b)-12/6(b)号写本
这里郑玄仍然在根据《周礼》给孔子算账。经文中“粟九百”以下是没有提到计量单位的,《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为“九百斗”,[22]而郑玄却认为是九百釜。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一釜是六斗四升,两人解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数量上已经差出了四千八百六十斗之多。郑玄的理由很明显,根据粟米法计算,粟九百釜就是米五百四十釜。《周礼·地官·廪人》“凡万民之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郑注“此皆谓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郑玄特别提到,逢中年则人月食三釜是“食米”,所以在《论语》注中提到“人食三釜”。所谓“中士食十八人”,《周礼》经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礼记·王制》却有“诸侯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23]之说,郑玄对此无注,但在《周礼·春官·内史》“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一句注中,引用郑众的解说云:“上农夫食九人……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24]郑玄对郑众的解说并无疑义,则可知郑众、郑玄均以《王制》说为周制,所以郑玄在此处认为“中士食十八人”。按照这个规则计算,中年则诸侯之中士的禄米应为一月五十四釜,那么粟九百就是鲁国中士十个月的收入,对于一个大夫的家邑之臣来说确实有点过多了。
但从给粟的量上来看,孔安国九百斗之说似乎更加符合情理一些,郑玄为什么要让孔子给原宪这么多呢?下面郑玄又做了说明,孔子希望原宪分给“邻里乡党”,“施惠于恩旧”。郑玄依据《周礼》对“邻里乡党”进行解释,《周礼·地官·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25]乡与遂相当,所以郑众注《周礼·地官·乡大夫》云:“万二千五百家为乡。”[26]郑玄此注把“邻里乡党”理解得很实,如果想要施惠于这样庞大数量的“邻里乡党”,那么孔子一次就给原宪数千斗禄米也就很正常了。
郑玄将“邻里乡党”照搬《周礼》中的数字作出解说,这样的例子在《论语》注中也很多见。比如《论语·泰伯第八》: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郑注】间,非。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丰洁。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方里为井,井间有沟,沟广四尺,深四尺。十里为成,成间有洫,洫广八尺,深八尺也。[27]
(P.2510号写本)
此注之中,井、沟、城、洫都是《周礼》里面的理想制度。《周礼·地官·小司徒》言:“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郑注云:“九夫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经之,匠人为之沟洫,相包乃成耳。”[28]所以《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又有:“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郑注“此畿内采地之制。”[29]《论语》郑注几乎完全袭用了《周礼》的原文,然而却与《论语》本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郑玄一定要照搬《周礼》来生硬地为“沟洫”作解,此时我们已经很难相信郑玄是在注《论语》,还不如说郑玄是在借《论语》来解说《周礼》。
以上是郑玄注《论语》时尊用《周礼》的几例,此外仍有很多,不必一一赘述。郑玄尊用《周礼》,一方面体现在对部分经文存在有多种不同解释可能的情况下,郑玄只以《周礼》的解释为准;另一方面又体现在郑玄最重视的还是《周礼》在《论语》中的反映,而非《论语》本身的语义。由以上诸多例证可以看出,《周礼》作为郑玄礼学的核心,不仅体现在其三《礼》注中,即便在《论语》注中也是如此。欲了解郑玄经学思想体系的构成,必须对《周礼》及《周礼》郑注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以此再与郑玄其他经注相参照,才能体会到郑玄所要表达的含义。
《论语》就其体例而言,与《礼记》中《曲礼》、《檀弓》等篇最为接近,内容也往往相关,所以郑玄注《论语》时参用《礼记》之处很多。如果对《礼记》郑注缺乏了解,自然难以捕捉到《论语》郑注的要点所在。但与《周礼》不同的是,《周礼》是郑玄注的基本准则,《礼记》只是郑玄的参考资料,以下略举几例以证。
《论语·八佾第三》: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
【郑注】林放,鲁人。孔(中缺)者,疾时人失(后缺)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郑注】易,犹简略。礼本意失于奢,不如俭;丧,失于简略,不如哀戚。《礼记》曰:“斩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齐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而哀;小功、缌麻,哀容可也。”[30]
——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8/1号写本
林放问礼,孔子作答,从含义来看,孔子是在强调礼意本自人心,外在的表现形式却在其次。经文大义不难把握。但郑玄用“简略”来解释“易”有其所指。因为《论语集解》引用包氏说“易,和易也”,看似与郑玄的“简略”差别不大,但《礼记·檀弓上》“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31]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相近,郑玄一定要呼应《檀弓》之义,所以将“易”解为“简略”。
郑玄在注中引用的一段《礼记》,都在说丧礼时的哭声,放在此处稍有突兀的感觉,然而仔细体会,也有其用意在内。这段话出自《礼记·间传》。据郑玄《三礼目录》,这一篇是“记丧服之间轻重所宜”[32],郑玄希望以此来说明丧礼之“戚”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郑玄要谈到这个问题呢?恰恰也在《礼记·檀弓上》又有一段:“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则哀矣,而难为继也。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郑玄认为“孺子泣”是指“声无节”,孔子认为无节之泣虽然哀已经足够,但难以为继,失去了礼的中道。[33]所以郑玄引用《礼记·间传》,实际上是有其潜台词在此。也就是说,虽然“丧,失于简略,不如哀戚”,但是哀戚并不是没有底线的痛哭,如果哭踊失去了节制,也形同失礼,《间传》正好说明了丧礼时哭泣之节。郑玄一定是在此有鉴于《礼记·檀弓》的记载,所以要对包氏的经说进行调整,并且加入自己的理解,使经义显得更加丰满充实。
又如《论语·乡党第十》:
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
【郑注】不忘敬也。朝服者,玄冠缁衣素裳缁带韠素。绅则带也。疾时寝室中北墉下也。[34]
(P.2510号写本)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经文在说孔子在生病时鲁君前来探病,孔子仍然不忘行礼,依旧要换上朝服,就连躺下的位置都有讲究。郑玄注在解释何谓朝服之外,又在后面加上一句“疾时寝室中北墉下也”,这是经文中没有的内容,究竟有什么样的根据呢?其实来自《礼记·丧大记》:“疾病,外内皆扫。大夫撤悬,士去琴瑟。寝东首于北牖下。”郑玄注称:“谓君来视之时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曰北墉下。”[35]这是郑玄对丧礼之前的基本认识,在《仪礼·士丧礼》“死于适室,幠用敛衾”一句,郑注云:“适室,正寝之室也。……疾时处北墉下,死而迁之当牖下。”[36]《仪礼·既夕礼》“士处适寝,寝东首于北墉下”句又注:“将有疾,乃寝於适室。”[37]北墉就是室中的北墙,郑玄认为士或大夫疾病时应当卧于正寝的北墙或北窗之下,头在东方,而此处《论语》经文中只说“东首”,但没有说是躺在南墉之下还是北墉之下,故此郑玄据《礼记·丧大记》将经义补足。
郑玄不仅仅利用《礼记》中的经说来印证或补足《论语》注,有时也会将《礼记》与《论语》具有相似性的段落联系在一起,直接将《礼记》注移用在《论语》之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在《论语·八佾第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郑注】(前缺)夷吾。言其德器小□,小□,以其才足成(中缺)奢侈,不务为俭也。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乎?”
【郑注】或人见孔子云(中缺)三归,娶三姓女(中缺)备官,大(中缺)是非为俭。
曰:“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郑注】或人见孔子云“焉得俭乎”,则以为知礼。(中缺)塞,犹蔽。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反坫,反爵之坫,在两楹之间。(中缺)于门树屏以蔽之。若与邻国为好会,其献酢之礼,礼(中缺)受爵于坫上。今管仲奢侈为之,是不知礼也。[38]
——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8/1号写本
这一部分前半段郑注缺损较多,已经无法看到全貌。后半段郑注相对比较完整,而且从字面来看,需要重点加以解释的部分也就是“树塞门”和“反坫”,郑注似乎也在此花费了不少笔墨,然而这一切却都取材于郑玄的《礼记》注。首先,孔子同样内容的言论,在《礼记·杂记下》中也有记载:“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这里郑注称:“旅树,门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39]两处经文的内容较为相似,只是《礼记》注较为简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因为在前面的《礼记·郊特牲》中已经有“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一句,管仲所为,正是“大夫之僭礼”中的两条。郑玄对《郊特牲》出注云:“旅,道也。屏谓之树,树所以蔽行道。管氏树塞门,塞犹蔽也。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盖在尊南,两君相见,主君既献,於反爵焉。”[40]仔细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此段郑玄《论语》注基本上是从这一段《郊特牲》注中直接转抄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孔颖达《礼记正义》,“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云云,是《礼纬》中的文字,[41]兼用经纬是郑玄注经的一大特色,所以在《论语》注中也有体现。相比于《礼记》原注,郑玄删去无关的“大夫以帘,士以帷”,又根据《论语》正文对此经注作出了必要的调整,并非简单重复原文,使整个经注能够贴合《论语》的经文,精巧而不显生硬。
对郑玄而言,经部文献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周礼》,是其礼学的发端,以下要算是《仪礼》与《礼记》,接下来才是《诗》、《书》、《易》、《论语》以及各种纬书,形成对其礼学体系的各种补充。在郑玄《尚书》注已佚的情况下,《论语》注为我们研究郑玄的思想体系提供了线索。所以在其《论语》注中,如上节所述,《周礼》是郑玄确定礼的内涵的基本依据,而《礼记》则是郑玄对《论语》经义的补充,郑玄凡对经义有所发挥之处,几乎离不开《周礼》、《礼记》两书,可见礼学在郑玄体系中的地位。
三《礼》之中,郑玄《论语注》对《仪礼》涉及不多,大概是因为《论语》与《仪礼》内容相去较远的缘故。但尽管郑玄较少直接引用《仪礼》,可是却有一些与《仪礼》有关的独特礼说,仍然贯彻在其《论语》注中。这里以郑玄的“人偶”之说为例,专门做一解析。
“人偶”一词在郑玄《仪礼》、《礼记》注与《毛诗》笺中均有出现,在其《论语》注中也出现过两次。如《论语·乡党第十》:
君使召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其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郑注】君召使摈,有宾客使之迎之。色勃如,矜庄貌。足躩如,逡巡貌也。揖所与立,人偶同位也。揖右人,右其手;揖左人,左其手。将作揖,必磬折。磬折则衣前垂,小仰则衣后垂,故曰“襜如”也。翼如,股肱舒张之貌。宾退,礼毕出。复命,白君曰:“宾已去。”[42]
(P.2510号写本)
《论语》中“揖所与立”并不难理解,而郑玄却要解释为“人偶同位”,反而让人感到费解。什么是“人偶”呢?大致可以理解为双方互相致礼。[43]郑玄之所以要在此处使用“人偶”一词,是因为他要把这一场合与《仪礼·聘礼》的记载联系在一起。“君使召摈”,郑玄解作“有宾客使之迎之”,而《仪礼·聘礼》对迎宾的规定是:“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摈者出请事。”孔子在鲁为大夫,应是承摈。那么迎宾时诸摈的工作是什么呢?郑注对此做出了解释:“摈,谓主国之君所使出接宾者也。绍,继也,其位相承继而出也。主君,公也,则摈者五人;侯伯也,则摈者四人;子男也,则摈者三人。《聘义》曰:‘介绍而传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质,敬之至也。’既知其所为来之事,复请之者,宾来当与主君为礼,为其谦不敢斥尊者,启发以进之。於是时,宾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摈在闑东阈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摈耳,不传命。上介在宾西北,东面。承摈在上摈东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摈,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摈之请事,进南面,揖宾俱前,宾至末介,上摈至末摈,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请事,还入告于公。天子诸侯朝觐,乃命介绍传命耳。其仪,各乡本受命,反面传而下,及末,则乡受之,反面传而上。又受命传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门容二彻参个,旁加各一步也。”[44]
如果把这段复杂的礼学语言换成生活语言的话,那就是主与宾各有参与行礼的人员,主君一方称摈,宾客一方称介,摈、介人数相当,各站一列,他们主要的工作在于传话。迎宾的主君为了表示对宾的尊敬,必须向其礼问来意。礼问并不能由主君直接向宾呼喝相问,而是由摈者来完成。主君先将问话告知距离自己最近的上摈,上摈传承摈,依次而下,直至最末一位的末摈,由末摈告知末介;末介又依次将问话传至上介,由上介将问话传递给宾,宾作答后通过诸介再依次传话,由末介告知末摈,诸摈又依次上传告知主君。如此往复,才能完成礼问的整个过程。那么,孔子置身摈列的时候,当上摈传话下来时,则先揖上摈,这时上摈在其右方,所以要先起右手作揖,也就是《论语·乡党》郑注中的“揖右人,右其手”,接着传话给下一位摈者,在己左方,则先起左手作揖,也就是“揖左人,左其手”。整个过程中都要有作揖的动作,这就是“揖所与立,人偶同位”。至于“罄折”和衣服的“襜如”都表现了孔子作揖时动作的美观。
原本在《仪礼·聘礼》郑注中也提到过“人偶”问题,但是并不是在迎宾传问的阶段,而是在宾入门以后,有“公揖入,每门、每曲揖”,郑注“每门辄揖者,以相人偶为敬也”。[45]这是公对宾的“人偶为敬”,但郑玄在《论语·乡党》注中将“揖所与立”解释为“人偶同位”,等于是在提示我们,迎宾时传问互揖也是“人偶”的体现,相当于是对《仪礼·聘礼》的补充说明。
在诸多《论语》郑注残卷发现之前,郑玄经注中“人偶”一词只出现过六次,分别是《仪礼》注三次、《礼记》注一次以及《毛诗》笺两次。《毛诗》笺中的“人偶”是在《桧·匪风》:
谁能亨鱼,溉之釜鬵。
【郑笺】云“谁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
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郑笺】云“谁将”者,亦言人偶能辅周道治民者也。(下略)
以下孔《疏》解此“人偶”作“人偶者,谓以人思尊偶之也。《论语》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辞’,《礼》注云‘人偶相与为礼仪’,皆同也。”[46]清代学者因为看不到《论语》郑注残卷,所以辑佚学者只知道“人偶同位”、“人偶之辞”是郑玄《论语》注,却不知道是何句之注,以致无所归附。其实“人偶同位”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的《论语·乡党》郑注,在伯希和2510号残卷上即可看到;“人偶之辞”恰好在卜天寿写本上也能找到,却是在《论语·里仁第四》: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哉!”曾子曰:“唯。”
【郑注】(前缺)呼曾子,人偶之辞。我之道虽多,一以贯知之。唯者,应敬之辞。[47]
——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8/1号写本
孔子直呼曾子之名“参”,郑玄在注中特别指出,这一举动没有其他含义,只是孔子为了表示对曾子的亲昵之意,所以是“人偶之辞”。遗憾的是,因为前段注文残缺,不清楚郑玄为何要在此处使用“人偶”来解释经文。总之,郑玄的“人偶”之说,在传世文献之中不过数见而已,从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注残卷上面就可以为我们增补两条,又可与《礼记正义》互证,可谓价值匪浅。
“人偶”两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郑玄要用这两个字来表示人与人之间互揖互敬的关系,这些疑问恐怕无法得到解答。但从郑玄的使用情况来看,“人偶”主要是用于《仪礼》中某些场合下表示情感关系的词汇,而这一词汇同时能够见于《毛诗》、《论语》,可见郑玄确实以其礼学支配其他诸经的解释。
从今天发现的诸多唐写本《论语》郑注残卷来看,郑玄对经义的确有许多独特的阐发。大体上来说,郑玄对《论语》解说是根柢于五经,处处需要与五经的内容相对照,如果读者对经书缺乏了解,读起郑注来实在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例如《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今人看来,“怪力乱神”代表了四个不同的概念。何晏编纂《论语集解》时也引用王肃说,认为:“怪,怪异也。力谓若奡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也。乱谓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谓鬼神之事也。或无益于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48]这一解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然而看到郑注之后,才知道王肃注是刻意针对郑玄而发。郑玄是怎样解释的呢?他把“怪力乱神”看作“怪力”与“乱神”两部分:“为识浅者将为之有精气,不修其德,而徒祈福祥,以惑世沮功。怪力,谓若石立社移。乱神,谓神降于莘之属也。”[49]“石立社移”是灾异现象,被郑玄概括为“怪力”;“神降于莘”则出自《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左传》称:“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50]其后虢君祷神求赐土田,终于在僖公五年被晋所灭。按照内史过的说法,这就是神降以观虢之恶,所以郑玄以为“乱神”。在其《箴膏肓》中亦提到“子所不语怪力、乱神,谓虚陈灵象,于今无验也”[51],与《论语》注意相呼应。假如我们对于《左传》的内容不够了解,只看《论语》郑注的话,恐怕就不能理解郑玄的意旨所在。
由此可见,郑玄体系的构成就像铺开的一张大网,经文就如同大网之上的各个节点,彼此总能互相呼应,《周礼》居于网络的中心,《仪礼》、《礼记》次之,其影响辐射到周围诸经。虽然《论语》在郑玄体系中位居诸经之末,在这张大网上仅占一隅而已,但恰恰是这一隅之地,又为我们从传世文献以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张大网提供了可能。我们今天研习郑学,仅仅是稍窥其端,就已经惊叹于这张大网的精巧细密,实在很难想象郑玄是怎样凭借个人之力,构建出如此复杂而有序的体系。期待今后地不爱宝,能够有更多的《论语》及其他经书郑注残卷在吐鲁番地区被发现出来,为研究郑玄的学术思想提供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滑动查阅注释
滑动查阅注释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