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耶路撒冷以东:一部巴以边界的民族志
《耶路撒冷以东》

对我而言,本书更像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一个样本。它尝试调和、甚至冲破学科的“边界”,试图从经验世界的空间出发,尝试“阐述”其背后的意义。这种明晰的参与式观察,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观察者的主体位置,对叙述的直接影响。它是有意识的、不隐藏的、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参与式的中心主义。
——殷之光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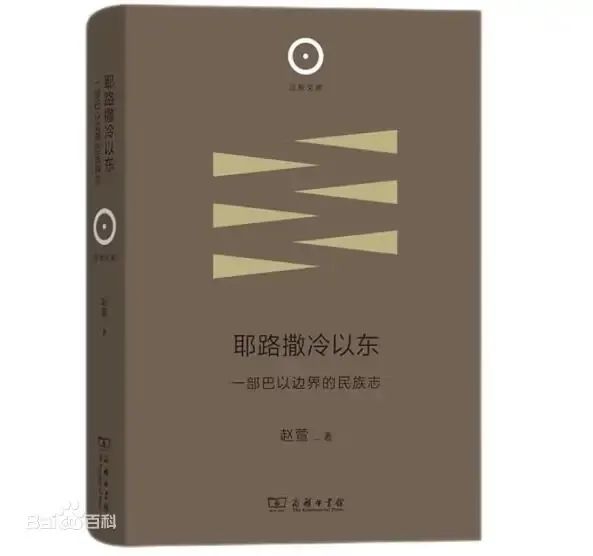
本书是中国学者在中东世界进行田野作业而完成的民族志发轫之作,全面描述和讨论了“在边界上”的耶路撒冷社会。沿着地缘-生命政治的理论路径,本书兼顾不同逻辑、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表述方式,将巴以冲突放回到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去考察,描述并揭示出家族、国家在“耶路撒冷以东”的本来面貌以及持续经历治理化的复杂过程,力图清晰详实地呈现历史叙事、权力关系与治理效果在地化的多样性与复合性,最终还原出一个客观、真实、饱满的耶路撒冷与巴以边界。
作者简介

赵萱,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成员,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人类学、海外民族志、批判边界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曾于耶路撒冷完成15个月的田野调查,并以“边界”为母题带领研究团队在中国新疆、云南、广东等地,突尼斯、保加利亚、比利时、新加坡等国从事田野作业,关注生命政治流动、治理、发展等议题,著有《边观:全球流动的人类学笔记》《常人之境 :中国西北边地口岸人的口述》等,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
耶路撒冷以东·序
殷之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外行,在赵萱的著作《耶路撒冷以东》面前,我也许更像是一个旁观者。2012年,作者带着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长久以来的兴趣”,以及由当时所谓“阿拉伯之春”所激起的“现实诱惑”,来到了东耶路撒冷进行田野调查,并最终选定“耶路撒冷老城与巴以隔离墙之间的橄榄山”以及橄榄山上巴勒斯坦人聚居的“榄村”,作为他书写的起点。与我熟悉的学术写作不同,在赵萱对橄榄山的叙述中,作者始终在场。当我们冲破本书第一章的理论思考之后,即刻便进入到了赵萱的旅行。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字里行间,与作为作者的“我”相遇。
通过赵萱对榄村的参与式观察,我们不但看到了橄榄山东麓绵延的巴以隔离墙,看到了灰黄色的耶路撒冷、圣殿山,看到了橄榄山中部及东南部谷地在巴勒斯坦聚居地中间散布的犹太教传统墓地,也看到了橄榄山上不乐意早起做礼拜咖啡店主、穆斯林贾米勒;贾米勒店里的伙计、因为年轻时与一位德国女子的爱情而转信基督教的阿卜杜拉;还看到了常去咖啡馆的德国传教士塔玛拉女士,和不管顾客信仰什么,他“什么都可以卖”的易卜拉欣;以及为了办理土地证而数十年奔走的亚金。我们还同作者一起,体会了作为外来人与未婚年轻男性,在榄村租房的艰辛;参加了拜节的庆典;甚至还一同经历了艾布浩瓦家族与艾布苏比坦家族对一起涉命交通案的调解,体会到了以色列国家权力与巴勒斯坦宗族秩序之间微妙的协作与互斥关系。
始终在场的作者可能会令许多学术作者感到不安。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博士生导师给我的第一个写作忠告,便是隐去行文中可能出现的“我”字。因为“我”的存在,会让本应当是“客观”的研究,显得充满了主观色彩。有趣的是,“我”的故意隐身,并不意味着“我”的退场。这一行动仅仅将观察的主观性问题悬置了起来,并营造了一种普遍性的假象。在过去的40余年里,这种对作为观察者的“我”的策略性搁置,被逐渐等同于普遍主义。通过这种意义置换,用以对现实经验进行阐释的概念范畴、术语以及理论进路等,似乎变成了一副套在经验世界上的枷锁。一方面,作为观察者的“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这些固有意识在面对现实时的局限甚至是荒谬。但另一方面,当离开了这些固有意识的支撑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又变得困难重重。赵萱从未试图掩饰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感,给作为一名学术工作者的他带来的困扰。
在当代人文学科的不同分支里,固有意识体现在学科体系内一整套理论、术语、甚至方法中。作为从国际关系史角度介入“区域研究”的我而言,“国家”、“民族”、“阶级”、与“关键人物”是我熟悉的分析单位。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而言,用“文明”、“社会”、“身份”等来理解复杂的现实也是搁置观察者“主观性”视角的绝好途径——这也是赵萱最初母题的基底。在具体问题方面,赵萱处理的是“巴勒斯坦问题”。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既陌生,但却又轻易能让人产生联想、激起情绪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下,我们从来不缺少国际关系、历史、宗教等学者的参与。更不缺少新闻图像与政治宣言这些与更广大观众发生联系的表达。在这所有讨论中,如果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出发,那么冲突、被殖民、压迫、难民等关键词,便自然而然地限定了我们作为“旁观者”理解“他们”的基本视角。同样,如果从以色列或是犹太复国主义政府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将看到国家治理、民族和解、反恐等成为了讨论的关键。然而, 在本书的开篇,赵萱便坦然地承认了他在面对这些宏大问题时的无奈。然而, 恰恰是这一坦然的自白,使得《耶路撒冷以东》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理论价值。值此,被搁置的观察者主体重新回归。
赵萱对观察者视角的自觉让人想起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所提到的“双重视角”(double vision)。1949年,作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瑞士人让·莫尔(Jean Mohr)第一次来到了杰里科和希伯伦,那里聚集了大量由于以色列建国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让·莫尔的任务是参与设立难民营、学校,并进行基本的人口普查。1979年,作为摄影师的让·莫尔在联合国的委托下,再次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他将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描述为 “一次伤痛心灵的经历” 。因为,时隔30年,难民们的处境非但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1983年,他将历年来在巴勒斯坦及许多巴勒斯坦人难民营中拍摄的照片,展现给了西方观众。这场展览引起了萨义德的注意。在萨义德的推荐下,莫尔受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的委派,再次前往巴勒斯坦拍摄。1986年,两人合作将影像与文字结合在一起,以《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为题出版。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里,萨义德时刻提醒着读者们自己的身份。在写作中,萨义德时而用“我们”,时而用 “你们”,也会用“他们”来指称巴勒斯坦人。随着这种代词的转换,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观察者萨义德,作为读者的我们,以及被观察者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现实存在的距离,感觉到了作为美国学者的萨义德,以及作为巴勒斯坦人的萨义德,在走进巴勒斯坦社会这个现实之后,两种自我间的游移与交错。这种“双重视角”坦然地将萨义德作为一名“参与的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将他自身的观察与思考,将他个体多种社会身份之间的游移与交错变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正是不掩饰“双重视角”的萨义德,才能将封闭、完结的文本,重新打开,并融入到开放世界之中,成为这个世界有生命的片段。作为作者,也正是在这种不掩饰的文字里,才能诚恳地邀请读者,参与到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复杂旅程之中。萨义德主体位置的认识与自觉,无法简单地用对巴勒斯坦“身份”的“认同”来概括。而更应当被视作是对单一身份定见的主动突破。
同样,在赵萱对榄村的描述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诸种建立在血缘、宗族、宗教、性别等范畴上的认同,在实践中的转换与消长。在《耶路撒冷以东》的第一章里,作者经由生命政治(bio-politics)介入,对传统国际关系与历史研究中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书写方式进行了反思,并对从地缘政治(geo-politics)视角理解巴勒斯坦问题中呈现的不足做出了回应。作者用以替代领土国家来理解巴勒斯坦的范畴是“边界”。这种边界虽然切割了地理的与秩序的空间,但是同时也划出了可被突破、延展与渗透的弹性界限。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不同力量互动的场所。
赵萱指出,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以色列治下的巴勒斯坦人的社会运行实践。实际上,这一点在萨义德对巴勒斯坦人的讨论中也有所体现。萨义德发现,在外界对巴勒斯坦的叙述中,巴勒斯坦人或者作为犹太人建立定居殖民地后的受害者,亦或是作为扛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头戴阿拉伯头巾的恐怖分子与战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两种“图标”虽然都展现了部分的真实,但却都是对巴勒斯坦人的他者化。将在实践中生活的,富有与你我一样情感的主体,禁锢在抽象的“受害者”或是“暴徒”的定见之中。这种意识上的霸权,既无助于理解巴勒斯坦复杂的现实,更无从实现巴勒斯坦人对政治主体地位的诉求,也无法带领我们走出自身固有意识的牢笼。
当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来理解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社会运行实践,绝不意味着消解巴勒斯坦人寻求民族独立的现实意志。赵萱的讨论为我们呈现了殖民治理下,反抗的多样性,及其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在这一复杂关系中,一个巴勒斯坦人建立在“受苦和离散上的共同体”(萨义德语)才得以形成。作者引入了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与阿克希尔·古普塔(Akhil Gupta)对国家的分析,通过对榄村日常生活的深入观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在巴勒斯坦人中间更丰富的“不以国家为中心的、非阶序化的、超越领土的空间认识”。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政府之间,并不简单是对抗关系。更多则是在顺从与协作的大前提下,以家族为中心,对自身空间与权力的有限度的维护。这一点,在作者对“好人亚金”的描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此外,作者还给我们讲述了一次阿拉伯土地日纪念活动中发生的暴力冲突。赵萱让我们注意到,这场冲突更像是以色列政府治理术的表演。通过暂时性让渡了国家对耶路撒冷老城周边极小部分领土与秩序的控制,以色列默许了巴勒斯坦人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进行短暂的情绪宣泄。我们可以在“好人亚金”与土地日冲突的故事中,看到帝国史研究者们愈发感兴趣的一种现象。在大卫·康纳丁(David Cannadine)对英国治理印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殖民帝国的治理除了暴力之外,更多依赖的是在被统治群体中间,通过寻找代理人,以授勋、荣典、教育、以及利益分配等多种方式,建构帝国代理人对帝国中心的认同。这种创造同意(consent)的治理特性,被康纳丁概括为帝国对“共同性”(Sameness)的建构。而这种帝国权力通过暴力与同意的双向展开,也恰恰体现了葛兰西对“霸权”(hegemony)构成的政治学分析。
观察者的现身,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阐释的内涵重新带入了我们用以认识世界的意识里。通过这一行动,作者不仅将“如何研究”带入到了思考中,更迫使作为读者的我们,对“为何研究”这一根本问题意识做出自觉的回应。作为人类学者的赵萱在《耶路撒冷以东》中,试图追问进行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意义。而对我而言,本书更像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一个样本。它尝试调和、甚至冲破学科的“边界”,试图从经验世界的空间出发,尝试“阐述”其背后的意义。这种明晰的参与式观察,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观察者的主体位置,对叙述的直接影响。它是有意识的、不隐藏的、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参与式的中心主义。
调查研究将学术工作带离了固有意识创造的安全港,带入了充满情感、经验与变动的复杂现实世界中。穿越“边界”,便是“我”,或者说是“我们”借理论思考进行实践的第一步。而在此之前,看见作为观察者的主体的“我”,则是一切问题与行动必需的起点。
通往未来的旅程,就此才刚刚开始。
2023年3月1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