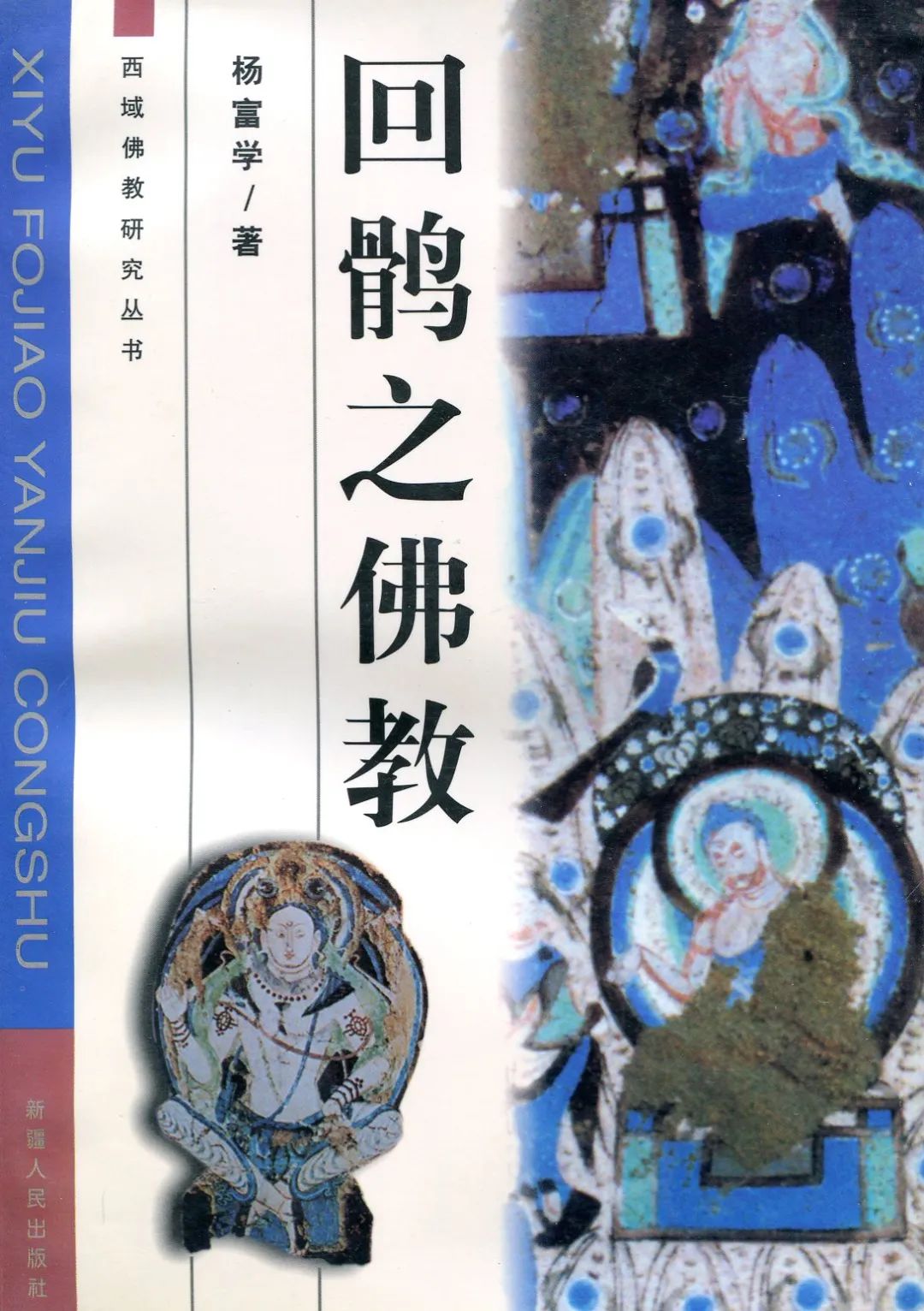书籍资料库
黄心川 | 《回鹘之佛教》序
我国的佛教最早是由古印度经过陆路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传入的。中国古代史籍对西域有着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西域是两汉以后对于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从狭义上看指葱岭以东的地区,广义则指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广大区域,包括新疆、中亚其它地区、印巴次大陆和欧洲东部等等。佛教传入新疆有南北二路:南路自天竺迦湿弥罗先传至于阗,复经疏勒、莎车、皮山、且末、楼兰(鄯善)等地而至敦煌;北路则自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一带)传至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尉头、龟兹、焉耆、高昌、北庭、哈密而入敦煌,自汉至唐,这里的佛教一直十分发达、昌盛。回鹘之佛教势力及文化遗迹就集中分布在丝路北道地区及河西走廊。史籍的记载和考古发掘表明,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曾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过历时达400余年之久的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在其强盛时,辐员相当辽阔,东起甘肃西端,西迄中亚两河流域,包括伊塞克湖地区在内,南自昆仑山北麓与于阗、喀什噶尔一线,北抵天山以北。高昌一带在汉朝时属车师前王国。班超曾于此国境内之柳中(鲁克沁)设西域长史,东汉以后佛教开始流行,在4世纪时已成了国教(见《出三藏记集》卷八)。据载,车师前王国国师曾向苻秦献梵本《大般若经》,著名的高昌僧人道普能通六国语言。高昌、焉耆、龟兹连同南道的于阗、疏勒都是当时西北边陲佛教活动的中心。麴氏高昌王国时期(502—640年),仅高昌地区就至少有130多座佛寺,高僧辈出,译经事业十分发达。公元7世纪中叶玄奘西行去印度途经高昌、焉耆和于阗时对这些地区佛教的隆盛情况在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有详细的记录。著名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西大寺、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吐峪沟、胜金口石窟、库车的苏巴什大寺、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石窟、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凿建的。回鹘人于9世纪中叶由漠北徙入西域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后,虽然仍奉摩尼教为国教,但对佛教采取扶持、奖掖的政策,使王国境内旧有的佛教在这一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公元982年宋使王延德出使高昌,亲见这里有佛寺50余所,寺中香火繁盛,备有大藏经;北庭的应运太宁之寺此时也持续繁荣(《宋史》卷490《高昌传》)。敦煌写本S.6551更是详载了高昌回鹘举国上下崇佛的情况:“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善男善女,檀越信心,奉戒持斋,精修不倦。更有诸都统、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师)、僧政、寺主、禅师、头陀、尼众、阿姨师等,不及一一称名,并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师,为国中宝。”
在回鹘西迁时,迁入河西走廊的那部分人也分别以甘州(今张掖)、沙州(今敦煌)为中心建立了两个汗国,同高昌回鹘一样,他们也尊奉佛教,由于受藏传佛教之影响,河西回鹘佛教比起高昌来,有着更浓重的密教色彩。他们开凿的石窟也不少,可见于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和酒泉文殊山石窟之中。
佛教在三个汗国中的传播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在前述高昌、龟兹及敦煌地区诸石窟的基础上,回鹘人又新开、重建了不少石窟,并绘制、雕造了不少艺术品。回鹘壁画、雕塑贴近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壁画造型新颖,笔法简洁,色调热烈明快,装饰富有趣味性,以大量的暖色使气氛显得活泼、奔放。雕塑兼具东西方的风格,既承袭我国唐代造像的遗风,也受希腊式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并呈现回鹘自身的特色。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的300年间,吐鲁番、哈密地区的佛教仍很流行,而河西回鹘直至17世纪末还有佛经写本出现,说明佛教仍在继续。尽管回鹘佛教也显得很芜杂,佛教常常与摩尼教和民间信仰相糁合,大小乘和密教之间的门户之见相当明显,但是,回鹘佛教覆盖的区域广大,历史长久,寺院众多,高僧辈出,译经事业发达,佛教文化繁荣,不仅对西域而且对汉地佛教都有深重的影响。可见,回鹘佛教在整个西域佛教中占有显要的地位,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回鹘佛教无疑地是中国佛教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鹘的佛教文明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地区在六朝的589年之前一般是经过西域地区的。佛教在西域地区传、发展到繁荣的时期,也可以说正是西域佛教传入内地,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的时期。当时,西域就有不少高僧到中原地区弘法,同时,内地也有不少僧侣、居士去西域求法取经,这些过往的僧人、学者自于阗的朱士行到唐朝的玄奘、义净无虑数百。他们从印度、西域取得大量的梵文经典后携归内地进行翻译以宣扬弘化,因此中原佛教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或者文化、艺术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过西域佛教或由西域传入的印度原始佛教的影响,中国汉地佛教中某些学派、宗派就是把印度佛教、西域佛教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土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此外,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汉地佛教及其文化艺术成长壮大之后反过来又通过丝绸之路回传至新疆、中亚乃至印度。例如在犍陀罗后期佛教雕像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中国唐风的影响。在这双向交流中回鹘佛教必然会起到重要传承的作用,这可以从回鹘佛教徒曾作为中原王朝与印度、波斯佛教界联系的中介一事看得出来,也可从佛教理论的弘化、佛教文学作品的创作、石窟的开凿、壁画的造型等方面得到印证,因此对回鹘佛教的了解、研究使我们可以弄清西域佛教和汉地佛教的关系,深入地了解中印佛教文化的历史和中国佛教发展的过程,以及回鹘佛教在汉地佛教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从19世纪中叶始,英、法、德、俄、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中国新疆和中亚其它地区的霸权,纷纷派出名目繁多的传教士、使者、学人、探险家、考古队接踵而至进行“学术调查”、“考古探险”等等,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河西走廊的敦煌和内蒙古西端的黑城等地获取了大批的古代佛教历史文献和文物,随后又组织人力进行学术研究,重点就放在对当地有着广泛影响的民族和宗教的研究之上,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可资借鉴。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些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明显地带有为帝国主义侵略目的直接服务的印痕,所以说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和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学术成果的局限性,特别是对那些明显含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必须予以批判,对其钻牛角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也应予注意。
在西方和日本学术界的刺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也一度出现了“西域研究热”和“佛教研究热”,不少学者对西域和敦煌出土的古代佛教和摩尼教的文献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终因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等原因未能持续发展下来。全国解放后,随着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作的重视,西域、敦煌的研究也再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自己培养出了新一代的西域民族和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撰写了蔚为大观的研究著作,阐述了西域、敦煌诸地各民族的灿烂文化。现在摆在面前的这部《回鹘之佛教》一书就是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同志对这一课题的最新奉献。该书是我所知国内外系统研究回鹘佛教史的第一部专著,正如同他去年刚刚发表的《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6月版)一书填补了沙州回鹘研究的空白一样,此书的出版,又填补了西域佛教史中的一个空白领域,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
杨富学同志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对维吾尔族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时直接考入新疆大学历史系师从苏北海先生专攻维吾尔族历史、语言与文献,毕业后又赴印度德里大学深造,学习梵文与佛教,他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新疆和敦煌,对维吾尔族历史、文化、宗教及古代艺术有着切身的体会,兼备了研究回鹘佛教这一复杂课题所需的多方面条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敬业精神,多年来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回鹘文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之中,这部书便是他多年精心研究的结晶。
书中收集的回鹘史料极为丰富全面,他不仅搜罗了外国学者和我国学者已经刊布了的回鹘文献和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也研读了大量的汉文史乘和敦煌、吐鲁番所出的佛教写本。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的鉴定,甄别其真伪,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对回鹘佛教进行了架构,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译经情况、功德思想、寺院的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探索。考虑到文献的缺乏和回鹘文本的收集、整理之不易,我可以想像得出作者在撰写这部著作时必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但作者还是尽了巨大的努力,以顽强的精神越过了撰写中的道道障碍。由于高昌回鹘和河西回鹘生活在广大的土地上,覆盖面宽,许多民族都逐鹿于这个地方,多种宗教和多种文化在这里汇合,加上复杂的地理条件以及目前资料还不很完备的状况,都使对回鹘佛教和回鹘文明作出完全正确全面的阐述颇具困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作者已尽了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渴望此书出版后能唤起更多的学者对回鹘历史和文明的重视,随着越来越多的回鹘佛教文献的发现与刊布和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来有更多的和更好的著作问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不仅从民族的角度对回鹘的佛教历史作了阐述,而且也对受到佛教影响的回鹘文明,诸如文学、哲学、美术、书法、语言文字等作了相当有意义的描绘,因此,此书不仅是一部回鹘佛教史,也是一部回鹘的文明史。回鹘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民族,她的文明既有自身的文化基石,又受到周围的汉、藏、粟特、吐火罗等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深深打着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的烙印。这种文化的融合现象在该书中都有着具体的反映,堪称可贵。
1996年6月于车公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研究员于2021年2月10日上午11点3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黄心川先生一生致力于东方哲学、宗教特别是印度哲学、佛教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就。对敦煌研究院的学术发展与人才培养咸有贡献。先生一生勤于治学,奖掖后学,一身正气,学识广博,著作等身,乃吾侪治学之楷模。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哲人其萎,满怀悲思;梁木斯摧,风范犹存。
缅怀黄心川先生


2016年黄心川先生在瓜州

黄心川先生与杨富学先生合影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