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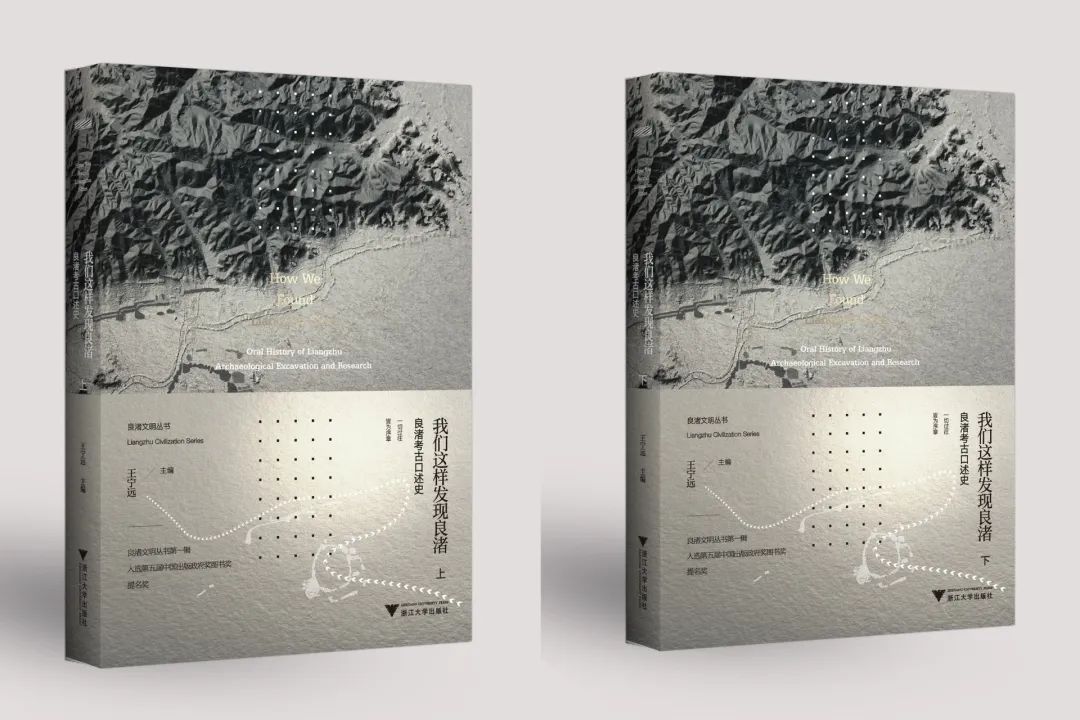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实际上它还有后半句:“但事实的真相只有亲历者才晓得”。
1999年,我在单位阅览室看到这年《农业考古》第3期上有我所牟永抗老师《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的文章,忽然发现文章很多地方被人用很细的铅笔做了批注,对很多细节提出了反驳。我马上猜出这应该王明达老师注的,因为当时考古所里这段经历的亲历者没别人了。我当时就很感慨,才过了十几二十年,那么多细节就有不同说法了。我觉得这个批注本身就是珍贵的学术史材料,于是马上请资料室的同事收藏好,换一本新杂志上架。据了解,这个批注本现在还收藏在我所资料室。
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工作经历及时记录下来很有必要。
考古工作提供的成果,多是出土文物以及报告、论文,都属于“果”,那它的“因”是什么?考古工作很多生动的过程和细节,不会出现在报告和文章里,只会存留在发掘者的回忆之中。把工作中的所思所想和过程记录下来,也是学术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2000年我开始从事良渚考古,良渚遗址的考古掌故以往零零星星听前辈同事们讲起过。不同人的表述也有出入,也缺乏系统性。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媒体对良渚的关注度大大提高。有很多人请我们讲述良渚的考古故事。当时我有过一个想法,想请反山、瑶山这些重要遗址的领队本人到遗址现场做回忆与讲解,同时把当时发掘队的成员都叫拢,现场相互补充纠错,记录下来当作一个标准版的发掘记,这样应该会更加准确、完整,也更生动。
当时我开始做过一点口述史的尝试。摄录了技工祁自力讲述勘探寻找良渚城墙的经历。为了了解莫角山和古城地貌的变迁,找了一个亲历的民工讲述古城西墙白元畈土墩“文革”期间取土的过程;还找了大观山果园的退休老职工回忆当年对莫角山地貌的改造。至于考古领队现场叙述这个事情,曾经和王明达老师提起过,但是因为没个专门项目,后来七拖八拖就没做。2013年后,因为建古城遗址公园,里面的村子都搬迁了,反山和莫角山和发掘时的环境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这个劲头就没有了。后来牟永抗老师去世了,我又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拖。当时余杭区政协要组织写一批良渚考古相关的回忆文章,所以我在写《良渚水利系统发现记》的时候,就把王明达、赵晔、丁品、方向明等先后参加过塘山调查发掘的同事都请过来,沿当时发掘点走了一遍,大家现场讲述,记录下来,回去再核对档案资料,据此整理、撰写水利系统发现史。这种记录方式比个人的回忆准确性高,但是要兴师动众,后来也就没有机会再做了。
申遗过程中,有一次在八角亭工作站,负责良渚博物院展陈设计的复旦大学高蒙河老师曾经很正式地建议我们说,良渚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江南小镇,最后经过了八十多年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最后走到了今天,是一个很成功很典型的案例。良渚考古是全面的考古,不仅要把考古成果介绍给大家,还应该把整个考古思路、过程、方法等做全面的记录和总结,给全国考古界做参考和借鉴。我当时深受启发,意识到之前我们有点自娱自乐的记录,它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良渚考古本身的学术史领域,还可以有更大的价值。
正好浙大出版社的王雨吟编辑约我写个良渚考古口述史,我因为这个原因,马上就答应下来了。但是项目开始后我又有点后悔,因为我很纠结于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最初设想是在全体发掘人员集中口述的基础上,再去核对档案和文字材料,把细节尽量还原到真实状态。但是发现做起来实在太难,要再像塘山那样把各遗址的发掘成员都凑拢去现场,再去全面查阅各种文字档案,实在是一件太过艰巨的任务。只能退而求其次,请发掘领队(或执行领队)主述。领队当然是对细节过程了解最多的人,但是采取他一个人主述会不会有各种原因导致回忆偏差?我曾经很长时间纠结于此,缺乏信心。
后来我自己经历一件事情,对这点终于释然。2019年7月6日的那天,我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亲身经历了良渚成功列入世界遗产的全过程。但是等我回国后,偶然看了会议的实况录像而获得的感受,和我现场的感受居然有很大差异。从直播录像剪辑的画面看,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会场听着大会主席用英文宣布申遗成功,看见敲锤子,然后大家开始欢呼。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坐得很远,看不清主席台,大家戴着耳机,听到的是干巴巴的中文同声传译,并不是大会主席的英文原声,我们欢呼是有延时的。这件事情就启发了我,那种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我们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的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不同的。它们是对同一真实事件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但都是真实的历史。所以因此,我对口述史中叙述者可能存在差异,就不再纠结了。此后的工作就按部就班地开展起来了。
我们记录的方式采取线下或线上录音采访,由被采访人自由讲述,几乎不加以干涉。然后用语音识别软件转成文字。再调整下顺序形成初稿,以便符合阅读逻辑,避免叙述者天马行空。初稿提交给被叙述人修改后,最后定稿。对于讲述内容除明显的时间、地点等错误硬伤做了备注外,对文字不刻意做核对和修改。录音文字大部分由我整理,姬翔、宋姝、张依欣等也做了部分工作。
口述史内容最初的时候计划只涉及良渚最重要的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古城、水利系统等几个“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来发现如果再补充点早期施昕更等的工作,以及良渚庙前、卞家山等其他重要项目,实际上可以涵盖良渚八十多年的整个考古历程,所以就扩大了口述史的内容范围。
实际工作中,我是先找王明达先生录过好几次,断断续续延续有一年多时间。后来专门找了刘斌、赵晔、丁品、芮国耀、陈欢乐、葛建良等做了录音。牟永抗先生这期间已经不在了,我根据他早年的录音整理了部分相关内容。施昕更的部分,是根据姚今霆先生编撰的施昕更年谱、西湖博物馆董聿茂馆长的回忆文字,加上施昕更发表的文字和书信来梳理,最后我来做一个整理。
这个时候我发现良渚考古的脉络已经比较清楚了。又考虑到在良渚古城发现以后,我们还做过很多的多学科研究,对认识良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多学科研究有很多其实是我自己负责或参与的项目,过程我比较清楚。所以又把动物、植物、遥感、地质、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内容纳入到口述史中。先后采访了董传万、罗以达、袁俊平、赵晓豹等外单位的参与者,以及我所的郑云飞、姬翔、宋姝等科技考古的同事。
国际合作是良渚考古的重要内容,其中以与日本金泽大学中村慎一先生领导的团队合作最为系统。但是因为疫情,这两年他们也来不了,所以只能以我的角度做简单的介绍。
口述史中古城、水利系统、反山这几个项目,发掘领队曾经发表比较系统的回忆文字,这次就以之前的文字为基础,补充了发掘者口述的一些细节。其他部分是重新录音和整理的。因为瑶山是盗掘发现的,考古所介入较晚,所以这次增加了当地政府部门和文物工作者王寿坤、颜云泉的回忆。录音文字整理完以后,经审读和多次修订,确定最终文稿,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叙述者本人的意思。
口述史大致的截止时间是到古城申遗为止,部分延续性的科技考古工作则叙述到2021年。限于篇幅,近年主要由第四代考古人做的工作,比如遗址系统勘探、姜家山、钟家港、北村等发掘工作本次未及收入,还是留待未来由他们自己叙述吧,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历史。
如果把良渚遗址八十多年的考古史当成一篇文章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起、承、转、合四个段落。我们的口述史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来编排的。
第一个阶段:起。这个阶段是施昕更1930年代发现良渚遗址,并将良渚视为山东四龙山黑陶文化南渐的一种文化。如果用一个关键字来总结这个时期的话,我觉得这个字是:“乱”。因为良渚第一次考古发掘在1936年年底,接下来1937就是“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件”,很快杭州沦陷,施昕携带书稿,踏上了逃难的路途,1939年病故在瑞安。所以施先生是赶在战火烧到之前的那一刻,抢一样地把发掘整理工作做完,在流亡路途中把考古报告出版的。所以整个是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过程。
那么建国以后和一直到1986年之前,可以算第二个“承”的阶段。整个良渚文化区内早期主要是延续施昕更时代的器物研究。后转入考古年代谱系研究,1959年从龙山文化中区分开来,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逐步建立本地区马家浜-崧泽-良渚的年代谱系。而同为良渚文化分布区的兄弟省市江苏和上海,这一阶段则发现了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福泉山等大墓,确认了原来一直被视为周汉时代的玉器实际属于良渚时代。得出良渚大墓埋葬于土筑金字塔之上的认识。本时期的杭州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不多,亮点很少。前辈们几乎白手起家,缺人、缺钱不说,中间还经历了长期的政治波折,其中之艰辛困苦,自不待言。特别是像牟永抗先生,王明达先生他们在政治大潮里面都经历过下放等很多的波折,这个阶段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难”。
1986年,以反山发掘为标志,良渚考古进入了“转”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堪称“开挂”的阶段。反山之后,良渚遗址一改以往几十年暗淡的表现,瑶山、莫角山、汇观山、塘山等等重要发现接踵而来,这些发现都是“七五”或者“八五”期间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发掘证实发良渚地区是整个区域内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个阶段的关键词,可以说是“惊”。而且从反山发现以后,就提出了“遗址群”的概念,良渚考古的研究逐步进入一种整体性的大遗址考古的视角,接下来与它匹配的遗址保护也转向整体性保护的一个正确道路。所以从发现、研究还是保护上,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非常契合“转”这个字。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以后的良渚考古,可以称为“合”的阶段。这时我们已经发现了古城的三重结构和外围水利系统的格局,整合以往的认识,大开大合,把遗址群里的这么许多遗址点,还原其真实的功能结构,从遗址群时代跨入了都邑考古的阶段。这是对遗址群这种模糊的大遗址功能的整合和提高。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宏”。同时在这个阶段以后,良渚已经不不仅仅是传统的考古了,开始大量利用多学科合力对良渚进行全面的研究,进入全考古的阶段,也称得上是一种“合”。
201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良渚文明丛书”中,同事朱叶菲有一本《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曾经系统梳理过良渚考古学术史。那么这本口述史可以理解为它的亲历者口述版,对比阅读两书或许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另外,近年电视媒体制作过很多关于良渚考古的纪录片,博物院和媒体公司做过很多短视频,能帮助读者更具象地了解良渚和良渚考古。我们征得节目版权方的同意,在前言部分放上央视10套《探索发现》栏目的《圣地良渚》(上下集,时长78分钟)和浙江卫视《良渚文明》(5集,时长190分钟)两部纪录片的链接二维码,可以先看视频,对良渚考古有个整体认识,再看本书。另外在具体的章节中,也插入良渚博物院和江苏兆物公司制作的短视频,希望对读者了解我们文中涉及的各考古项目背景有所帮助。
跋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口述史到这里戛然而止,显得有些突兀。但是良渚考古是一条河,会长长久久地流下去。未来的良渚故事,会有下一代来讲述。
不知道读完这本口述史,读者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对我来说,是感动。
八十多年,太不容易了。
我们每个良渚考古人,身处不同时代,性格秉性各异、人生际遇也大不相同。但是通过口述史的整理,我忽然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是“真”——性格上纯真,学术上求真。
记得采访中,牟永抗先生多次哽咽,情绪难于自已:“我不敢讲我自己的学术有多少高,但是我是纯真的,这条我敢自评。”刘斌一向很儒雅沉稳,回忆起文物被破坏的往事,忽然变得非常激动,忍不住爆粗口。方向明一向很刚直,当年看见辛辛苦苦清理的木构水井塌方,直接掉下眼泪。我也知道王明达老师与牟永抗先生几十年间多少有点纠葛,这次王明达老师在结束他口述史叙述的时候,最后对着方向明、芮国耀和我,特别加重语气强调:“不管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牟永抗是浙江考古的学术带头人,这样的地位应该承认的。”
真情流露,是为真人。这本书里的叙述不可能都真实无误,但是我可以保证每个叙述者对我都是敞开心扉、直言不讳的。与外部的采访者不同,我自己就是局内人,问题相信也能问到点上,尽管很多内容无法百分百呈现在这里。
对于口述史,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二十几年前的念想,一直不了了之。今天终于一了了之,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最后要特别感谢浙大出版社和王雨吟、赵静两位编辑,你们的敬业和热情,使我们有机会把良渚考古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希望这不仅仅是敝帚自珍吧。
王宁远
2022年12月13日
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
(图文转自:“浙江考古”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