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遗产视野丨我们需要更多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声音
笔者认为,与单纯的称颂或贬低官方遗产话语不同,一种新的遗产话语可能成为未来中国遗产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一些珍贵的、个别的在地实践案例,正在进入公众视野):由在地遗产精英和当地居民、地方保护机构合作形成的新话语模式,有可能弥合官方和民间话语的隔阂。
对于一个生产遗产的大国,我们希望这样的反思,来的早一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其中旅游业总收入达到2.5万亿元。到2015年,中国共拥有世界遗产48项,总数居世界第二,是30年来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数量来看,中国已经是遗产大国,从经济活动角度,遗产保护与利用带动文化产业、旅游业甚至房地产行业发展,从而驱动城乡经济发展,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看起来,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正在逐渐进入“遗产纪元”。
以上这个开头,会让我们想起RodneyHarrison在他的著作《遗产:批判性方法》中的第一章,章名为“遗产遍地”。作者描述了纽约的周一午餐时间,穿过切尔西市场(由饼干厂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商业地标)后,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被遗址、纪念碑、挂牌文物、生态保护区等包围,历史遗产如此普遍、遗产保护成为了文化现象和全球趋势。

饼干厂改造而成的纽约切尔西市场
出人意料的是,作者把这个现象作为反思的基础,在下面的章节,作者致力于将遗产放置在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语境下,讨论“遗产危机”:遗产是如何在全球化、去工业化背景下大行其道,而国际遗产保护组织主导下的价值观念又可能带来哪些风险。

饼干厂改造而成的纽约切尔西市场,是当地享有盛名的购物地标。
透过Harrison,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群人:“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在西方正在逐渐形成。这个学术共同体包括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约克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学者。在一个遗产行业已经成熟乃至饱和的社会,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遗产保护研究的学术最前沿。
在一个问题上,中国的遗产情境可能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目前不是保护的太多,而是保护太少。但如果仔细阅读这些作者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讨论的话题,同样发生在中国,这值得我们深思。而且,遗产行业的成熟乃至饱和,是我们终究会面临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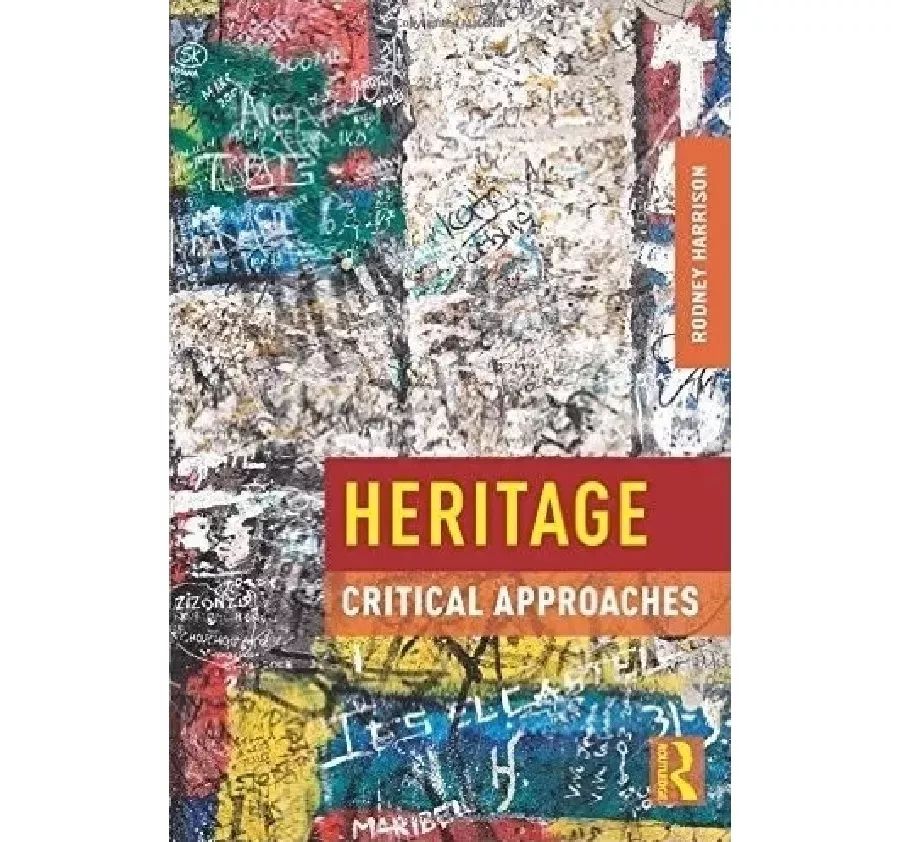
Rodney Harrison的作品《遗产:批判性方法》
国外的批判性遗产研究对于中国同行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呢?或者说国外已经取得了哪些进展?
第一,“批判性遗产研究”将遗产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
对遗产的理解不同,构成了居民共同体与技术专家共同体之间最为核心的矛盾关系。在社区层面,遗产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作品”,这构成了遗产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但在公共政策、法律法规和管理实践中,这恰恰是被忽视的内容。遗产是一个文化过程,是意义创造的过程。因此,遗产不再是一个物品或者地点,而是一个非物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文化价值观被辨识、讨论、拒绝和确认。因此遗址之上的行为比这个地点本身要重要得多。
另一方面,学者们常常以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分析,“遗产保护”的官方活动,是如何把来自过去的材料进行选择、生产、消费的。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力量,政府常常把遗产作为施加其意识形态、历史观点、民族观念的工具,事实上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上升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遗产保护的在西方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同时,遗产的生产和利用,往往以经济利益、产业发展为衍生物、甚至是遗产开发动力,由此可能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矛盾。在此过程中,“原真性”也是一种事实上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社会建构,成为学术话语自我建构的工具。遗产批判的基础,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文化是动态社会过程”的观察基础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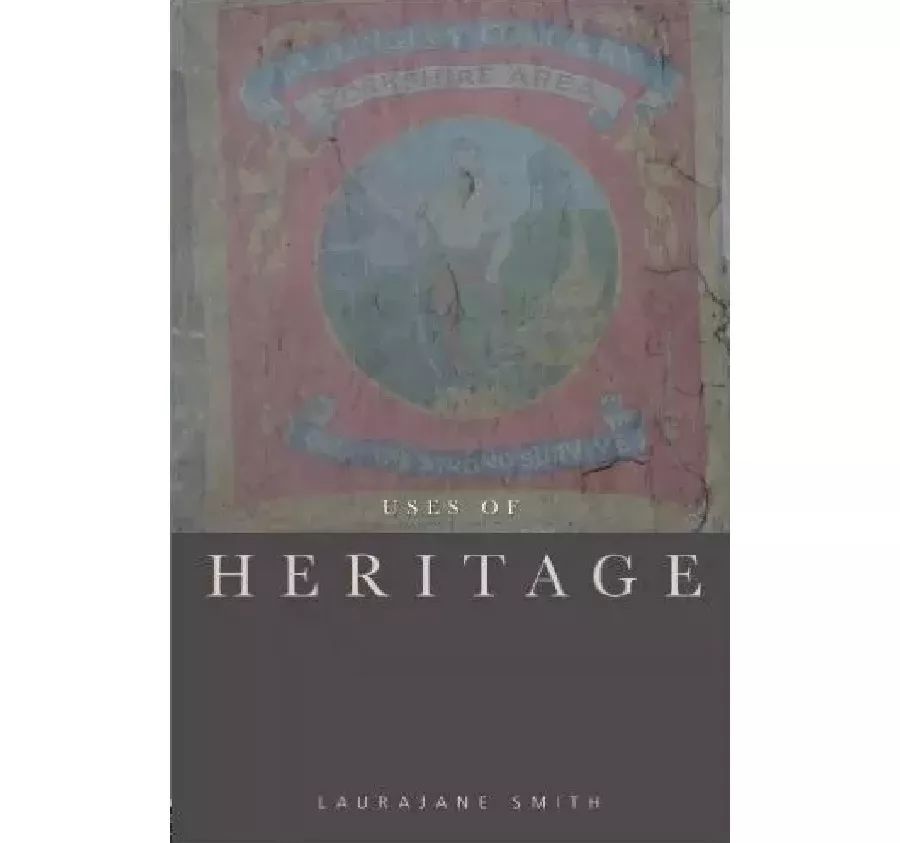
LaurajaneSmith作品:《遗产的作用》,是批判性遗产研究的经典之作
第二,“批判性遗产研究”对“官方遗产话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发展出一系列的学术工具。
什么应该保护、如何保护,这本身应当被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来看待。在当今遗产实施过程中,从国际性的遗产保护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国家级和地方性的文物局,与从事遗产保护的技术精英,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遗产话语权,这种权力话语,认定哪些对象值得保护、主导保护的过程,并且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价值等级”评价标准。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地遗产话语”,恰恰是生活在遗产中的当地人,在遗产如何保护中,拥有最少的发言权。
批判遗产研究事实上可能受到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宏观与微观、社会与社群,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问题,成为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因此构建出两种话语,并进行讨论,就成为了前提。
第三,“官方遗产话语”对日常生活、社区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没有一望而知的效益的遗产保护计划容易受到政府冷落,有所谓重要性和产值的计划往往被政府利用为工具,这一过程中受到最大的影响的是被迫迁离的居民。一系列长期的、在地的人类学研究的案例证明:在一些地方居民社区与遗产形成了非正式的共居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未诉诸文字,但居民在事实上承担了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保护责任。在这些地方官方遗产话语常常篡夺居民对遗产意义的解释权,并且剥夺居民对遗产的使用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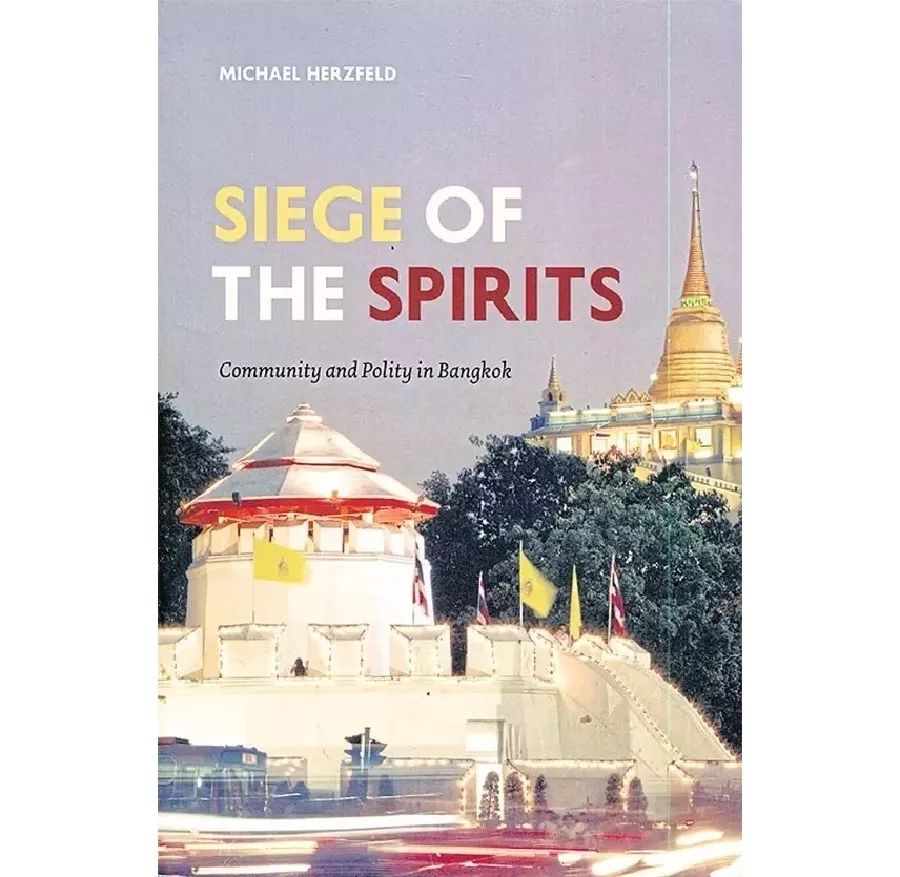
在《Siege of the Spirits》一书中,哈佛人类系Herzfeld教授讲述了曼谷老城居民共同体抵抗遗产当局征收的故事,用深度的人类学研究诠释了民间话语中的遗产实践。
遗产保护中,常常被用以提供保护合法性的“记忆”、“身份”,也成为学者反思的对象。记忆是具有流动性和复杂性的,纪念物、遗址却常常被用来作为记忆和遗忘的文化工具,通过层层的记忆来固化而形成身份。然而身份本身是也是流动和多样的,因此这又开启了对身份建构的反思。
总之,对于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警惕,成为批判性遗产研究的价值前提。民族主义使得物质文化得到过度追捧,而忽略了文化本身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而掌控遗产保护话语权的技术精英(考古学家、建筑师等),作为一个潜在的利益团体,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固话自身的利益,使得在地利益被边缘化。
笔者认为,与单纯的称颂或贬低官方遗产话语不同,一种新的遗产话语可能成为未来中国遗产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一些珍贵的、个别的在地实践案例,正在进入公众视野):由在地遗产精英和当地居民、地方保护机构合作形成的新话语模式,有可能弥合官方和民间话语的隔阂。
对于一个生产遗产的大国,我们希望这样的反思,来的早一点。
发表于《世界遗产》2016年第3期,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贺鼎,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美术遗产
美术 | 考古 | 建筑 | 文物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