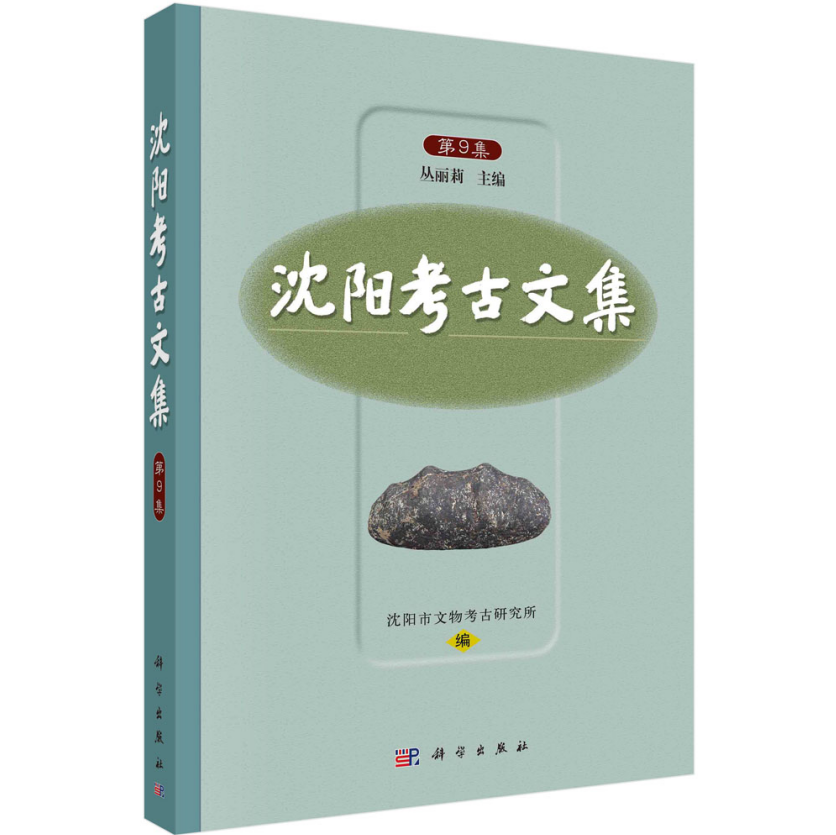研究前沿
时间、空间、秩序:田野考古摄影的维度
原作者: 宋振军,王闯 |
来自: 考古 |
发布时间:2024-8-20 22:08 |
查看: 779 | 发布者: gogoyy |

当下,摄影已经完全介入考古活动中,凡考古必有摄影。考古工作者尽力用足摄影这种工具,尤其是无人机等一些前沿技术只要产生必应用,手段不断更新,力图通过技术手段取得考古的突破。人们接受摄影在考古方面的应用,同时投入资金购买设备、培训工作人员。机械复制和现代技术给考古插上便捷的翅膀,但也出现照片最后在电脑中沉睡的状况,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从网络上文献看,关于如何拍摄的文章比较多,也有一些摄影在考古上应用个案介绍(涉及遥感或航空影像的较多),但反思考古摄影的地位和作用的少,大量摄影工作是否给考古一个革命性的促进现在鲜有人去讨论,探讨如何利用照片拓展考古领域研究的几乎没有。这时候我们应该反向思考摄影对考古的意义。
考古摄影范围很广,包含考古发掘拍摄、考古调查拍摄、文物拍摄、考古宣传拍摄等,这样的分类又不是完全的并列关系,有的时候有交叉,如发掘和考古调查中也涉及文物的拍摄。本文“田野考古摄影”着重指田野调查和田野考古过程中为了论证或揭示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的摄影活动,不含展示和宣传作用。
一、摄影在中国考古中的应用
摄影在考古上的应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应用主要是外国人。
中日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于是大批日本学者来中国进行考古或者考古调查。最早使用相机进行考古的是鸟居龙藏,1896年也就是摄影术公布57年后受东京帝国大学的委派,他带着相机到台湾进行人类学、考古方面的调查。1901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小川一真作为摄影师随同东京帝国大学博士伊东忠太、土屋纯一、奥山恒五郎到北京考察,拍摄了紫禁城及其他一些宫殿楼阁的建筑照片并出版了画册《北京城写真》。1902~1914年大谷光瑞率队分三次前往和田、库车、吐鲁番、西安,发掘吐鲁番、楼兰、库车等地古迹。1915年香川默识将大谷探险队三次所获文物、文书,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编为《西域考古图谱》,选图600多张,首次公布了大谷探险队所获的西域考古相关历史文物、文献。1922年关野贞、常盘大定、田中俊逸、外村太治郎在调查天龙山石窟遗迹时,指导专业摄影师平田饶精心拍摄,“1924年,(关野贞)委托庆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甯超武去再次摄影,1925年常盘大定委托甯超武、赵青誉与太原美丽兴照相馆再去拍摄”。1936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考察龙门石窟并于1941年出版《龙门石窟的研究》一书。
除日本学者外,骗走大量敦煌文物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1907年编著了《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详细介绍了第一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探险的全过程,包含300多幅图片及地图勘测图,涉及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古楼兰遗址。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及摄影师一行人等短短数月间遍历我国河南、四川、山西、山东、陕西、辽宁、北京等地名胜古迹,采集了至可宝贵的一手图文资料(石窟造像、金石拓片等),归国后于1909年在巴黎发布了《中国北部考古图录》(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另一位法国汉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于1909年、1914年和1917年先后多次参加中国的考古远征,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拍摄并出版了《谢阁兰的中国考古摄影集》,内含照片数百幅,地点涉及明十三陵、四川、陕西、南京、杭州等地,题材多为石窟造像、陵墓石刻、古碑汉阙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于1920~1924年出版了《敦煌石窟》(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收录1908年他的考察团从新疆进入敦煌所拍摄的洞窟、彩塑、壁画等照片计约300幅。照片为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拍摄。
从目前发现的画册上看,民国以前外国人在中国的考古行为以考古调查为主,大谷光瑞、斯坦因等也进行了考古发掘,不过涉及发掘的照片较少。
从现有文献上看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一些著名考古学家比如李济、梁思永、苏秉琦及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等都把摄影作为记录考古或者古建筑调查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出版画册的较少。现在在很多地方考古所都能看到保存完好的考古底片。近些年航空摄影广泛应用于考古调查。其中比较典型的如1996年4月26日~5月28日中国历史博物馆航空考古工作小组和洛阳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地区开展了一次航空摄影考古,这是我国境内首次开展的航空摄影考古调查工作,1997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合作,以三位德国专家为顾问对内蒙古东部赤峰市等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航空摄影考古。除航空摄影外近些年来又有三维建模加入考古活动中。三维建模是以拍摄为基础通过Agisoft等软件复原立体空间,由原来的三维空间被压缩成平面转变为再以三维的影像记录三维空间。利用了摄影的纪实性、记录功能,考古过程中用相机随时记录成为常态。
考古摄影属于纪实摄影,偶有涉及艺术摄影中的并置、重构等。从网络上看几乎所有人都把摄影(含摄像)用在考古上解释为记录某一事件。和刑侦摄影一样,记录不是目的,我们要做的是证明,用考古过程的影像来证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证明可能在发掘当时,也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影像在求证的方面不追求艺术效果,即使涉及光影等也是为求证服务。摄影之于考古的意义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时间、空间、秩序。摄影是瞬间艺术,它能够使生活中的某个瞬间定格,变成永久的存在。考古是不可重复的试验,尤其是挖掘过程。有些丝织品、木制品在刚出土时能够显示出原始纹饰、文字,但是瞬间被氧化,这是大多数抢救性挖掘不能回避的问题。还有基于考古成本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把某一状态永久保留,又不能在短时间分析完全,一旦进行下一步将打破原有的迭代关系,这时候就要通过影像记录下来。考古摄影给我们慢慢思考的机会,是考古活动和摄影活动完美的结合,是把考古过程中某一瞬间或某一时间段(摄像)特定内容定格。考古过程会呈现无数的细节,摄影甚至摄像不可能把所有细节都记录下来,即使全方位记录后期使用时也没有意义。我们只能选取最有意义的点进行定格,这也就决定了考古摄影只能是碎片性的记录。考古影像记录的是挖掘时的瞬间,挖掘时的时间和遗址历史上的年代存在一个映射关系。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年代越早的越位于下层,被挖掘出的时间越晚。时间能反映灰坑的迭代关系。不过在考古过程中物件和时间又不是完全的一一映射,比如同一灰坑中出现数件文物,这些文物有的用了10年,有的用了100年,通过出土时的时间就没法判断制造的年代,这就需要后面提到的秩序来判断。文物的摆布空间同样能证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打开一个墓穴,现场的文物放置关系能够显示出埋葬时的时间关系,这也能还原墓室主人所处年代的丧葬文化。考古影像经过时间的变化能反映文物或遗迹的变化,可以探讨如何对文物进行保护。前面提到的关野贞等在调查天龙山石窟遗迹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不久这些地方就遭到以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为代表的日本人也包括一些中国人的盗割和破坏。常盘大定写道,1925年时他的学生拍摄的天龙山石窟已经是“几无幸免,尽遭破坏,其状不忍卒睹”,“有价值者已大半佚失”。而今天再翻开常盘大定的照片和当年他发出感慨时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通过影像的“凝固”能够反映出文物的破坏或者“衰变”的状况。考古摄影关联着时间的概念,在拍摄时就应该注意。比如拍摄的角度是否能反映时间的顺序。同时挖掘相邻两个灰坑,同时出土一些文物,如果在拍摄前考虑二者的时间关系,在后期研究过程中就会思索两批文物的年代关系。反过来如果拍摄时不注意,考古记录又是分头写的,等整理文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这批文物的时间关联,更不会找出问题所在。“目前的状况依然是历史学家没有足够认真地把图像当作证据来使用……使用摄影档案的历史学家人数相当少,相反,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依然依赖档案库里的手抄本和打字文件。”在考古调查时更应该注意前期拍摄的图片,最好能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视角再一次拍摄。这样对比就能发现环境变化情况,遗迹被破坏的情况,有没有必要抢救性挖掘,如何进行保护等。在遗址和文物保护方面如果能够生成时间-衰变数学模型则是最理想的。考古是现代与古代的对接,考古摄影是用现代的时间反映历史上的时间。这两个时间的对应关系非常复杂,仅有部分保存良好的墓葬是历史上某一特定时间原始状态的完美呈现,大多数场合我们见到的是灰坑、破碎的陶器等都是原始人遗弃的东西,还包括盗墓以及因自然原因造成的挤压、冲刷等,这也就给我们拍摄时确定时间关系带来了巨大的难度。拍摄过程是将三维空间转换为二维空间的过程,所以拍摄离不开空间。考古发掘是一个“镂空”的过程。把覆土等不必要的部分剔除,让文物、痕迹等显露出来。通过挖掘的方式不断探究遗迹遗址内部结构,在挖掘过程中会给我们呈现出不同的剖面,这个剖面显示着灰坑的分层、文物的摆放等关系。通过影像记录这些剖面的分布关系,以此能够推演出一些内容,比如通过墓葬内部器物的分布看原始社会尊卑关系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形成稍纵即逝的立体空间。这个空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除了建模外,大多数照片都是形成二维影像。这就引起一个问题,平面的影像能否通过空间想象变成一个立体的空间,这是考古摄影需要解决的问题。考古过程中不可能仅挖一个探方,经常是多探方同时跟进,通过肉眼观察我们能了解不同探方的关系。而拍摄就存在这样一系列问题:同一时间段,是否多探方进行拍摄;拍摄后的照片能否反映多探方间的关联;不同探方的灰坑跨界怎么通过图片反映出来。最关键的是同一时间内不同空间发生的事情,脱离考古者的回忆别人能否读懂。考古摄影的空间还体现在不同地区的遗迹对比上。在赤峰的阴河两岸分布着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包含一些古城址,还有大量的陶片。这些遗存间有没有姻缘或者是继承关系,他们之间有没有器物的交换,一些器物是否产地一样,古城的建造是否有同一的工匠按照统一的规格。通过不同空间的影像对比可以揭示不同地方的类属关系、姻缘关系。这样看来在摄影过程中考虑空间问题远比时间问题复杂。考古过程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拍摄的图片动辄几百几千张,空间的变化不能完全靠记忆。在通过影像呈现空间状态时能让人瞬间看明白最关键之处。关于空间就涉及摄影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主体和陪体、视角、透视、光影、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在拍摄过程中广角镜头是能够解决空间狭小的唯一办法,但产生的畸变改变了空间现状。通常情况下广角镜头主光轴周围变形很小,四周大,所以可以通过这种思路去解决。同时目前的全景VR可以通过动态效果解决变形的问题,又能随时展示空间的变化。航空摄影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主要解决从高角度看考古现场的问题,这是普通相机很难实现的视角。原来在低角度看不出来的效果通过航空影像一目了然,尤其在大型遗址调查时。通过航空影像我们能看见考古符号间的构成关系,空间摆布关系。包括洪水遗址、色彩的区别、植物标记、土壤标记、潮湿标记、耕地上的农作物标记、谷类庄稼标记的变化过程等。建模和考古视频是体现空间关系的最好手段。在中国农村一个地区的房子大致相同,因为房子的造型、大小、结构、样式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主要决定于气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现在主要决定于当地的木匠和瓦匠,他们虽然没有制式一说,但大都结构相同。在史前,制陶肯定不是所有地区都有的,在大甸子遗址考古过程中发掘出很多制陶的遗址,显然这里是制陶的集中点。可以想象这里制出的陶器会向周围扩散。所以对周围陶器的研究是研究当时人们生产生活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这就涉及秩序。在考古摄影中秩序包含两个方面:显性秩序和隐性秩序。显性秩序指我们看得见的,比如发掘现场器物的摆放、石头城中房子的位置规律、墓穴中祭祀品的放置原则。这些规律容易被发现,对于摄影者来说就是要把这些秩序表现出来,不需要读者再去分析。比如对古墓的拍照应该顺墓道方向逐渐进入主室,而不是杂乱的。对古城址的拍摄应该找到城门的位置、找到主要街道。通过航拍等高角度拍摄全景,凸显排列规矩等。隐性秩序是在考古现场或者通过单张照片不能发现的,这就需要对相关知识有详细的了解,并且对现场进行缜密分析。以前面提到的大甸子大规模制陶遗址被发掘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周围遗址出土的陶器和此处有关,此处生产的陶器一定会向周围辐射。所以在考古过程中进行陶器图片的拍摄和分析很关键。一个考古摄影工作者,如果能找到一些隐性秩序,他的活动将对考古结论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考古过程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不断出现谜团的过程。长期以来人们习惯重视显性结论。比如一个多年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某个墓葬中的墓志铭解决了。对于大多数隐性问题,很少投入大量精力去思考探究。在考古过程中通过秩序的分析是为探究谜团提供一个基本的方法。德国摄影师伯恩·贝歇(Bernd Berher)夫妇1959年开始拍摄破旧的德国工业建筑,并通过类似九宫格形式进行展示用以揭示相似建筑的不同,从此开启了“类型学”摄影(也被称为“杜塞尔多夫”学派)。后来又延伸到建筑、工业、器物等。类型学摄影对考古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比很容易找到相似器物、建筑等的关系。有的时候在考古现场或者是拍摄现场找不到秩序,但在后期分析照片时能发现秩序。在这里考古摄影和考古挖掘是两个并列的工作,都是揭示一些重要的规律。有秩序的很好地表现秩序,没有秩序的发现秩序是对考古摄影的基本要求。照片的拍摄者应该对以往类似考古环节了解,尤其是熟悉曾经的照片或图片,这样能够发现问题,在问题导向下拍摄更完美。比如以往考古过程中是否出现与本次出土类似的器物;可否在某个地点以同一视角不断拍摄考古进程,形成地层的对比关系。可否对一个遗址多次拍摄记录文物被破坏或者是自然风化的过程。从前面的分析上看,考古摄影并不是简单地拍摄清晰、拍摄出细节。“德亦偶从事于斯术,初也觉其易,渐乃知其难。”时间、空间、秩序是考古摄影的三个维度,它们互相关联。随着时间的变化空间和秩序都将发生变化,空间和秩序的变化一定是在一定时间段内发生的,秩序的变化一定会引起空间的变化。考古摄影是在拍摄者和观看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对研究很有意义。摄影过程很多时候是在混乱中寻找秩序。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考古过程中的摄影有两个主要问题:为考古提供证据,通过影像发现问题。考古摄影是让参与考古的人恢复考古过程中的记忆,让没有参与考古的人充分了解现场。摄影过程是通过现代影像推演原始画面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传统胶片影像或者是数字影像的机械复制。但目前考古摄影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因为考古经费的使用主要在挖掘过程。大多数考古都是重挖掘过程,轻事后整理;重现场分析,轻事后分析。一次考古要拍摄几千甚至数万张照片,除了部分重要的照片公布外大多数都在领队手中,并不能共享。这就决定了没有参与考古的人只能利用现有结论进行研究,而不能独立分析,客观上造成“使用摄影档案的历史学家人数相当少,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必须依赖档案库里的文献”。考古摄影成为挖掘的附属品,对影像的研究远弱于考古现场的直观经历和对考古现场的文本叙述。有时候摄影者并不是考古行家。摄影和考古两个环节割裂开来。摄影的过程只想拍摄,甚至想到如何拍摄出艺术效果,至于怎么用就不管了,更不用谈时间、空间、秩序的关系了。考古摄影是在恰当的时间合理反映出现场空间并能描述出合理秩序。随着考古挖掘的结束,遗迹就消失了,这些必须通过影像来反映。有的时候同一遗址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挖掘,前期的影像就尤为重要。考古摄影属于纪实摄影一类,纪实摄影一定带有主观性的,比如不同人拍摄的纪实摄影内容肯定不同,体现在时间空间上不同。还有选择的样本不同拍摄出来的效果也不同,在考古摄影里面尽量要求看照片的效果和考古现场体会到的一样,这样一个准则就能评判拍摄效果的如何。在考古现场考古人员已经对现场进行了一次心理复制,而且这种印象会留在脑海中。拍摄是对重要的信息进行第二次过滤。考古过程会给人留下大量的选题,这些选题都需要考古结束后去慢慢思考。通常在考古结束后我们要根据考古简报和留下的影像资料去重构考古场景、推断历史场景。现在很多工作都是线性的,即随着考古的每一个环节记录,如果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去翻看影像。我们要做反向工作,就是通过图像反推考古的过程和结论。像其他类型的历史证据一样,图像或至少是大部分图像在被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将来会被历史学家所使用。照片和视频都有这样的特点,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知道拍摄得不够好、不够用。图像的拍摄者不能只关心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不想将来怎么使用。考古的话语权大都垄断在现场发掘的工作人员手中,这样很容易形成他的结论权威。而这个结论一旦失误则会造成重大损失。图像可以有很多种阐释,通过对图像的不同阐释可以打破考古发掘者的话语垄断。非常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根据图像考证……”的相关文章。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图像共享的机制还没有建成。考古影像是一个系统,有的时候单凭一张照片说明一个史实是不充分的,而把这些照片串起来过程就是研究,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考古当事人。考古摄影不但要解决影像清晰的问题,更要重视在论证过程中的作用。书写历史需要历史文献、历史文物和地下发掘,考古的过程就是一次历史书写的过程,所有人都力图实现无限逼近历史真实情况。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图像和文字是相伴的。早期以图像为主,因为图像的生产相对复杂,后期以文字为主,摄影术诞生后,这种迅速生成过程很快成为人们的工具,其记录功能在很多方面得到迅速应用。历史是客观的,但是历史的书写一定带有大量的主观性。历史研究的是历史问题,而不是追求再现历史的全景。由于史料的限制,早期的很多史料并不一定准确,甚至导致某人揣测的观点被不断使用、引用,作为公理普遍运用。考古摄影的作用在于帮助揭露历史真相,矫正原有的错误观点。本文由 赵越 闫广宇 摘编自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沈阳考古文集(第9集)》之 《时间、空间、秩序:田野考古摄影的维度》。内容有删节、调整。(审核:孙莉)
978-7-03-078747-7
定价:238.00元
本集共收录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学术论文等文章22篇,内容涉及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的文物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以及辽宁省内其他文物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尤其是沈阳地域性考古学文化和沈阳地方史研究者,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者参阅。
转载自:赛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