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学术文摘丨甘青宁地区传统村落的初步研究(下)
中国文化遗产 2018年第2期
甘青宁地区传统村落的初步研究
(下)
张力智
5. 建筑遗存所显示的历史
说了这么多,最终又回到本文开始提到的农耕与游牧的对立之上。不过假使抛开上述所有社会历史因素,甘青宁地区的建筑本身也可以呈现出一条完整的历史轨迹。
甘青宁地区史前遗迹众多,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辛店等文化遗址中多有建筑遗迹,从地下竖穴、半地穴、横穴到地面木构建筑应有尽有。早期建筑多以半穴居为主,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时(秦安大地湾第四、五期)才大量出现地面建筑。最初地面建筑多在天水一带,也可见天水地区的自然环境更适合木构建筑的发展。不过不论木构或是穴居,这些建筑往往将火塘置于中心,四周布置居住和储藏空间——这与后代蒙古族、土族、藏族民居,甚至与满族民居中的“万字炕”相似。近年甘肃张家川马家塬贵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也证实——战国时期天水文明曾有中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诸多特征。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多以西为尊,在西侧设置佛堂、神位和尊位,坐西朝东容易在清晨最寒冷的时候获得日照,这也是《仪礼》中以西为尊的来源。从先秦古礼到汉代宫殿,再到辽代寺院和今天北方少数民族的住宅,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绵下来,礼失求诸野,古礼依然保存在胡虏的建筑之中。
甘青宁地区史前建筑还有一个特点,地面建筑往往在建筑外面添加一个门蓬,如后代的卷棚轩、龟头殿以及献殿一般,整个建筑呈“凸”字形的布局。考古学者和建筑史学者都认为这是为了增加室内进深,不过即使后代建筑规模、进深增大,类似的空间布局也一直保存在当地庙宇建筑之中。本文涉及的天水街亭村城隍庙大殿、天水新阳胡家大庄村清池观大殿、互助土观村菩萨寺、泾源北伍家村清真寺等是如此,在本文没有涉及的众多大型庙宇,无论藏式、汉式还是伊斯兰式也多是如此。这种稳定的建筑形式似乎超越了历史,也跨越了各种宗教——恒久不变的存在于甘青宁、山陕和西藏地区,《仪礼》中的“檐廊”也很可能与此有关。笔者无法解释其原因,但想必不止增加空间那样简单。
考古发掘所见甘青宁地区先秦时期的建筑传统与中原多有差异,直至汉武帝“凿通西域”,中原文明和建筑形式才大规模输入甘青宁地区。今天甘肃仍保存了汉魏时期的大量明器建筑,其中尤以武威雷台汉墓、张掖郭家沙滩汉墓出土的陶楼院最为著名(图14)。这些陶楼院常常被研究者视为汉代坞壁的缩影,它们与甘青宁地区史前遗迹大为不同,是中原移民用以殖民和避难的建筑。陶楼院平面多呈方形,外围堡墙,堡墙四角设置角楼,正中则多为住宅,另有二层仓楼和四至五层高的望楼。不过随着唐代之后甘青宁地区政权的稳定,坞壁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少见,最终退化成只会在战争年代出现的建筑,譬如民勤县的瑞安堡,以及天水地区的众多土堡之类(图15)。这些土堡中不仅没有了粮仓和望楼,有的甚至连住宅建筑都变得非常简陋——在稳定的政权下,盗匪不能在一地停留过久,应对盗匪的坞壁也就成了临时建筑。

图14/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陶楼院,此楼是研究河西古代坞壁的重要标本。(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网站www.gansumuseum.com)

图15/甘肃武威市民勤县三雷乡三陶村瑞安堡,此建筑颇有古代坞壁之风,但中心的望楼已退化成一个名为“双喜楼”的游憩建筑。(摄影:张力智)
坞壁中不见了仓楼和望楼,只剩下被围墙环绕的住宅厅堂,这就与廊院式建筑相去不远。廊院式建筑是北朝以来宫殿、重要庙宇和重要住宅建筑最为常见的建筑形式。今天敦煌壁画中保存了隋、唐、五代及宋朝建筑的诸多图像,其中大部分都是廊院式建筑。但随着后代围廊转化成厢房、倒座,廊院式建筑迅速转化成为合院式建筑(见前文图03)。合院也是甘青宁地区今天主要的建筑形式。

图16/敦煌壁画中举折很大的屋面,以及近似平出的屋檐。(图片来源:《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敦煌壁画中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建筑图像中常常出现斗栱、椽子和飞椽的仰视形象,这些都不是透视和画法,而是因为建筑出檐过于平缓所致(檐下构件易被看到而已),这也是甘青宁地区乡土建筑的重要特点。甘青宁地区气候寒冷,平缓的出檐能够让更多的阳光照到室内,维持室内温度。平顶建筑水平出檐自不必说,甘青宁地区的坡顶建筑为了做出平缓的出檐,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大式建筑一般将坡顶举折增大,加大坡顶曲线,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就是如此(图16);大部分小式建筑和宁夏地区的大式建筑将坡顶做成折线,金柱以内做坡顶,金柱以外水平出檐,如宁夏中卫高庙、兰州部分河口民居等等(图17);还有一些小式建筑会用飞檐调节出檐角度,飞檐明显上翘,如宁夏吴忠董府;河西和兰州地区的民居大门更为夸张,常用平顶来伪装坡顶——平顶正中立起极高的正脊,两侧立起三角形的山墙,从山墙看好似坡顶,其实只是平顶而已(图18)。简而言之,平顶和坡顶结合时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举折”方式,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举折”提供了契机。从现有实物遗存来看,中国建筑的举折形成于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入侵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早期建筑学者认为这种弧形“反宇”屋面是对北方游牧民族帐篷曲线的模仿——这种解释过于浪漫和形式化了。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如何不让中原地区的大屋顶过多遮挡日照才是关键,举折只是北方平出屋檐与南方坡屋顶的嫁接而已。

图17/宁夏中卫高庙中举折巨大的屋顶,以及近似平出的屋檐。(摄影:张力智)

图18/兰州西固区河口村住宅建筑大门,实为平顶,但伪装成坡顶。(摄影:张力智)
平顶可以改造坡顶,来自中亚的圆顶同样可以改造坡顶。元代之后,中亚工匠、伊斯兰教和中亚建筑风格流入中国,对西北,尤其是穆斯林(回族)的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甘青宁地区的回族民居、清真寺依然多用盔顶和卷棚顶,如宁夏吴忠董府住宅建筑,青海循化孟达清真寺,甘肃临夏大拱北、张家川宣化岗拱北等等都是如此(见前文图12)。

图19/宁夏固原市回族民居,当地回族“高房子”随处可见。(摄影:张力智)
还有一种普遍的建筑形式——高房子,也可能是中亚建筑形式的变体。民居史中的高房子特指宁夏和陇东地区的回族住宅,这些住宅多为一层,只在院落一角建二层小阁楼,外置楼梯上下,据说可以防御瞭望,也供回族老人礼拜诵经,今天则多是用来堆放杂物(图19)。事实上除回族之外,甘青宁诸多民族也都有类似的高房子。兰州河口汉族住宅正房当心间上常常建有类似的阁楼,通过院内的梯子上下,阁楼内放置家庭祖先神牌(图20)。同仁土族也有类似的阁楼,建在二层正中间的用作经堂(历史上土族儿童都需出家为僧,这些经堂就供家中僧侣回家时居住),或建在二层西北角的供奉萨满神祇。互助土族庄廓门侧也有类似角楼,也需要通过院落中的爬梯上下,据说从前是老人家监视家中活动的所在,现状也多用来堆积杂草(图21)。由此可见,高房子是甘青宁地区一种稳定的建筑形式,既可用于防御,又可供奉神灵,还可堆放晾在房顶上的粮食,只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功能不同罢了。新疆、中亚和西亚地区类似的建筑也有不少,甚至于古代西亚联系紧密的闽南地区,也有大量类似的“高房子”——当地称“角脚楼”“埕头楼”,但所有这些都还是类似而已,其传播影响关系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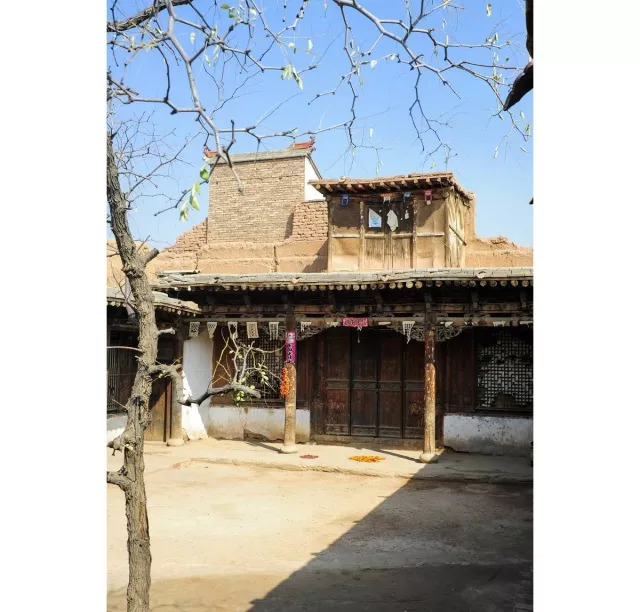
图20/兰州西固区河口乡河口村北街住宅,正房当心间上方有一“高房子”,用于供奉祖先。(摄影:张力智)

图21/青海互助土族风情园中土族民居,远处可见此庄廓民居亦有一“高房子”。(摄影:袁周)
甘青宁地区建筑对多元风格的融合,更突出地表现在建筑装饰上。蒙元时期大量中亚工匠迁入汉地,到了明代又有大量江南工匠迁入藏区……蒙藏两族的毛毯和纺织品装饰,中亚的琉璃、金银器和玻璃装饰,汉族的木雕和砖雕装饰全部汇集到甘青宁地区。譬如甘青宁地区常见的砖雕和木雕垂花装饰,其实就从中亚丝织品帐额演化而来(图22)。青海地区色彩浓烈的纯色琉璃装饰,则是西亚矿物颜料、琉璃烧制工艺与藏族审美趣味的融合。再譬如唐卡,一种结合了中亚的细密画,藏族用色以及汉族的工笔技法的艺术形式,大面积地装饰在青海地区的庙宇建筑上。上述装饰甚至影响和改变了甘青宁地区的建筑结构。举例而言,西北地区木构建筑的斗栱繁复而细密,出跳极多,又有几何整体性,明显受到伊斯兰审美趣味的影响;西北地区建筑檐下垂花、花板装饰很多,河西走廊地区甚至出现了花板代栱的做法,花板代替承重构件。与此类似的还有天水地区的垂花门,门柱两侧承托屋面的带状装饰显然也是从丝织品挂落演化而来。总而言之,甘青宁地区的建筑装饰色彩浓烈,细密复杂,与中原地区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图22/宁夏中卫高庙,甘青宁地区建筑,尤其是回族民居建筑中使用垂花装饰很多。(摄影:张力智)
6. 总结与研究视野的拓展
在建筑形式和装饰的分析中,我们又一次回到了本文的起点——中原与西域的融合。类似的对立范畴——农耕与游牧、河谷与高原、湿润与干旱、坡顶与平顶、木构与夯土、封闭与开放,也构成了我们对甘青宁传统村落和乡土建筑的理解框架。在此框架下,本文特别强调了两条研究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甘青宁地区建筑、村落形式与西域建筑传统的联系。譬如建筑形式方面,我们谈到了“高房子”和“盔顶”的使用;建筑装饰层面,我们谈到了木构垂花花板对西域丝织品装饰的表现。城市布局方面,庙宇在城镇中的重要地位等等。城乡关系方面,我们也谈到了甘青宁“小村大镇”与欧洲中世纪的相似性等等。由于学力和篇幅所限,上述所有线索和脉络都无法在本文展开,但它们却是未来学术研究的潜力所在。
其实中西交流之类的话,在甘青宁地区的人文历史研究中已经相当俗套了,但为何在既往村落和乡土建筑研究中,连这样的俗套框架也建立不起来呢?这是因为甘青宁地区的村落和乡土建筑呈现出一种与关中、新疆都有较大差异的风格——除了天水民居与关中有些相似之外,其余地方的民居与中原、中亚都很不相同,完全不像是二者融合的产物。由于这样的原因,甘青宁地区的建筑研究长期无法推进,在学术史中,也仿佛关中、新疆与西藏之间的一片模糊空白。
这里就要指出本文所强调的第二条线索。
第二条线索,也是更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甘青宁地区建筑形式与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之间的联系。文中我们谈到了以西为尊,口袋房在北方少数民族住宅中普遍存在;互助土族住宅向心式布局与蒙古族萨满信仰的联系;以及“日”字型城市在甘青宁地区、中亚和蒙古高原的普遍出现等等。说得直白一些,青海河湟庄廓与宁夏中卫民居、大同民居、张家口民居甚至远在辽东的满族民居都有若干相似之处。在农耕帝国的北方边界上,可能共享着一种此前未得足够重视的建筑类型。这种建筑类型可以与中原、中亚的建筑传统分别融合——它是文明交流的平台,也是甘青宁地区乡土建筑的底色。
视野放开,这种类型的建筑大量出现在中华农耕帝国的北方边境上(甚至中西亚地区也有发现),固然与亚洲内陆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但也与亚洲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游牧民族又好像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将地理空间大大压缩——甘肃张家川的西戎墓葬会出土西亚风格的工艺品,河北张家口的汉墓中会发现匈牙利生产的铜器,不同地方的农耕文明因这些游牧民族而联系到了一起。中原和西域并非直接碰撞,它们之间有一个持续流动的中介——只是自诩文明的人们不愿正视这些奔驰在草原上的蛮夷而已。
在此框架下,甘青宁地区复杂的民族构成只是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结果而已,而随着历史发展,在更“文明”的世界里,同样的流动性就会以商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回族在这一区域取代蒙古、回纥等古代民族的关键原因。而在社会功能主义的视角中,宗教也只是协调流动性与定居人群的一种方式,所以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差别也没有看起来那样大,更不要说这些宗教内部的诸多教派了。通过这种分析,我们越过了甘青宁地区复杂民族和宗教所构成的障碍,异彩纷呈的历史迷雾背后,(象征流动性的)商业和(整合流动与定居的)宗教才是甘青宁村镇的支柱。
事实上在欧洲城市史叙述中,欧洲中世纪城镇发展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商业和宗教——甘青宁地区的城镇在此层面上似乎具有“普世”的意义。只是由于中原帝国的驻军,那里的城镇才走上了与欧洲城市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正因如此,这些城镇的意义才更为重要——我们得以从中窥视到了“中国城市”背后的军事本质,当然在形式上,这也可以视为中原与西域交流中一个更为深刻的注脚。
由于甘青宁地区相关研究基础薄弱,也由于笔者学力所限,本文论述也只能止步于此。近些年来乡土建筑和传统村落的研究虽然繁荣,但相关研究框架依然是刘敦桢、陆元鼎、陈志华等先生们创下的。前辈学者受时代所限,往往对华南、华东地区研究较深,研究构架也更为系统,华中和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就已相对薄弱,更不要说长期不被关注的西北、西南等地了。尤其是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交界混居的宁夏、甘肃、四川、湖南和广西等省区,受复杂民族历史的影响,村落和乡土建筑研究碎片化相当严重,个案研究自说自话,互不关联,整个地区也变得毫无重要性可言,笔者在进入甘青宁地区的研究时,就被这种碎片状态所深深困扰。在近一年的研究中,被甘青宁地区传统村落和乡土建筑的特点所激发,笔者尝试探索一个更有解释力、也足以呈现甘青宁地区重要性的研究视野,这也就是本文强调商业、宗教对村镇规划的主导的原因,也是本文强调中亚、北方少数民族习俗影响建筑布局的原因。只是研究视野越开阔,个案研究就越是显得不足——本文的所有叙述只是一些稀松案例所勾连出来的线索而已。抛砖引玉,真心希望更多同道能够意识到现有研究框架的不足,也真心期待相关研究能够跳出一村一地一省一族的藩篱。唯有如此方能呈现甘青宁地区传统村落和乡土建筑的重要性,当然对于西南、东北的研究也是一样。
最后,笔者在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受益颇多,在此特别说明。
全文完,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编辑:孙秀丽
排版:段牛斗
题图:甘肃瓜州锁阳城遗址
张力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助理教授。
美术遗产
美术 | 考古 | 建筑 | 文物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