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青海吐蕃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青海吐蕃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徐承炎(塔里木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
夏吾卡先(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关键词]青海;吐蕃墓葬;研究综述
[摘 要]自1982年青海地区首次科学、规范地发掘吐蕃墓葬以来,该区的吐蕃墓葬考古工作已持续30余年。其间,随着所获吐蕃遗存的逐渐增加,国内学界藉此开展了由浅入深的吐蕃墓葬研究工作。几近同时,国外学界也基于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进行了若干专题研究。系统梳理青海境内30余年的吐蕃墓葬考古工作,介绍、评析国内外学者之研究成果,对该区域吐蕃墓葬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均有助益。
7世纪初,几与李唐同时,西藏雅砻河谷的悉补野家族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政权。663年,吐蕃势力东扩之际兼并了雄踞青海达350年之久的吐谷浑。至此,吐蕃东境与唐相接,为与李唐相抗吐蕃曾长期屯重兵于吐谷浑故地,当地也因此留下了众多的吐蕃遗存。而在青海现存的各类吐蕃遗存中,又以墓葬数量为最多。
自1982年起,青海地区已持续开展吐蕃墓葬考古30余年。其间,发掘吐蕃墓葬百余座,采集文物数以万计,为学界积累了一批宝贵资料。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也藉此开展了众多研究工作,并发表论著逾百篇(部),进一步深化了吐蕃史和吐蕃墓葬的研究。笔者拟对青海地区30余年的吐蕃墓考古工作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推介和评析,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呈若干浅见。
一、1982—2000年:青海吐蕃墓的科学考古发掘与初步研究
1982—1985年,许新国陆续清理发掘了都兰县热水乌苏河北岸的血渭一号大墓和20余座中小型墓葬[1—2]。1988年,为配合李家峡水电工程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家单位发掘了化隆县黄河北岸雄先乡上班主洼村北的4座吐蕃墓葬[3]。199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化隆县上班珠哇村森岗拉尕发掘6座吐蕃墓葬[4]318。1990年,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在贵南县北部穆格滩大沙漠里的一处三角形沙漩中清理出1座吐蕃墓葬[4]321—332。1994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都兰县夏日哈乡河北村的大什角墓地中发掘中小型墓葬9座[5]。199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都兰县热水乡直尕日二村发掘中小型墓葬20座[5]26—30。1996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热水乡扎马日村血渭、智尕日村和夏日哈乡河北村什角沟等地发掘墓葬数十座[6]。1998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香加乡莫克力沟发掘墓葬21座[7]。1999年,受唐研究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都兰热水乡乌苏河南岸的中小型墓葬4座[8]。

2019年发掘的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截至2000年,青海省境内共发掘吐蕃时期墓葬90余座,然当时尚未见考古报告(或简报)发表。发掘墓葬的零星信息仅得见于《中国考古学年鉴》和发掘者的研究文章。许新国曾基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2—1985年的考古资料,先后发表多篇论文[注],在1990年发表的《缂丝织物的历史和制造技术初探——从都兰出土的缂丝谈起》中重点介绍了都兰吐蕃墓出土的缂丝织物,并探讨了缂丝的制作工艺[9];1991年的《吐蕃丧葬殉牲习俗研究》对都兰血渭一号大墓及其陪葬墓中所见的动物殉葬现象进行了解读,同时考索了这一习俗的渊源[10];同年的《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一文又对都兰吐蕃墓所出丝织品的品种、图案类型、年代和分期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11];1994年的《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一文对比研究了都兰出土的部分金银器与粟特系统金银器的关系[12]。1995年的《都兰热水血渭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一文尝试性地复原研究了一号大墓前殉马坑内出土的一件舍利容器,并探讨了舍利容器的年代和族属等相关问题[13];同年的《吐蕃墓的墓上祭祀建筑问题》一文研究了都兰血渭一号大墓的墓室结构,探讨了墓葬封土顶部建筑的功能[14];1996年的《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研究了含绶鸟织锦的类型、形式、分期、年代以及它所反映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15];1997年的《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一文探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太阳神鸟丝织品图像的来源问题,并讨论了太阳神图像所体现的东、西文化交流现象[16]。此外,王尧、陈践两位先生也曾联合发表《青海吐蕃简牍考释》一文,文章考释研究了出土于都兰县热水血渭草场两座古墓中的十一支吐蕃简牍[17]。1998年,瑞士学者艾米·海勒博士发表了《都兰考古发掘工作评述》一文,文中首次比较详细地向海外学界介绍了都兰血渭一号大墓的情况,同时也对都兰考古中出土的金银器、丝绸、木简、石狮子等文物给予了细致介绍[18]。
总体上讲,由于这一阶段公布的考古资料十分有限且部分选介研究类文章发表在了内部刊物(如《青海文物》)上,故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影响较小。国内该时段完成的两部极具影响的著作——《西藏考古大纲》和《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因受限于考古材料,也只简单地介绍了青海吐蕃墓,未及深入[19—20]。
二、2000年至今:青海吐蕃墓葬考古资料的陆续刊布与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
200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肖永明抢救性发掘了热水北岸南岸卢斯沟地区被盗墓葬33座[21]。同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发掘位于乌兰县东部铜普乡察汗诺村大南湾的墓葬6座[22]。200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清理被盗古墓2座[23]。2008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清理了1座位于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的被盗壁画墓[24]。2012—2014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玉树治多县治曲乡治加村的聂龙沟内聂龙加霍列墓群和治多县立新乡叶青村章齐达墓群进行发掘,共发掘墓葬17座[25—26]。2014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对都兰热水乡扎麻日村察汗乌苏河南岸芦丝沟东侧环山内的古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25座[27]。
自2000年以来,青海吐蕃墓的考古资料开始陆续公布。2001年,许新国介绍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1982年以来在都兰县进行的历次考古发掘工作情况,并比较详细地公布了血渭一号大墓的相关资料[5]26—30。200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公布了乌兰县大南湾6座墓葬和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2座古墓的资料。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树芝研究员公布了都兰热水墓地2000年发掘的7座墓葬之树木年轮测年数据[28]。2005年,《都兰吐蕃墓》正式出版,其中介绍了1999年发掘的4座墓葬之详细资料[29]。2017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公布了2014年在都兰哇沿水库发掘的墓葬资料[27]。2018年,李天林主编的《青海海西古丝绸文物图集——丝绸之路》一书出版,其中公布了出于青海吐蕃墓葬但现藏于海西州博物馆的丝绸资料[30]。
综上可知,这一阶段考古资料陆续公布,学界拥有了较多的研究资料,并藉此推进和深化了青海吐蕃墓葬的研究工作。具体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血渭一号大墓墓主身份及族属的研究。自2001年以来,许新国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对先前推定的吐蕃墓群之族属进行了重新考证,进而确认都兰墓群归属于吐蕃文化,墓主的族属是吐蕃治下的吐谷浑人[5][31—32]。随之青海地方史学界对以都兰血渭一号大墓为中心的整个墓群的族属是吐蕃还是吐谷浑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程起骏先后发表数篇论文,首提都兰热水古墓群是非吐蕃化的吐谷浑诸王及显贵们的墓地[32—36]。三木才认为都兰一号大墓所反映的墓葬文化是吐蕃类型,墓主身份可能相当于吐蕃赞普级别[37—38]。2003年,霍巍在《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一文中,从吐蕃治下吐谷浑邦国的地位入手,又对血渭一号大墓的墓主身份给出了以下几种推测:一是吐蕃封立的“吐谷浑小王”之类的王室贵族;二是下嫁吐谷浑的吐蕃公主;三是已投降归顺吐蕃的吐谷浑原王室残部;四乃受吐蕃支配的吐谷浑军事首领[39]。这一观点与许新国的“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族墓葬说”基本相合。同年,美籍华人王涛同样基于实地调研撰写了《吐蕃还是吐谷浑:再访都兰墓地》一文,文章通过开展热水一号大墓与其他吐蕃墓地的类型学比较,并辅以墓中所出丝织品、木材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经过校正433—642年),再结合敦煌文献中所记自633年以来吐蕃大将禄东赞及其家族是青海地区的最高统管者之史实,推测热水一号大墓的墓主是7世纪活跃于吐蕃东境的禄东赞[40]。2009年,许新国又在《中国考古60年》“青海省·隋唐时期”章节中推测血渭一号大墓的墓主身份可能是莫贺吐谷浑可汗[41]。2011、2012年青海藏族研究会先后编辑出版了两期《青海藏族》都兰吐蕃墓专辑,收录文章中以许新国先生的最具特色,其文首次公布了血渭一号大墓所出的7件古藏文木牍;又通过对墓中出土丝绸的研究,考证出大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叶,并判识墓主的族属是吐蕃人[42]。2012年阿顿·华多太发表《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一文,文章就程起骏所著《古老神秘的都兰》一书中有关都兰古墓论说部分的虚实真伪作了逐一解答,并重申都兰古墓是吐蕃墓的学术共识[43]。同年,仝涛发表《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一文,从大墓的形制、规格、出土物(丝织品、金银器)及吐蕃征服吐谷浑的历史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梳理考证,并推断墓主可能是吐蕃册封的首位吐谷浑王、薨于694年的坌达延墀松[44]。2013年,周伟洲发表了《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一文,文中对都兰血渭一号墓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枚举了一号大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提呈了个人观点,即基本认同一号大墓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族墓葬”[45]。同年,李朝、柳春诚发表《都兰热水一号大墓考古研究的重大收获——兼与仝涛先生商榷》一文,文中对仝涛先生关于墓葬的形制与年代、墓主人身份等诸认识都进行了逐一修正,并认为墓主人是吐谷浑王夸吕(535—591年)[46]。此后,基本不见对一号大墓族属讨论的专题文章。
(二)德令哈吐蕃彩绘棺板画的专题研究。2004年,柳春诚、程起骏陆续发表《吐谷浑人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出土棺板画研读》《郭里木棺板画初展吐谷浑生活》两文,文章以都兰一带曾是吐谷浑人的故乡为据,认为德令哈彩绘棺板画所绘内容为吐谷浑人的日常生活场景[47—48]。2005年,许新国发表《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一文,文中对2002年8月在德令哈郭里木乡清理发掘的两座吐蕃时期墓葬的3具木棺上的彩绘内容,即四神图、狩猎图、商旅图、宴饮图、帐居图、男女双身图、射牛图、妇女图、人物服饰和赭面现象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49]。2006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青海专辑下”“重塑历史”专栏中发表了程起骏、柳春诚、罗世平、林梅村等4位学者的《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郭里木棺板彩画临摹记》《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和《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四篇文章,诸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郭里木棺板画的内容进行专业解读。稍后,罗世平和林梅村又发表了《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和《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50—51],两文均认同墓主为吐蕃贵族。2007年,霍巍发表《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一文,文中指出棺板画反映的不是一般所谓的“社会生活场景”,而是具有吐蕃苯教特点的丧葬活动,棺板画上的人物族源可能属于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52];同年,他的另一篇文章——《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又对青海吐蕃人和入华粟特人墓葬中所见的棺板装饰传统进行了对比研究,并认为两者间存有某种联系[53]。是年,仝涛在《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一文中提出,青海德令哈郭里木发现的两座吐蕃时期墓葬中的木棺板画保留了鲜卑族的部分文化因素[54];许新国认为青海德令哈郭里木吐蕃棺具档头上所绘制的四神直接取法于中原,但又受到西方文化和吐蕃民族中不同民族成分之传统文化的影响[55]。2008年,仝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夏塔图M1、M2的左右侧板、前后档板及一块散落民间的木棺侧板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两块彩绘板画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详细考证了吐蕃棺板画的制作源流[56]。同年,王树芝等人在《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一文中对在郭里木四座墓葬采集的树轮分析样本进行了科学定年,结果显示夏塔图1—4号墓的年代分别为757、756、790和785年(或介于785—843年之间)[57]。2010年,仝涛和瓦特蒙用英文联合发表了《西藏高原北部发现的吐蕃时期彩绘棺板》,文中对国内公布的各棺板画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就其与吐蕃丧葬仪轨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58]。同年,吴晓燕又对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发现的彩绘棺板画的图像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刻的研究,并认为郭里木所见的棺板彩绘是鲜卑、羌、吐蕃、中原和西方等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59]。2012年,仝涛在《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一文中结合敦煌出土的吐蕃丧葬仪轨文书和相关的汉藏文资料,深入考释了棺板画上的丧礼图内容,并认为它所反映的是吐蕃苯教的丧葬仪轨[60];许新国发表《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的壁画墓》一文,对青海乌兰县新发现吐蕃壁画墓的情况进行了首次披露和研究[24]。2013年,周伟洲在《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一文中从郭里木夏塔图三具彩绘木棺的形制、彩画主题和画中人物服饰等角度重新考证了墓主的族属,并认为墓主为吐谷浑人,且墓葬定名应为“吐谷浑墓”或“吐蕃王朝统治下的吐谷浑墓”[45]。2015年许新国发表《德令哈吐蕃墓出土丝绸与棺板画研究》一文,刊布了目前收藏于海西州博物馆的又一彩绘棺板画资料,并对棺板画中描绘的社会场景作了详细介绍[61]。
除以上胪列的专题研究文章外,《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藏学学刊》,2007年)、《考古发现所见吐蕃射猎运动——以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为对象》(《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收录于《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读者出版集团2012年)、《西藏美术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等论著也都详略不一的涉及到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的部分内容。
(三)都兰及其周边的吐蕃墓葬、吐蕃文物之综合研究。2003年,汤惠生在《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一文中对都兰县科孝图吐蕃墓地的一对石狮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吐蕃石狮的独特艺术风格直接来自中原,14世纪左右这种吐蕃风格的石狮逐渐消失[62]。2005年,林梅村发表《青海都兰出土伊斯兰织锦及其相关问题》一文,文章对都兰吐蕃墓葬中出土的一组以鹰纹和凤纹图案为特点的早期伊斯兰织锦进行了研究,发现伊斯兰艺术中的凤凰源于唐代艺术[63—64]。2006年,艾米·海勒先后发表《公元8至9世纪吐蕃墓葬所体现的丧葬仪轨》和《评都兰考古工作:一处公元8至9世纪的吐蕃墓葬》两文,前文对以都兰血渭一号大墓为主的科肖图吐蕃墓地所反映的苯教丧葬仪轨进行了介绍,后文将都兰血渭一号大墓与西藏腹地的吐蕃墓葬进行了比较研究。2008年,肖永明在《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一文中以都兰墓地里经树木年轮定年为685—784年的7座墓葬为研究对象,同时结合663年吐蕃灭吐谷浑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对比研究了7座墓藏与西藏地区吐蕃时期墓葬在形制、构筑方法及丧葬仪轨等方面的关系,并最终提出“都兰热水墓主人的主体应属于外来吐蕃人”的观点[21]。同年,仝涛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梳理了青海境内7—8世纪的墓葬(以都兰墓地为主)资料,研究发现该时段的墓葬习俗深受吐蕃文化影响,偶有因袭吐谷浑遗俗或受周边文化影响的现象,同时还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阐释[56]。2011年,许新国和格桑本联合发表《东嘎·洛桑赤列先生与都兰血渭六号墓出土的木牍》一文,文中公布了一枚书有“萨萨芒姆基”(吐蕃王妃)、“府邸”等藏文的木牍资料[65]。2012年,宗喀·漾正冈布等人发表《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u Ka)——都兰三号墓出土藏文碑刻考释》一文,文章对出土于热水南岸三号墓、刻有文字的石碑作了释译,并结合敦煌古藏文等文献资料,考证了墓主姓名、身份及偕微氏族与热水河古墓群的关系[66];宗喀·漾正冈布等人的另一篇文章——《七(bdun)、九(dgu)与十三(bcu gsum)——神秘的都兰吐蕃墓数字文化》,从都兰热水河沿岸墓葬中所频见七、九、十三等数字现象,重点探讨了上述数字在吐蕃文化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67];阿顿·华多太的《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一文也对都兰热水墓地、科孝图墓地所出的藏文木牍和石刻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43];恰嘎·旦正的《青海都兰三号吐蕃墓葬碑文考析》一文详细评析了都兰三号墓所出石碑的内容,并分析了赞普为谢乌大臣在都兰建墓立碑的原因,评析了碑文的特点[68—69]。2013年,德吉措在《都兰吐蕃三号墓鹿与鹰文化内涵的解读》一文中对都兰吐蕃三号墓所处地势及出土文物所折射出的鹿和鹰文化现象进行了解读,并认为这一现象与吐蕃苯教的丧葬仪轨有关[70]。是年,周伟洲重新审视研究了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热水血渭南岸4座墓和德令哈夏塔图2座彩绘木棺墓的墓主族属,并认为他们并非学者所说的“吐蕃或苏毗族”,而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族”[45]。2013年,曾科在《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大型墓地研究》中介绍了都兰吐蕃墓葬及墓地所出的部分文物[71]。2015年,格桑本发表的《吐蕃王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都兰吐蕃墓群的发掘和研究情况简介》两文中深化了都兰墓群是吐蕃墓葬的认识[72—73]。2016年,周毛先和宗喀·漾正冈布联合发表《都兰吐蕃古墓考古研究综述》,文中比较详细地梳理了学界对都兰吐蕃古墓之形制、族属和年代等的研究状况[74]。王瑄的《汉唐之际“青海道”墓葬概论——以都兰吐蕃墓葬为中心》一文还对出于都兰吐蕃墓的文物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析[75]。2017年,阿顿·华多太发表《〈下查那违约赔偿契书〉〈董布卜辞祈文〉——2014年都兰23号墓出土的古藏文甲骨释读》,文章释读了甲骨上的藏文,并认为所书内容可能与宗教仪轨有关[76]。
(四)流散海外的青海吐蕃文物研究。20世纪末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青海都兰及其附近一带盗墓活动猖獗,并致部分珍贵吐蕃文物流散海外,而这也客观上刺激和激发了国内外学界研究青海吐蕃文物的兴趣。1998—2006年间,艾米·海勒曾先后发表《两件带有题记的织物及其历史背景——公元7至9世纪吐蕃审美和丝绸贸易的观察》《一件公元8世纪粟特和汉式儿童服饰》《中亚吐蕃王朝时期的考古出土物》和《新发现的吐蕃纺织品》4篇文章,1998年的两文分别对青海吐蕃墓所出丝织品的绘制图案和制作工艺进行了介绍研究[77];2003年的文章又从纹饰、纹样、工艺特点等角度对比研究了流散海外的金银器和吐蕃墓葬考古中所出金银器[78];2006年的文章则重点研究了流散瑞士的两件纺织品之工艺和主题纹样[79]。2007年,霍巍在《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一文中对流散美国现藏于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部分金银器、金属饰件和纺织品等吐蕃文物作了详细介绍和初步研究[80]。2009年,霍巍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结合都兰热水墓地所出的马鞍残构件和彩绘木板画中绘制的马匹鞍具对芝加哥博物馆收藏的一套吐蕃时期的马具进行了复原研究[81];同年,他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文又对都兰吐蕃墓出土的金牌饰、银质管状器、银带饰、包金银球(珠)饰、鎏金银带饰等进行了造型、纹饰和制作工艺的研究,并认为吐蕃系统的金银器既受到了唐、粟特、波斯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82]。2013年,艾米·海勒在《吐蕃金银器皿和人工制品上的铭文》中对流散海外的多件金银器上的铭文和部分数字符号进行了解读研究[83];同年,她又在《吐蕃帝国彩绘棺板画的观察》和《吐蕃墓出土彩绘棺板画的初步研究》两文中对一幅流散海外且保存完整的吐蕃彩绘棺板进行了研究,同时参阅国内公布的同时期棺板画图像,探讨了吐蕃棺板画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场景及其所反映的艺术风格,并认为画面内容受到了中亚粟特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的多重影响[84]。是年,林梅村在《丝绸之路上的吐蕃番锦》一文中,对都兰吐蕃墓中考古所出的丝织品和流散海外的丝织品之产地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都兰墓地所出的“粟特织锦”多是中亚伊斯兰化以后的产品,其真实产地应在吐蕃本土而非中亚[85]。
三、青海吐蕃墓考古工作取得的成就及未来工作展望
青海吐蕃墓的考古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首开以来,已持续进行30余年。其间,文物工作者陆续公布了部分考古资料,学界藉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规范地发掘了青海境内百余处吐蕃墓葬,为学界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素材,并运用考古手段获取了青海吐蕃墓的形制布局、构筑方式等诸多信息,为未来该区域吐蕃墓葬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田野调查工作的大量开展还初步厘清了境内吐蕃墓葬的数量、掌握了这些墓葬的具体分布情况。第二,经对发掘的部分重要墓葬进行科学测年,已就墓葬年代、文化属性和墓主族属等若干问题达成共识,同时考古发现还证实了青海吐蕃墓所体现的丧葬文化具有多源流性。第三,青海吐蕃墓考古所获文物,如胡锦、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还为吐蕃统治时期的青海道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都兰县境内大量吐蕃墓葬的发现还进一步证实了当地曾是吐蕃东向扩张的一处重要军事基地[86]。第四,国内学者开启的青海吐蕃墓研究成果丰硕、极具影响,且备受国际藏学界所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出版论著近百篇(部)[45],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学者的成果,他们掌握着这一研究领域的绝对主导权。
虽然青海吐蕃墓考古工作取得上述诸多成就,但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加强的地方。
(一)部分重要墓葬的墓主族属、身份仍未确定。以都兰热水一号大墓为例,因正式的考古报告尚未发表,致使学界对部分关键性问题的了解还很不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对墓主身份和族属的正确判识。另,青海地区吐蕃墓葬的考古报告滞后发表还影响学界对吐蕃治下青海地区丧葬习俗的研究。
(二)前吐蕃时期(即吐谷浑统治时期)青海吐谷浑墓的考古工作亟待加强。目前学界对青海吐蕃墓葬考古中发现的墓主人族属和墓葬文化性质的认识常存争议,究其原因是考古工作者未发现可确定是吐谷浑统治时期的吐谷浑墓葬,致使学界对吐谷浑人的丧葬习俗不甚清楚,故在青海吐蕃墓葬的考古工作中很难区分部分墓葬的墓主族属。这继而引发了学界持续多年的青海吐蕃墓部分墓主族属的争论,更甚者有如部分青海史研究者还据“青海是吐谷浑故地”的历史来否定历史上吐蕃文化曾对当地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客观史实。借助考古手段,还原历史真相,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十分重要。
(三)要加大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力度。青海吐蕃墓中所出遗物,尤以金银器和丝织品为大宗,且两类文物种类繁多、极具特色,然与之不相称的是从事两类文物研究的学者极少。以青海吐蕃墓出土丝织品的研究为例,国内仅许新国、赵丰两位先生进行过专门研究,然二位一已退休,一身兼数职,难于集中精力从事研究;致力于吐蕃金银器研究的学者则更少,国内只霍巍教授一人。显然,国内有志于吐蕃金银器和丝织品研究的学者已近青黄不接的局面。与此同时,近年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又对外首次展示了藏于该馆的百余件珍贵藏品(含一部分吐蕃金银器和丝织品),公安部门也破获追缴了青海都兰古墓盗掘的文物646件(多为金银器)。这些新材料的面世,无疑又对专业研究人员匮乏、紧缺的局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应注重对吐蕃丧葬仪轨文献的解读整理工作,以便更好地研究青海吐蕃墓葬。现存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是目前唯一一部比较完整的记录吐蕃苯教丧葬仪轨的文献,对认识和了解吐蕃丧葬习俗具有重要价值。国内外学者如拉露[87]、哈尔[88]、褚俊杰[89—91]、迈考·沃特[92]等曾先后对其进行过释读研究。上述诸研究中,对国内学界影响较大的是褚俊杰先生的解读成果,然其释读内容仍有可商榷之处,如“尸魂相合”仪式、施行还阳术、守灵人扶正武器、侍者向活人告别仪式、剖刺放血、嫡幼子驾临仪式、“墓穴厌胜”法术、舅臣在多麦主持吊丧仪式等均无法在原文中找到对应词句,或是译者的意译[93]。此外,随着敦煌古藏文文书资料的全面公布和吐蕃史研究工作的日渐深入,也很有必要对P.T.1042号藏文写本文书进行再次释译。
(五)继续深化青海地方史的研究,尤其是吐谷浑史的研究。在青海地区的历史上,吐谷浑居主导地位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而有关该族群的史料文献主要是用汉、藏两种文字所书写,书撰者在记录具体史实时会出现因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和记述视角的不同而用不同术语表述的现象。以藏文中“阿夏”和汉文中的“吐谷浑”为例,周伟洲先生认为二者实为同一族群[94],藏族学者夏吾李加则持不同观点[95]。究其原因,则是两位所据的史料不同,这对利用汉、藏文资料进行吐谷浑史研究的学者或具有启发性。另,吐谷浑的疆域及唐、蕃对其影响的时间问题等也都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参考文献]
[1]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71—172.
[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祭祀遗址[N].青海日报,1985-10-16.
[3]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71.
[4]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5]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C]//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大坂经济法科大学.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6]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39—240.
[7]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303.
[8]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83—284.
[9]许新国.缂丝织物的历史和制造技术初探——从都兰出土的缂丝谈起[J].青海文物,1990(4).
[10]许新国.吐蕃丧葬殉牲习俗研究[J].青海文物,1991(6).
[11]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
[12]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J].中国藏学,1994(4).
[13]许新国.都兰热水血渭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1).
[14]许新国.吐蕃墓的墓上祭祀建筑问题[J].青海文物,1995(9).
[15]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J].中国藏学,1996(1).
[16]许新国.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J].中国藏学,1997(3).
[17]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J].西藏研究,1991(3).
[18]Amy Heller.“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Excavations at Dulan.” In Orientations 29(9),1998:84—92.
[19]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103—104.
[20]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89—213.
[21]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J].青海民族研究,2008(3).
[2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2(12).
[23]许新国.青海吐蕃墓葬发现木板彩绘[J].中国西藏,2002(6).
[24]许新国.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的壁画墓[J].青海藏族,2012(1).
[25]乔红.青海玉树三江源地区史前文化与吐蕃文化考古的新篇章(二)[N].青海日报,2015-04-24.
[2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热水哇沿水库发掘古代遗址和墓葬[N].中国文物报,2015-07-03(008).
[2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都兰县哇沿水库古代墓葬2014年发掘简报[J].青海文物,2017(12).
[28]王树芝.青海都兰地区公元前515年以来树木年轮表的建立及应用[J].考古与文物,2004(6).
[29]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都兰吐蕃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30]李天林.青海海西古丝绸文物图集——丝绸之路[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8.
[31]许新国.寻找遗失的“王国”——都兰古墓的发现与发掘[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1(2).
[32]许新国.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J].考古,2002 (12).
[33]程起骏.打开吐谷浑古国之门的钥匙——关于都兰热水古墓群札记之一[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1(2).
[34]程起骏.磨洗沙砾认前朝——关于都兰古墓群札记之二[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1(6).
[35]程起骏.踏访深埋在地下的吐谷浑王国——都兰古墓群文化归属解惑[J].中国土族,2003(3).
[36]程起俊,毛文炳.倾听千座古墓的诉说——就都兰古墓群的文化归属与许新国先生再商榷[J].中国土族,2006(3).
[37]三木才,刘树军.都兰古墓1号殡葬民俗文化考察[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1(6).
[38]三才木.关于“苯神血祭”仪轨与都兰吐蕃古墓——吐蕃殡葬文化研究系列之一[J].柴达木开发研究,2011(3).
[39]霍巍.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3).
[40]Wang Tao,“Tibetan or Tuyuhun:the Dulan site Revisited”.in From Nisa to Niya:New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in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Edited by Madhuvanti Ghose and Rusell-Smith,Saffron,2003.
[41]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60年:1949—2009[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566—567.
[42]许新国.关于都兰县热水乡血渭一号大墓的族属与年代[J].青海藏族,2012(1).
[43]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J].中国藏学,2012(4).
[44]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J].考古学报,2012(4).
[45]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J].史学集刊.2013(6).
[46]李朝,柳春诚.都兰热水一号大墓考古研究的重大收获——兼与仝涛先生商榷[J].中国土族,2013(1).
[47]柳春诚,程起骏.吐谷浑人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出土棺板画研读[J].中国土族,2004(2).
[48]柳春诚,程起骏.郭里木棺板画初展吐谷浑生活[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5(2).
[49]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J].中国藏学,2005(1).
[50]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J].文物,2006(7).
[51]林梅村.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C]//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8—275.
[52]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J].西藏研究,2007(2).
[53]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J].敦煌学辑刊,2007(1).
[54]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J].藏学学刊,2007.
[55]许新国.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6]TongTao,Unpublished thesis : The Silk Roads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from the Han to Tang dynasty) as reconstructedfrom Archaeological and Writen sources (Tübingen 2008),http://tobias-lib.uni-tuebingen.de/volltexte/2008/3628/.
[57]王树芝.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J].考古,2008(2).
[58]Tong Tao and Patrick Wertmann,“The coffin paintings of the Tubo Period from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In Wagner,Mayke and Wang Wei,eds.,Bridging Eurasia,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Beijing Branch office.Mainz: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2010:187—211.
[59]吴晓燕.青海海西州棺板彩绘的初步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0]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J].考古,2012(11).
[61]许新国.德令哈吐蕃墓出土丝绸与棺板画研究[J].青海藏族,2015(2).
[62]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J].考古,2003(12).
[63]林梅村.青海都兰出土伊斯兰织锦及其相关问题[J].中国历史文物,2003(6).
[64]林梅村.试论唐蕃古道[J].藏学学刊,2007.
[65]许新国,格桑本.东嘎·洛桑赤列先生与都兰血渭6号墓出土的木牍[J].青海藏族,2011(2).
[66]宗喀·漾正冈布,等.论赤偕微噶(Blon Khri She’u Ka)——都兰吐蕃三号墓出土藏文碑刻考释[J].文物,2012(9).
[67]宗喀·漾正冈布,等.七(bdun)、九(dgu)与十三(bcu gsum)——神秘的都兰吐蕃墓数字文化[J].敦煌学辑刊,2012(1).
[6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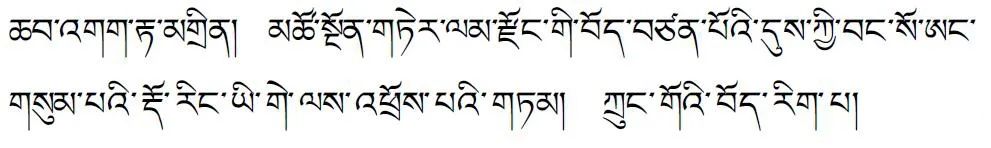 2012(4).
2012(4).
[69]恰嘎·旦正.都兰吐蕃三号墓石刻考析[J].西藏研究,2016(1).
[70]德吉措.都兰吐蕃三号墓鹿与鹰文化内涵的解读[J].西藏研究,2013(2).
[71]曾科.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大型墓地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2]格桑本.吐蕃王朝时期的墓葬形制[J].青海藏族,2015(2).
[73]格桑本.都兰吐蕃墓群的发掘和研究情况简介[J].青海藏族,2015(2).
[74]周毛先,宗喀·漾正冈布.都兰吐蕃古墓考古研究综述[J].西藏研究,2016(4).
[75]王瑄.汉唐之际“青海道”墓葬概论——以都兰吐蕃墓葬为中心[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76]阿顿·华多太.《下查那违约赔偿契书》《董布卜辞祈文》——2014年都兰23号墓出土的古藏文甲骨释读[J],青海文物,2017(13).
[77]Amy Heller,“Two Inscribed Fabrics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Some Observations on Esthetics and Silk Trade in Tibet,7th to 9th Century.” In Entlang der Seidenstrabe:Frü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wischen Persien und China in der Abegg-Stiftung.Riggisberger Berichte 6.Karel Otavsky,ed.Riggisberg:Abegg-Stiftung,1998:95—118;“An Eighth Century Child’s Garment of Sogdian and Chinese Silks.” In Chinese and Central Asian Textiles: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1997.Hong Kong:Orientations Magazine,1998:220—222.
[78]Amy Heller,“Archaeological Artefact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In Orientations 34(4),2003.
[79]Amy Heller,“Recent Findings on Textil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n Textiles and Their Context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Riggisberger Berichte 9.Regula Schorta,ed.Riggisberg:Abegg-Stiftung,2006:175—188.
[80]霍巍.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5).
[81]霍巍.吐蕃马具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J].考古,2009(11).
[82]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
[83]Amy Heller,“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Volume 1 Inaugural Issue, 2013:259—292.
[84]Amy Heller,“Observation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of the Tibetan Empire”,Christoph Cuppers,Robert mayer,Michael Walter eds.,Tibet after Empire Culture,Society and Religion between 850-1000,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Held in Lumbini,Nepal,March 2011,Kathmandu:Dongol Printers,2013:117—168;“Preliminary remark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from Tibetan tombs”.In Dotson,Brandon,Iwao,Kazushi and Takeuchi,Tsuguhito eds.,Scribes,Texts,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Proceedings of the 12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iesbaden:Reichert Verlag.2013.
[85]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吐蕃番锦[N].东方早报,2013-11-11(007).
[8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32—134.
[87]Marcelle Lalou.“Rituel Bon-po des funérailles royales fonds Pelliot-tibétain n° 1042>”,JA,1953:339—361.
[88]Erick Haarh,The Yar-lung Dynasty.Copenhague,G.E.C Gad’s Forlag,1969:364—379.
[89]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J].中国藏学,1989(3).
[90]褚俊杰.苯教丧葬仪轨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的解读[J].中国藏学,1989(4).
[91]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T.239解读[J].西藏研究,1990(1).
[92]Michael L.Walter,Buddhism and Empire,Brill,2009:191—197.
[93]夏吾卡先.藏王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94]周伟洲.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va-zha)与吐谷浑[J].中国藏学,2016(1).
[95]夏吾李加.藏文化语境下的阿夏与吐谷浑之族源考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疆境内丝路南道上吐蕃遗存的调查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YJC780003);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喜马拉雅地区8—11世纪藏文题刻的整理与翻译研究”(项目编号:17YJA870022);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元1—10世纪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地带的文明联系研究”(项目编号:18CKG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承炎(1989—),河南商城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西域考古与吐蕃史研究;夏吾卡先(1981—),藏族,青海同仁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西藏考古与艺术史研究。
原载《西藏研究》 2019年第1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