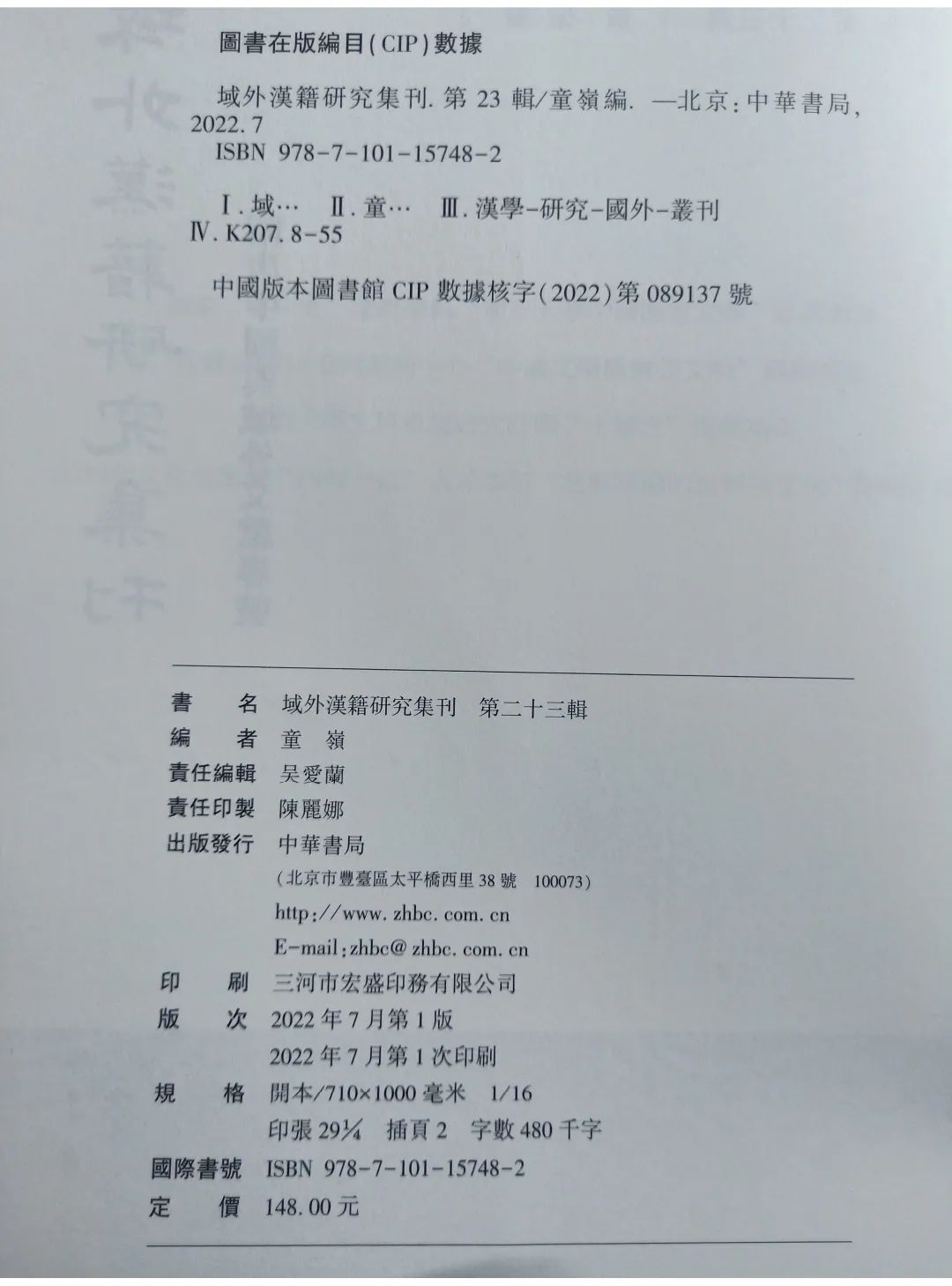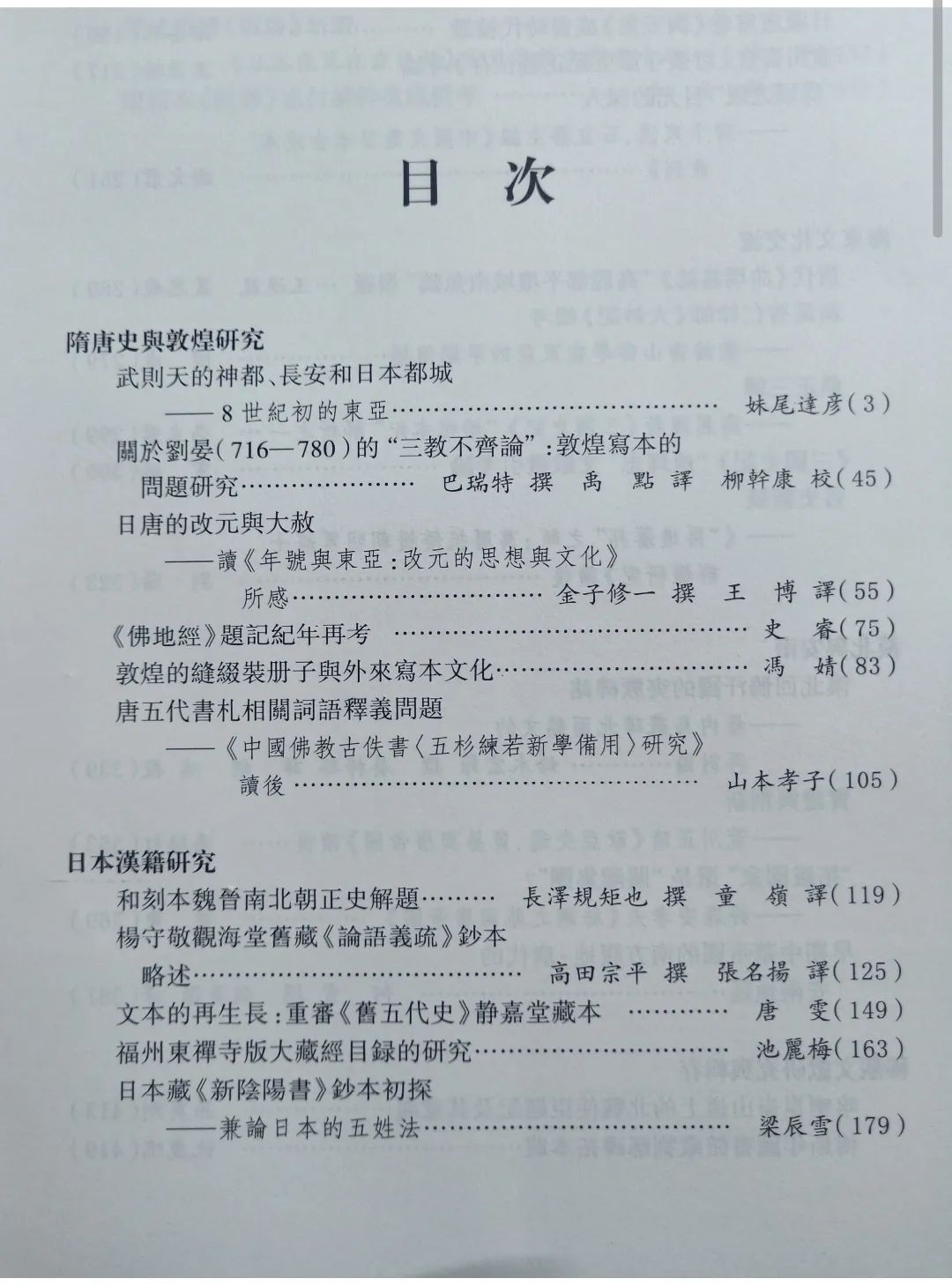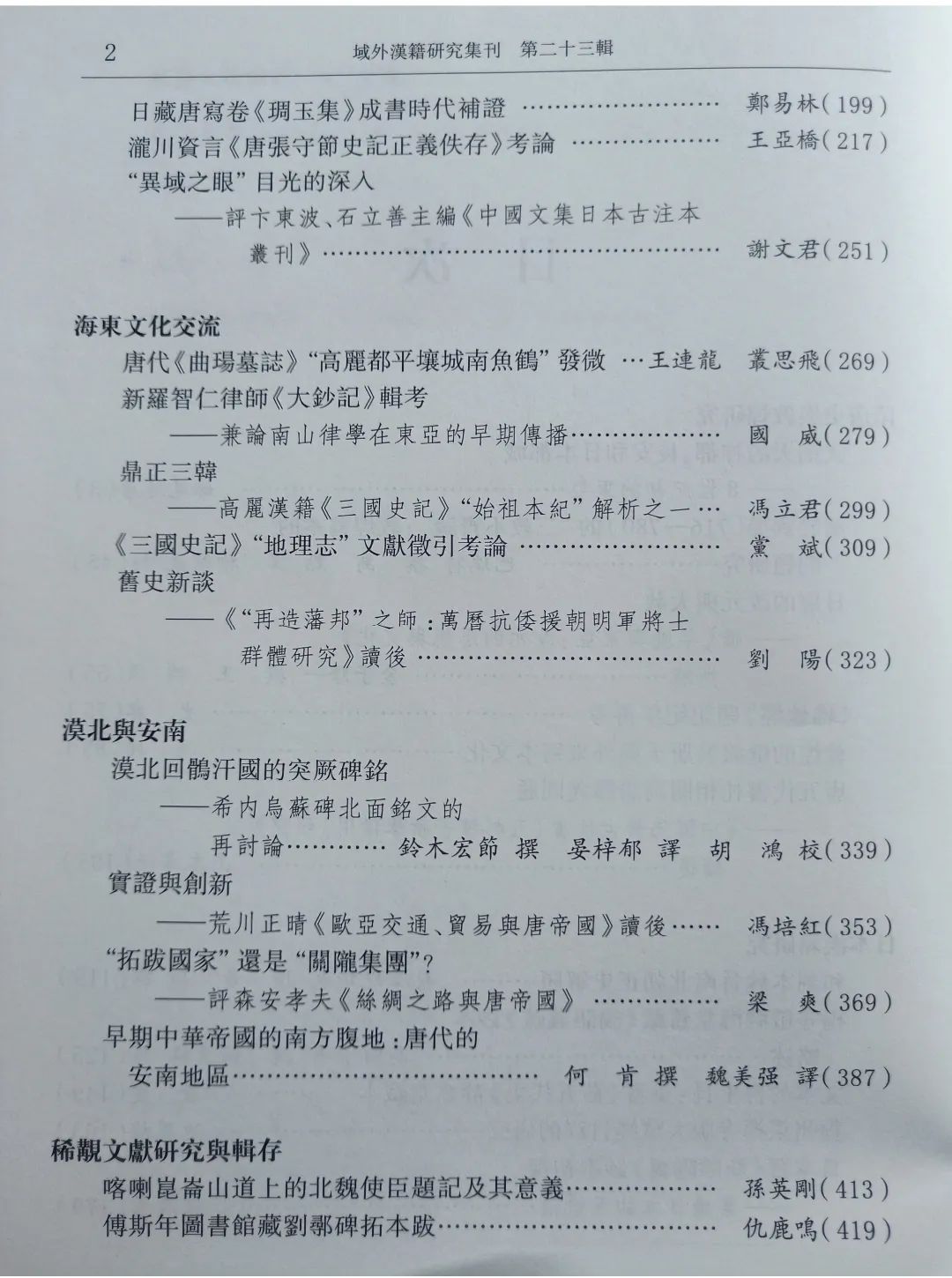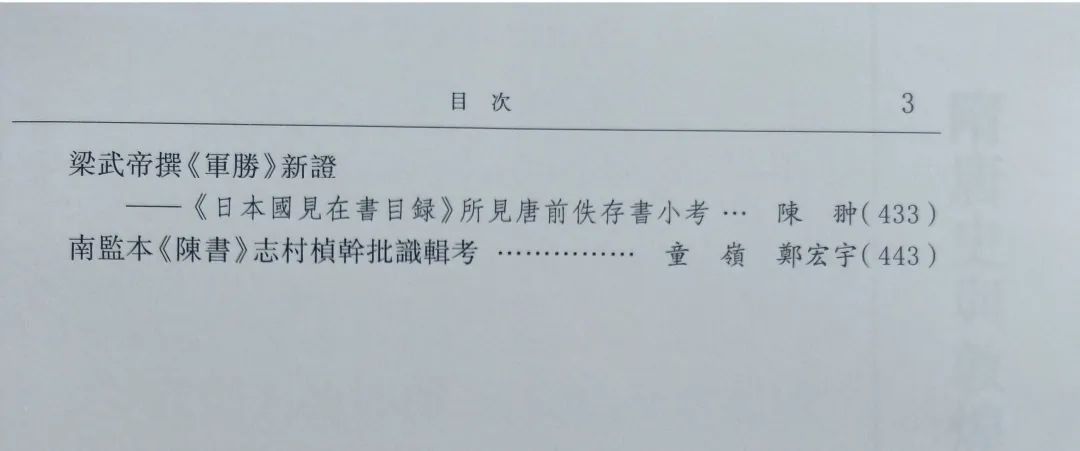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发表论文122篇。2010年,日本大阪大學荒川正晴教授出版了《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一書,這是他於2008年向該校提交的博士學位論文的修訂本[1]。需要說明的是,荒川氏於1981~1986年攻讀博士課程的學校並非阪大,而是早稻田大學。其本科、碩士、博士均就讀於早大,分別於1979、1981年獲學士、碩士學位。1986年博士畢業後,過了22年纔向阪大申請博士學位,獲得通過。荒川氏生於1955年,獲博士學位時已53歲。老一代的日本學者大多是這樣的求學經歷,幾乎是用一輩子的所學去申請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含金量是很高的。2008年荒川氏獲得博士學位後,對論文內容略作修訂,並且調整了篇章結構(頁553),兩年後正式出版成書。從書後所附的《論文初刊一覽》可知,此書是作者在1982~2008年間所撰部分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增補,部分章節係新寫而成的。若從1981年開始攻讀博士課程算起,至2008年獲得博士學位,長達27年;若至2010年出版成書,則達29年之久。可以說,這本厚達630餘頁的著作,凝聚了荒川氏一生的心血,無疑是他在學術領域中的代表作。荒川氏長期任教於大阪大學,同時還是日本“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的成員,該研究會成立於1987年,成員由荒川正晴、片山章雄、白須淨真、關尾史郎、町田隆吉五人組成[2]。另外,熊本裕、森安孝夫、高田時雄、武內紹人、吉田豊五人組成了“敦煌青年委員會(YTS)”。這兩個學術團體成為近半個世紀日本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核心隊伍。作為日本學界該領域的代表性人物,荒川氏的治學特點是:利用吐魯番、敦煌、于闐等地出土的文書等資料,研究6~8世紀中國西北地方的歷史,尤其是以麴氏高昌、西突厥、唐及粟特為重點,注重實證,見微知著,多有創新。《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一書以交通與貿易為研究內容,關注粟特人這一中介羣體,將其置於從西突厥到唐朝的時代轉換過程中觀察,通過歐亞世界的宏觀視野與細緻入微的分析考證,揭示出了6~8世紀歐亞東部地區的歷史實相與圖景。此書分為序言、3部10章、結語等部分。每部均以小序、各章、小結的形式呈現,形式規整,井然有序。序言的標題為《本書的視角與課題》,交待了此書的研究對象與內容,特別強調從中亞自身的視角入手研究,但又不僅限於中亞地域,而是探討中亞內部之間及中亞內外的政治統屬關係,將視野擴展到整個歐亞地區;就課題內容而言,此書探討從西突厥汗國到唐朝統治時代的交通與貿易,抓住粟特人這一流動性羣體的特點,將研究內容有機地串連起來,可謂別致新穎,頗有靈韻。第 I 部《突厥系遊牧國家與綠洲國家》,由小序、第1章《突厥系遊牧國家的建立與交通系統》、第2章《綠洲國家、遊牧國家與粟特人》、第3章《綠洲國家的接待事業與財政基礎》、小結構成,主要探討西突厥汗國控制下的中亞交通系統及其伴生的稅役供應,並以麴氏高昌國為例,考察高昌國的粟特人及其與王權的關係、接待以粟特人為主的西突厥遊牧使節及其接待事業的經濟基礎。關於西突厥的交通體制,作者的切入點是ulaγ,目光獨到,並由此引出西突厥控制下的交通系統,具體體現在吐魯番文書所反映的麴氏高昌國的遠行制。在討論遊牧國家與綠洲國家的關係時,作者從流動於兩者之間的使節切入,敏銳地發現使節中充斥著粟特商人的現象;並通過西突厥遊牧汗國派遣使節、麴氏高昌國接待遊牧使節及其財政供應所需的稅役,提出兩者之間建立共生關係的概念。這對於認識歐亞內陸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第 II 部《唐帝國與歐亞東部的交通體制》,由小序、第4章《唐代公用交通系統的構造》、第5章《唐代河西、西域的交通制度(1)》、第6章《唐代河西、西域的交通制度(2)》、小結構成。這是繼第I部探討西突厥時代之後,進入唐朝統治中亞時期的交通制度。作者首先交待了唐朝的驛傳制及其研究史,然後再來談河西、西域的交通制度。然而,根據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記載,驛傳制並非如想像中的那樣被推行到唐朝的所有控制區;實證的結果顯示,西突厥時代的遠行制持續影響到了唐代,而且在地域上還進一步擴延至河西走廊,亦即唐朝在河西、西域實行的長行坊制。這樣的觀點無疑具有新意,甚至衝擊了以往對唐代驛傳制的認識。最後,作者討論了承擔這一交通制度的經濟基礎,發現ulaγ稅役負擔照樣存在,這也為作者提出的長行制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第 III 部《唐帝國與胡漢商人的流動和貿易》,由小序、第7章《唐帝國與胡漢商人》、第8章《唐朝的通行證制度與公、私交通》、第9章《唐朝向河西、西域咚蛙娦栉镔Y與商人》、第10章《唐朝的統治與貿易、經濟環境的變動》、小結構成。如此書標題所示,其主要內容是研究唐帝國的交通與貿易,第 II 部考察的是交通制度,第III部考察的是貿易活動。作者在第 I 部關注到麴氏高昌國中的粟特官員、西突厥遊牧使節中的粟特商人,在第 III 部更是集中討論了唐代的胡漢商人,尤其是粟特胡商的貿易活動。作者提出了一個新見,即強調了粟特商人在唐朝向河西、西域咚蛙娦栉镔Y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書的最後是結語,在總結全書的基礎上,對序言中提出的“唐帝國為什麽因統治中亞而承受如此沉重的財政負擔?”、“唐帝國的統治給中亞帶來了什麽變化?”這兩個問題作了迴答,使全書前後呼應。作者再次強調中亞的交通與貿易不祇是遊牧國家和綠洲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必須與中亞外部的動向一併予以把握,指出從廣域視角開展研究的重要性。第一,立足西域與河西的自身立場,放眼歐亞世界的廣域視角。雖然此書依據的史料基本上是碎片性的出土文書,但書名中的“歐亞”一詞展現了作者宏闊的學術視野與系統的理論思考。尤其是序言的標題中旗幟鮮明地道明《本書的視角與課題》,並在開篇首句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將6~8世紀中亞地區活躍的交通與貿易置於歐亞東部地區的廣域空間中來重新把握,以揭明它的實際狀況與興盛原因”,以及第一段的末句直言強調“本書從中亞自身的視角入手進行探討”(頁1)。作者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基於絲路沿線各地出土的文書,通過考析文書的內容,並將這些出土地點串連起來,來探討6~8世紀絲綢之路的交通與貿易實相。作者所說的“中亞”,原意是指以帕米爾高原和天山山脈為中心的亞洲腹地,但由於文書的出土地點主要在帕米爾以東地區,所以書中討論的實際上祇是今中國新疆地區,以及向東延伸至河西走廊。作者批判了日本學界主要依靠漢文史籍以及從中原政權經營西域的視角,強調應該從中亞(西域)自身出發,哂梦饔蚣岸鼗统鐾恋奈臅鴣黹_展相關研究。作者的這一批判雖說是針對日本學界,但實際上中國學者大多也同樣如此。從書中的論述來看,作者利用西域及敦煌當地出土的文書,貼近綠洲民眾的生活,完全是從當地人的視角出發研究的。這一研究立場無疑更為客觀,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更加可信。從歐亞世界或絲綢之路整體來看,西域地區的綠洲各國並不具備獨立性,經常依附於周邊的強大政權,這是西域綠洲各國的自身特點,因此研究這一地區必須放到整個歐亞世界中去觀察。早在2003年,作者出版《綠洲國家與隊商貿易》一書[3],書中第五部分的小標題為《歐亞的變動與粟特商人》,就已經關注整個歐亞世界,尤其該書重點探討的粟特人是個極為活躍的商業民族,隨著他們的足跡所履而擴大了地域範圍。作者是著名的粟特研究專家[4],對粟特人及其商業活動以及對唐代交通體制的研究[5],直接催生了《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一書,其學術視野自然也隨著粟特人在絲綢之路上的活動而擴至整個歐亞世界。祇不過研究依憑的文書主要出土於帕米爾以東各地,而6~8世紀歐亞大陸的形勢發生巨大變動,嚈噠、柔然走向衰落,突厥、隋唐相繼崛起,中亞地區的粟特人成批地向東遷徙,所以作者此書的研究視野也就定在了歐亞東部。如上所言,西域各國不具有獨立性,先依附於西突厥,後來被唐朝征服。也正因此,作者在提倡中亞自身立場的同時,又非常注重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強調此書“考察特定地域的交通與貿易,不憚其煩地討論超越該地區的廣域範圍的政治、社會、經濟關係的性質,尤其是將中亞、乃至包含中亞的中央歐亞置於近代以前‘世界’的中心地位”(頁5);“本書從中亞內部之間及中亞內外的政治統屬關係,以及在此基礎上構築的共生關係與地域秩序入手進行探討”(頁13);“本書抓住6~8世紀中亞的交通與貿易,不僅在其內部世界,而且將之放在歐亞東部地區來探討,是不可或缺的”(頁16),並且提出了“共生關係”的概念。在正文中也同樣如此,第I部考察遊牧國家與綠洲國家,是把麴氏高昌國放在西突厥的政治統治下論述的,兩者之間結成共生關係;第 II、III 部考察唐朝的交通體制與商人貿易,也是把西州、沙州、于闐等地放在唐朝統治中亞的框架內討論的。第二,此書是實證研究的典範之作,在史料哂蒙献钜?俗⒛康氖鞘褂昧舜罅砍鐾廖臅?瑏K對之進行精細的分析考證,然後將其考證結果用於本書的論證中。這些文書出土於吐魯番、敦煌、庫車、和田、穆格山等地,尤其是以前兩地所出之文書為主;此外,還使用了《唐六典》、《唐律疏議》等唐代史籍,以及個別日本和阿拉伯史料。哂贸鐾廖臅?怯纱藭?奶囟ㄑ芯康赜驔Q定的,或者反過來說,正因為以上這些地點出土了文書資料,纔能有效地開展由各出土地點串連起的絲綢之路的交通與貿易研究。書後的《索引》分列事項、人名、文書三類,其中文書類列舉了239件(有1件係由多個編號拼合,有的還被多次引用),它們主要出自吐魯番,特別是出自阿斯塔那墓羣的文書至少達170件[6],這構成了該書史料哂玫淖畲筇厣?F浯危?藭?褂玫亩鼗臀臅?m然件數不多,僅有22件(分藏於法、英、俄、日四國),但價值極高,對於研究河西、西域的交通制度與貿易問題至為重要。最後,書中還使用了庫車、和田、穆格山出土的文書,尤其是第6章第2節《安西四鎮地區與ulaγ》中,哂昧撕吞锫樵??癯鐾恋摹多w落馬帳》等文書,探討了安西、于闐等地的交通及關聯的稅役問題,這對於說明吐魯番以外的西域地區的交通制度起到了填補空白的作用,也使此書在對整個歐亞世界的交通與貿易研究上更具有代表性。這些出土文書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豐富堅實的史料,其所開展的研究主要基於對出土文書的分析,實證性強,特別是對一些重點探討的文書,在釋錄上力求精准。這些重點文書大多篇幅較長,內容豐富,價值極高,在每章中都有哂谩F澝空赂髋e一件於下:第1章第3節之《給價文書》、第2章第3節之《供糧食帳》、第3章第2節之《車牛役簿》、第4章第3節之《傳馬坊牒》、第5章第3節之《長行坊狀》、第6章第1節之《西州館牒》、第7章第3節之《唐垂拱元年(685)康義羅施等請過所案》、第8章第3節之《唐開元廿一年(733)唐益謙、薛光泚、康大之請給過所案卷》、第9章第3節之《唐開元廿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為勘給過所事》、第10章第2節之《唐開元十六年(728)末庭州輪臺縣錢帛計會稿》。從該書頁34注45)、頁60注41)、頁114注25)、頁184注59)、頁243注37)、頁273注1)、頁349注38)、頁392注15)、頁480注79)、頁523注16)可見,以上10件文書中,有8件作者曾親往收藏機構調查過文書原件,有1件是拜託在巴黎留學的森安孝夫幫助調查的,還有1件祇是參照了陳國燦的著作。類似的重點文書在書中還有不少,約略統計可知,作者於1992、1998、2000、2003、2007年先後5次出國,或赴新疆,或至歐洲,總共實地調查過27件文書。有些文書還調查過兩遍,如《給價文書》、《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車牛役簿》、《唐開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給西州百姓遊擊將軍石染典過所》。因此,作者對文書的釋錄相當精凖,也進一步修正了原先錄文之誤,既包括《吐魯番出土文書》及柳洪亮、朱雷、童丕(éric Tromber)等人所錄之誤,也包括作者自己的初錄之誤。這些出土文書是作者分析討論的基礎性史料,可以說藉之構築起了此書的基本骨架。當然,作者也不是僅限於對單篇重點文書的考證分析,書中還綜合利用大量文書開展相關問題的研究,充分顯示出他對出土文書的熟悉程度,已經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例如,第2章第2節考察麴氏高昌國的粟特官員,列有表2-1《麴氏高昌國粟特諸姓人物任官表》(頁51),展列了23位史、康、何、安等姓粟特官員,從表中的出處一欄可以看到是從眾多的吐魯番文書與墓誌中輯錄出來的;第3節考察西突厥、中原王朝、西域諸國或勢力集團派至麴氏高昌國的遊牧使節,列舉了14件吐魯番文書及表2-2《麴氏高昌國使節、客人一覽表》(頁72-74),表中所列使節派遣者及其所遣的使者、客人多達59欄,也都是從大量的吐魯番文書中蒐輯出來的。此外,第3章使用的稅役文書,第4、5、6章的馬牛驢文書,第7、8、9、10章的粟特商人貿易與交通文書,以及表10-2《吐魯番出土西州時期買賣與借貸契中的絹、錢表》,從中可以看到作者使用了吐魯番及其它各地出土的大量文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這些敦煌、西域出土的文書,根本無法還原麴氏高昌國與西突厥、唐朝在西域與河西地區的交通制度和貿易活動,更無法串連起貫通歐亞的絲綢之路貿易路線。而作者長期浸淫於出土文書的整理研究及對內陸亞洲歷史的探索,以其對出土文書的熟稔掌握,信手拈來地哂玫綄?z綢之路的交通與貿易研究中,從而在實證中作出創新。第三,作者根據出土文書所作的微觀考證,極為細緻綿密,分析層層深入,探賾索隱,從而得出一些以前不為人知的新觀點。舉例來說,第1、6章對ulaγ的考證,是從《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的“鄔落馬”入手的,作者不僅從日本奈良興福寺所藏抄本中發現“驛馬也”、“傳馬也”等附注文字,而且還揀出吐魯番出土的三件《西州館牒》中的“烏駱子”之記載,對之作了十分精彩的考證剖析,認為鄔落(烏駱)是古突厥語ulaγ的音譯漢字,但其使用範圍又不僅僅局限於突厥語,在蒙古語、滿語及包括西藏和印度在內的歐亞大陸廣闊地區也都在用,甚至唐代西州漢人官吏在公文書中也在使用該詞。然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西突厥交通體制中的ulaγ及其伴生的稅役負擔。麴氏高昌國時期的出土文書記錄了跨越綠洲諸國的遠行馬、遠行車牛,作者將這種使用遠行馬或車牛的交通制度稱為“遠行制”;第5、6章研究指出,西突厥及其控制下的麴氏高昌國滅亡以後,唐朝在西域地區並未推行驛傳制框架下的傳馬坊制度,而是繼承了遠行制的衣悖?o不過將遠行馬更名為長行馬,在節度使體制下設置了“長行坊制”,而且公文中仍然使用“烏駱(ulaγ)子”一詞,無論是綠洲民眾抑或遊牧民眾都要承擔相關的稅役。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過實證分析,進一步提出唐朝還將長行坊制推廣哂玫胶游髯呃取?Q言之,唐朝雖然控有河西、西域,但在交通制度上卻未施行驛傳制,而是接受了高昌國、西突厥的制度遺產。這一新觀點的提出可謂獨具慧眼,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以往的認知,也加深了對唐朝制度實施與統治差異性的理解。第1章中引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記高昌王麴文泰相送玄奘的史料,作者所作的點逗考辨同樣體現出精到細緻之功。他對“並書稱”後面的書信內容,提出了與高田修截然不同的斷句法,認為不是到“願可汗憐師如憐奴”為止,而把“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也包含進來。當時能給綠洲諸國發敕的人非西突厥可汗莫屬,顯然作者的觀點是正確的。對這段史料的細緻閱讀,更典型地體現在第2章對“殿中侍御史歡信”的點逗上。以往的學者毫無例外地皆釋讀為“殿中侍御史/歡信”,認為前者是官名,後者是人名。然而,作者卻獨闢蹊徑,指出高昌國並未設置殿中侍御史,而認為殿中侍御是官名,史歡信為姓名,且與同時代吐魯番文書中的史歡隆、史歡太為兄弟輩人物,故釋讀作“殿中侍御/史歡信”。這一細緻的考證辨析,充分體現出日本學者在研讀史料中的細膩特點。不僅如此,作者還進一步從吐魯番文書與墓誌中蒐揀出麴氏高昌國的粟特官員,所列23人中,史姓14人、康姓6人、安姓2人、何姓1人,史姓人物佔了61%。這個結論以前沒人作過統計,所以也未曾注意及此。如今經過作者的統計列表,讓人很直觀地看到了史姓在麴氏高昌國獨樹一幟的地位。第2章重點考察遊牧使節,作者指出遊牧國家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具有多樣性,並將之分為遊牧國家與遊牧集團;綠洲諸國也存在不同的形態,分為聚落型與國家型;另外,他特別注重遊牧國家與綠洲國家之間形成的共生關係。通過對大量吐魯番文書的分析,作者發現遊牧使節的派遣者來自不同的勢力,並非都由可汗(qaγan)所派遣,珂頓(qatun)、提勤(tegin)、移浮孤(yabγu)、抴(šad)、大官(tarqan)、希瑾(irkin)等也都派出使節,這對於認識突厥汗國的性質具有重要的價值,也豐富了對西突厥各部落及階層的認識。作者還特別留意到,這些遊牧使節中有不少是粟特人,並從粟特語角度對使節人名進行考證,揭示出充當使節兼商人的粟特人與西突厥遊牧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同時指出粟特人除了作為使節出使麴氏高昌國外,還在積極地開展個體私人貿易。這樣的實證考析對於深入認識粟特人的特性至為重要。類似這樣的細緻分析,在書中不勝枚舉,如第6章注意到吐魯番文書中記載的“漢道”,以及行走在漢道上的長行馬與失卻此馬而逃亡的突厥閻洪達家人,具體而微地揭示了唐朝西域地區的交通制度以及對少數民族的統治;第9章揭出粟特人在唐朝向河西、西域咻斳娦栉镔Y中扮演的角色,視角獨特,言前人之所未言,讀了令人耳目一新[7]。與以往的粟特研究不一樣,此書給人的一個深刻印象是,作者將粟特人鑲嵌進西突厥、麴氏高昌、唐朝等各個政權中,進而通過考察出使、貿易、咻數攘鲃有袨椋?逵山煌?w制再將其統領起來觀察,這也非常符合粟特人的特性及其實際情況。第四,此書涉及西突厥、麴氏高昌、粟特、唐朝及絲綢之路等多領域的歷史學研究,且都是國際上學術研究的熱點,作者不僅積極吸收各國學者的觀點,而且還努力向國際學術界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書後所附的《引用文獻目錄》臚列了大量日文(344種)、中文(204種)、歐文(67種)論著,初步展現出作者寫作此書的學術視野。若就具體而言,書中對ulaγ一詞的考證,參閱了歐美學者S. Julien、S. Beal、P. Pelliot、W. Kotwicz、D. Sinor、G. Doerfer、G. Clauson與中國學者岑仲勉、楊廷福等人的觀點,並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說。書後所附長達7頁的英文摘要,也體現了作者努力將其研究成果介紹給西方學者的願望。此外,他還積極地用英文發表多篇學術論文[8],以便西方學者閱讀;也有不少論文用中文寫作或被譯為中文[9],他在《後記》中表達了年輕時代沒能到中國留學的遺憾,但有意思的是,落款卻寫著“2010年11月2日於北京中關村”(頁556),當時他在北京大學訪學三個月,時年55歲,終於完成了一樁心願;作者甚至還翻譯過俄文論文[10],《引用文獻目錄》中也列有2本俄文著作。總的來看,作為該領域的一線研究者,作者積極躋身於國際學界,同時也以他的傑出研究贏得了國際學界的讚譽[11]。第五,此書還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即作者對已刊論文作了大幅的增補、修改乃至新撰。此書雖然以已刊論文為基礎,但作者聲稱“原則上儘量不照搬這些論文,而是對原論文進行析分,再編成本書”(頁557)。這些已刊論文最早的發表於1982年,最晚的遲至2008年,中間跨度長達26年,特別是吐魯番文書自1981年起纔陸續刊佈,庫車、和田文書更是刊佈較晚,早年舊作確實需要參考新刊文書而作修訂,更何況作者還要實地調查原件。其中,新寫的有第1章第1節,第6章第3節之(3),第10章第1節;大幅增補的有第2章第3、4、5節,第7章第1節,第9章第1節之(2);修訂或改編的有第2章第2節,第3章第1節,第5章第1節,第6章第1節之(2)、第2節,第7章第2、4節,第9章第1節之(1)(3)(4),第10章第3節,第10章第2節。作者這種增補、修改乃至新寫的做法,固然與部分舊作發表較早、未能參考當時尚未刊佈的文書有關,但比起日本學界的通常做法,還是顯得有所不同。2015年森安孝夫出版論文集《東西迴鶻與中央歐亞》[12],就採取“原文主義”的方式,對舊作原文不作改動,另外採用頁下腳注與文末“〔書後〕”的形式進行補訂或說明。在今日中國學界,將已刊論文重新結集出版論文集之風甚盛,但大多學者不再對舊作進行修訂,再版時因為重排之故往往新添錯誤,以致新書價值反趨低劣,像劉浦江、劉安志等個別學者對已刊舊作精加修訂的極為少見[13],在當下的學風中尤顯難能可貴。此書立基於出土文書,以實證研究見長,論證紥實有據,加之善於發現,考證精微,所以新見迭出,但也出現一些疏誤,有的地方論說欠充分。第一,此書對出土文書校錄極精,甚至對不少文書作了實地調查,但在引錄文書時仍然存在失誤。例如,頁35文書第20行“陰世校”之“校”,當作“皎”;頁233文書第26行“前狀如前”之第一個“前”,當作“件”;頁409文書第99行“虞侯”之“侯”,當作“候”。有些文書中的文字頗為潦草,不易識讀,如頁190文書第136行“賈德”、第140行“氾行德”,核之圖版(圖1、圖2),末字均非為“德”,且頁198表4-2中又分別寫作“賈憙”、“氾行憙”,前後也未作統一。從文書圖版來看,實際上兩字既非“德”字,亦非“憙”字。前後未作統一的異寫之誤,在書中其它地方也時有出現,如頁85正文中“骨邏佛斯”與注釋中“骨邏拂斯”、頁92注98)的“TkM”與書中大量出現的“TKM”、頁144的“畳壹疋”和“畳一疋”,自應統一。

第二,此書據以成稿的博士論文完成於2008年,出版於2010年,但卻未使用2008年出版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14],殊為可惜。這固然是因為兩書出版時間相差較近,但荒川此書以吐魯番文書為研究重點,日本學者向來以迅捷獲取資料信息著稱,加之作者在2008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也略作修訂,卻未及時吸收利用最新出土的吐魯番文書,無疑是令人遺憾的。事實上,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出版的前一年(2007),“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在《敦煌吐魯番研究》、《西域研究》、《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西域文史》、《歷史研究》、《文物》、《中華文史論叢》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組專欄論文[15]。從時間上看,荒川氏照理應該讀到這些論文及相關文書,《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一書中也確實引用到刊於《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上的榮新江《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係》及其研究的97TSY1:13-4.5v文書(頁31);然而通觀全書可知,關於這些新獲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論文,書中也就祇引用了上舉榮文一篇而已,但該文書屬於闞氏高昌國時期,時代偏早。而有些文書及其研究論文倒是應該參考,如榮新江《新獲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人》、《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唐龍朔年間哥邏祿部落破散問題》、《吐魯番新出送使文書與闞氏高昌王國的郡縣城鎮》,李肖《交河溝西康家墓地與交河粟特移民的漢化》,畢波《吐魯番新出唐天寶十載交河郡客使文書研究》、《怛邏斯戰役和天威健兒赴碎葉——新獲吐魯番文書所見唐天寶年間西域史事》,文欣《吐魯番新出唐西州徴錢文書與垂拱年間的西域形勢》等論文及其引用研究的文書。第三,書中有些地方的論說欠充分。第2章考論麴氏高昌國的王權與粟特人,列有表2-1《麴氏高昌國粟特諸姓人物任官表》,表中共列史、康、何、安4姓、23人。首先,作者對史料的蒐集尚不完整,如吐魯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國官員史伯悅(鎮西府省事、□□□主簿)、曹仁秀(鎮西府戶曹參軍)、曹孟祐(戶曹參軍)、曹智茂(兵曹參軍)、曹武宣(鎮西府曲尺將)、康業相(商將)、康延願之父(交河郡內將)等人的相關墓誌[16],皆未統計入內;其次,如作者所言,除康姓外其他人均帶有漢式名字,既然如此,將表中之人均視作為粟特人,則頗有泛化之嫌,至少是缺乏充足的論證。儘管書中提到高昌國的交河史氏源自甘州的史姓集團,而固原粟特史氏也出自甘州的建康史氏,從而為判斷交河史氏是粟特人提供了證據鏈,但書中對這一證據鏈的論證過於薄弱,自然也削弱了作者的觀點。又如,第6章將北庭都護府推定設在西州境內,關於此點,作者祇是讓參看他在200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而未在書中作較充分的論說,以至於影響了這一推斷的說服力。第四,此書總的來說校對精良,但也存在一些錯別字。第一是引用史料出現錯誤,如:頁9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衍一重文符“々”,“絹”當作“綃”;頁247引《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茨讚水”之“讚”當作“萁”。第二是誤書個別學者的姓名,如:頁159“王青冀”當作“王冀青”,頁191“廬向前”當作“盧向前”。第三是行文中的錯別字,如:頁282“《西州圖形》”之“形”當作“經”,頁456“穎州”之“穎”當作“潁”,以及頁377注103)“trnslated”脫漏了字母“a”。2020年荒川正晴教授從他長期工作的大阪大學退休了,此前他出版了2本書,除了本文所評之書外,另一本《綠洲國家與隊商貿易》是僅有82頁的小薄冊。可以說,荒川氏在一生中主要撰寫了《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一書。如果放在今日急劇膨脹的出版業與大多著作等身的學者中看,荒川氏一生祇做一件事、祇寫一本書,似乎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卻立足於世界學術之林,此種現象豈不令人深思?此書出版以後,荒川氏又與人合作撰書,陸續出版了《寫給市民的世界史》、《絲綢之路與近代日本的邂逅——西域古代資料與日本近代佛教》、《中央歐亞史研究入門》等書[17],2022年初又出版了由他領銜主編的《巌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卷《中華世界的重組與歐亞東部 4~8世紀》[18]。荒川氏儘管已經退休離開了阪大,移居到日本海一側的島根縣松江市,但仍在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他表示將要研究唐代通行證、粟特人兩個課題,衷心地期待他迎來學術第二春。[1] 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交通·交易と唐帝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年,頁v+630。
[2] 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第1號,1988年8月26日;收入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編《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情報集錄——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 1-50號——》,1991年,頁1。
[3] 荒川正晴《オアシス國家とキャラヴァン交易》,山川出版社,2003年。
[4] 在粟特研究領域,荒川正晴先後發表以下系列論文:《唐帝国とソグド人の交易活動》,《東洋史研究》第56卷第3號,1997年,頁171-204;《唐代トゥルファン高昌城周辺の水利開発と非漢人住民》,森安孝夫主編《近世・近代中国および周辺地域における諸民族の移動と地域開発》,1995-1996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B)(2)研究成果報告書,1997年,頁49-64;《北朝隋・唐代における“薩寶”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東洋史苑》第50、51合併號,1998年,頁164-186;《ソグド人の移住聚落と東方交易活動》,樺山紘一等編《商人と市場》(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5),岩波書店,1999年,頁81-103;《唐代前半の胡漢商人と帛練の流通》,《唐代史研究》第7號,2004年,頁17-59;《唐代粟特商人與漢族商人》,榮新江、華瀾、張志清主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中華書局,2005年,頁101-109;《麴氏高昌国の王権とソグド人》,《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職記念論集 古代東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汲古書院,2007年,頁337-362;“Aspects of Sogdian Trad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Western Turkic State and the Tang Empire.”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2, 2011, pp. 25-40;《唐代天山東部州府の典とソグド人》,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汲古書院,2011年,頁47-66;《西突厥汗國的Tarqan達官與粟特人》,榮新江、羅丰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科學出版社,2016年,下冊,頁13-23;“The Silk Road Trade and Trader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74, 2016, pp. 29-59;《ソグド人の交易活動と香料の流通》,《専修大學 古代東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5號,古代東歐亞研究中心,2019年,頁29-48。
[5] 荒川正晴《唐代の交通システム》,《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40號,2000年,頁199-335。
[6] 另外,大谷文書也有部分可能來自於吐魯番阿斯塔那墓羣。
[7] 近年,李謇C發表《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絲綢之路上的劍南絲綢》一文,也提到“在劍南絲綢在絲路上更深入的前行中,粟特商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見《敦煌學輯刊》2019年第3期,頁39。
[8] Masaharu Arakawa,“The Transit Permit System of the Tang Empire and the Passage of Merchants.” Memoirs of the Res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59, 2002, pp.1-21; “Passports to the Other World: Transformations of Religious Beliefs among the Chinese in Turfan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 D. Durkin-Meisterernst, S. Raschmann, J. Wilkens, M. Yaldiz & P. Zieme (eds.),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19-21, 1pl; “Sogdian Merchants and Chinese Han Merchant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é. de la Vaissière and é.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5, pp. 231-242; “Sogdians and the Royal House of Ch‘ü in the Kao-ch‘ang Kingdom.”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94, 2008, pp. 67-93; “Aspects of Sogdian Trad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Western Turkic State and the Tang Empire.”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2, 2011, pp. 25-40; “The Transportation of Tax Textiles to the North-West as part of the Tang-Dynasty Military Shipment Syste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2, 2013, pp. 245- 261; “The Silk Road Trade and Trader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74, 2016, pp. 29-59.
[9] 前者有:荒川正晴《唐代粟特商人與漢族商人》,榮新江、華瀾、張志清主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頁101-109;《唐代天山東部州府的典和粟特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編《國學的傳承與創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與科研六十周年慶賀學術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下冊,頁952-966;《西突厥汗國的Tarqan達官與粟特人》,榮新江、羅丰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下冊,頁13-23。後者有:《唐政府對西域布帛的咚图翱蜕痰幕顒印罚ㄍ跣米g、李明偉校),《敦煌學輯刊》1993年第2期,頁108-118;《關於唐向西域輸送布帛與客商的關係》(樂勝奎譯、李少軍校),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6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42-353。《唐代于闐的“烏駱”——以tagh麻札出土有關文書的分析為中心》(章瑩譯),《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頁66-76。《關於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中的ulaγ》(李徳范、孫曉林譯),胡厚宣等編《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1998年,頁198-211。《唐帝國和粟特人的交易活動》(陳海濤譯、楊富學校),《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頁81-91。《唐過所與貿易通道》(歐陽暉譯、朱新校),《吐魯番學研究》2005年第1期,頁40-49。《北庭都護府的輪台縣和西州長行坊——以對阿斯塔那五〇六號墓所出與長行坊有關文書的討論為中心——》(尹磊譯、于志勇校),《吐魯番學研究》2006年第1期,頁132-148。《英國圖書館藏和田出土木簡的再研究——以木簡內容及其性質為中心》(田衛衛譯,西村陽子、榮新江校),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6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35-47。《粟特人與高昌國麴氏王室》(殷盼盼譯),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27-42。
[10] Л. И. チュグイェフスキー著、荒川正晴譯《ソ連邦科學アカデミー東洋學研究所所藏、敦煌寫本における官印と寺印》,《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第98、99號,1994年,頁1-14。
[11] 如耶魯大學歷史系韓森稱“荒川教授已經發表了許多關於絲綢之路貿易和吐魯番的傑出之作”,見其《絲綢之路貿易對吐魯番地方社會的影響:公元500—800年》,榮新江、華瀾、張志清主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頁130。
[12] 森安孝夫《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年。
[13] 劉浦江《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自序”云:“有的學者在將論文結集出版時,聲稱為保持原貌而不對文章加以改動,那樣一來,豈不祇是舊文的彙集重刊而已?我頗疑心這是懶惰的一個借口。……作者編選自己的文集,怎麽可以一仍其舊呢?我有一個長年養成的習慣,在每篇論文發表之後,都會隨時將所知所得記錄下來,以備它日修改之用。因此需要說明的是,收入本書的論文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訂”,中華書局,2008年,頁2。劉安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關於後書,筆者曾撰寫過書評,稱:“還值得提倡的是,作者在編集本書時,對收錄的每一篇舊作論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尤其是《讀吐魯番所出〈唐貞觀十七年(643)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孫氏辯辭〉及其相關文書》、《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唐高宗咸亨年間的西域政局》、《對吐魯番所出唐天寶間西北逃兵文書的探討》、《唐代西州的突厥人》等四篇成文較早的論文,更是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學術研究譬如積薪,從來都是逐漸進步的,可貴的是能夠不斷地進行自我修正,從而推進學術的進展。作者除了對舊作進行修改之外,有時還在注釋中指出自己以前的錯誤觀點,進行糾正”,見馮培紅《出土文書與傳世史籍相結合的典範之作——劉安志〈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介評》,《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3期,頁168。
[14]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荒川書後所附《引用文獻縮略號》中未列此書,而《吐魯番出土文書》、《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大谷文書集成》、《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寜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等書則均在列。
[15] 這些論文後來編集為兩本論文集: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論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孟憲實、榮新江、李肖主編《秩序與生活:中古時期的吐魯番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除了2007年在多家刊物集中發表專欄論文外,二書還收了個別發表於2008、2009年的論文。
[16] 前5人見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巴蜀書社,2003年,頁360、91-92、103-104、223-224、370;後2人見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下冊,頁378-379。
[17] 大阪大學歷史教育研究會編《市民のための世界史》,大阪大學出版會,2014年;《シルクロードと近代日本の邂逅——西域古代資料と日本近代仏教》,勉粘霭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