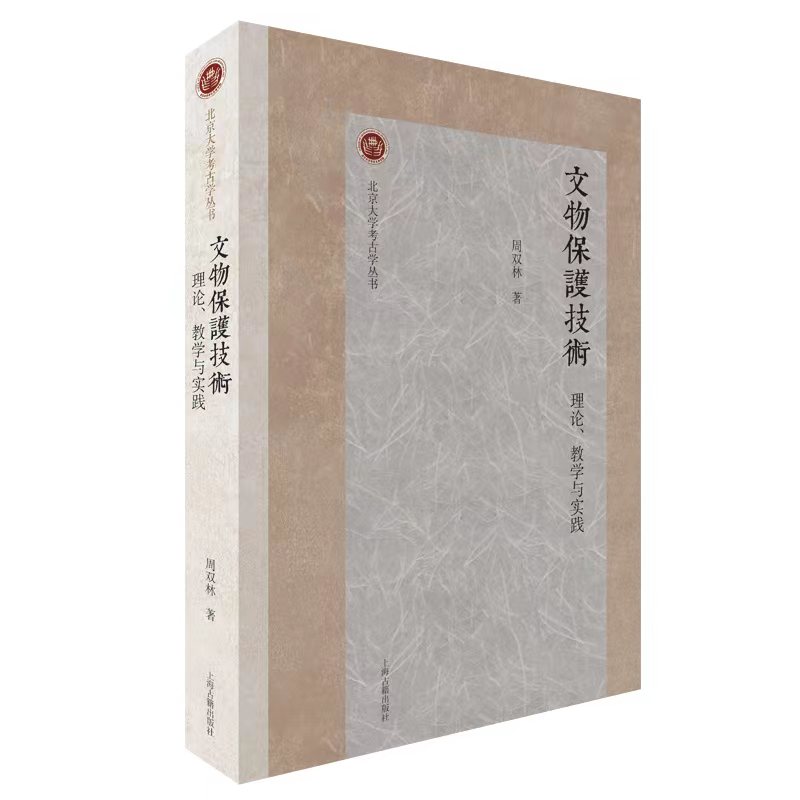专家观点
我与北大考古︱周双林:有过平淡与艰难,更有那些美好的回忆
进入文物保护界是一个偶然。大学毕业主要采取的是分配制,少数人自己找工作。我当时毕业时初步分配在外地,后来换成了河南省博物馆,因为那边有个指标而且离我家最近,公交只需五站地。我对这地方非常熟悉,小时候经常去参观,还在对门河南电影院看电影,都是走了来走了去的。
进入河南博物馆的十年是一段比较平静的时光,文物行业延续着既往的平淡。十年后期有了变动,因为建成了新的博物院。
那时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年初申报些经费,买些化学试剂、手术刀、玻璃容器等,做些简单的保护工作,例如纺织品开春的杀虫防霉、日常的青铜器去锈缓蚀、陶瓷器的脱盐保护等。经常去库房是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也能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将收藏几十年的青铜器拿出去做X光,拍出了几十字的铭文,后来李伯谦先生就说这很重要。剩余的很多时间就用来看书。那时时间很多,每年看一种类型的书,比如今年看金属的书,明年看陶瓷的书,后年就看木材的书。那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乐趣是逛书店、买书,但是经常捅窟窿,这边多花钱,那边就得收紧裤腰带过日子。这十年工作中也有一些难得的培训,比如1991年在泰安的培训,见到了陆寿麟、黄克忠、李最雄等我一直仰慕的专家真人;1994年在陕西考古院的培训,见到了修复水平很高的德国专家;1996年在陕西文保中心跟意大利专家学习青铜和陶瓷器的修复,也遇到了很多在以后成为很厉害专家的业内同行。
之后进入北京大学是不断提高的结果。从1990年代开始,国家文物局在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搞了在职研究生培训,我非常想去,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都未能如愿。到了1997年北京大学开设文物保护专业,在物色培养相关人员,我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来到了北京大学。
三年的博士学习是很艰苦的。我辞掉了河南博物院的工作,也就没有了工资,每月只有320块的补贴。家里是管不上了,有时候连自己都顾不上,记得第一个“十一”国庆,身上没钱了,还找室友借了3次钱(总共不到30块),就用这30块钱挨到了下次发补贴。这个时候家里已经很难了,我考试的时候岳母已经确诊了尿毒症;孩子还小在上幼儿园,上学放学没人管,可以想象这三年的艰难。
这三年也是迅速提高的阶段。除了出现场、外出开会或者回河南的家,每一天我都过着“机械”的生活,早上起来上课,中午回来午休,晚饭后直接去实验室,晚上11点多回寝室,跑操、睡觉,每一天都是如此。那一段时间,在赛克勒博物馆熬夜的就那么几个人。每天的任务就是读书、做实验、为了实验找材料。有一次为了找紫外线吸收剂,转车几次跑到北京和廊坊交界的一个村子的化工厂,还记得接待我的那个技术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姓氏。这三年也读了一堆外文资料,比如去陕西文保中心时复印的意大利专家带来的资料,去国家图书馆借阅并复印了外文书,还有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国外文物保护会议的论文集。后来这些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博士论文选择的是土遗址保护方向,这也决定了后来几十年的科研领域,以至于在之后的20年都很难跳出这一领域,因为做顺手了就停不下来。要知道我在河南博物馆的时候主要是做室内文物保护的。
博士期间,院里的文物保护专业开始招收文物保护方向的本科生,我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外,还帮着上课带学生。头几次的课主要是请北京的专家来讲的,我们几个年轻的博士只讲其中一小部分。然后慢慢地就全部接手下来了。
我的课程是“文物保护材料”和“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开前一门课是因为我有化学的底子,讲后一门课是因为我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土遗址保护。
课程开设费劲,而学生还比较少,功效比低。
开设一门新课需要做课程内容设计,要查资料、找案例,才能把需要讲的内容充实完善,还要设计好PPT。每开设一门新课,一般先写出大纲,逐步填充内容,然后再做PPT。需要图片的时候,一种是扫描,一种是自己画,还有一种是自己去拍。当时为了开课,找了很多的书来扫描,扫描完了再用Photoshop修图。案例方面的,则去各个文保单位的网站上找发表的文章,一些文章带彩图,就比较省事。还有就是自己去现场拍,很多时候是在搞项目时随时拍下的。带着相机到处拍照,是收集资料最常用的方法,包括逛博物馆时、参观实验室时、看古建筑古遗址时,还有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时。网站也是找资料的一个很好的渠道,起初还用BBS的时候,可以去国外的网站找资料,上面有很多资料;上盖蒂研究所、ICCOM等网站也可以找到不少。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英文资料,开始是纸质的,后来就用学校网站订购的英文期刊的资料。收集的资料很多,几乎没有整理完的可能。在这之后,我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课程的很多照片,用的都是我自己拍摄的照片了。自己拍的照片,角度是自己选择的,带有我自己的深刻认识。
在这20年中,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学生的数量却很少。考古文博学院新增的10个本科名额是同时给文物保护和古代建筑专业的。为了方便,两个专业隔年轮流招生,今年是文物保护专业招生,明年就轮到古代建筑专业招生,这样每个专业可以招够10个学生。但是轮到文物保护专业时,要么招不满,要么中途有转院的。
校内的学生少,相反校外的学生却源源不断,他们主要来自国家文物局的在职培训。最开始是中意班的培训:中国—意大利政府合作进行在职人员培训。开培训班时,我正好备了4年课,而且我与中意合作培训也有渊源,我1996-1997年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首次中意合作文物修复人员培训,那时候是作为学员参加的。从2004年起,我帮助国家文物局做了很多次在职培训教学,在这过程中也认识了很多在地方勤奋工作的同行,后来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对文物保护专业人才的需求倒推了学校培养相关专业学生的需求,因此一些学校就开始招收修复保护方面的学生。为了帮助这些学校培养人才,我也先后去一些学校讲一些课,比如去廊坊、顺义给北京城市学院开设保护材料课程,去安阳给安阳师范学院开设修复保护概论课程,还有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开设建筑保护课程。
最近又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培养方式,就是学校开设的外国专家讲座。这个讲座开设的目的是开阔学生的视野,了解国外的学科发展。从2019年开始,我出面组织了几次活动,讲座的专家包括日本著名文保专家泽田正昭先生、意大利著名文保专家米盖利先生。这样的讲座除了线下外,还可以开放线上,受众就比较多,好多国内做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士,自己本身学识过人、经验丰富,在文物保护方面遇到了很多问题,对外国也就有了了解的需要。我觉得这种讲座要经常进行,文物保护应当是国际性的。
现在回头看自己在学校的20年,主要工作有这些:
培养了一些学生:十几位研究生,包括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还有替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带的研究生,还有指导过本科论文的十几位学生,他们基本都进入了文博行业,有些已经是副高职称。
做了一些项目:国保级的遗址保护项目通过了12个。涉及的项目就多了,大大小小有100多个,几乎涉及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地,还有国外的项目如新加坡的近代建筑保护。
写了一些文章:有研究思考,有工作体会,有保护总结,大大小小有100多篇,但是发表级别都不高,这个行业毕竟小众,遗址技术保护更加小众。
帮助和关心了一些学生:有学生新入文保行业,需要建议和资料;有学生考研或者出国需要指导;还有外专业的学生想了解文保技术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认识了不少年轻人,让我自己也觉得还毕竟年轻。
现在算来,从业已经35年,在文物保护领域也算做了些工作,至少还算比较努力。也应该感谢一路上帮助我进步的人们。感谢在河南博物馆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们,周贵祥书记、王世俊院长、付玉芳主任、王玮老师、杜安兄弟;感谢在河南的时候,经常帮助我的陈进良先生、张居中先生、曹桂岑先生;感谢我的导师原思训先生;感谢经常在课题上帮助我进步的黄克忠先生;感谢在专业发展上帮助我成长的詹长法老师;也感谢各地的合作伙伴,大家从合作做项目开始,最后成了经常惦记的好朋友;感谢在分析检测上帮了我20多年的杨文言老师、郑爱华老师。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容纳了我,感谢各位领导和同事在教学科研上的各种关心和帮助。感谢课题组的学生们,希望他们多出成果,多写文章。
本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文物保护技术:理论、教学与实践》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