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获得新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10年获赠了500多件文书(以下简称“人大文书”),其中汉文文书300多件、于阗文文书160多件、粟特文文书13件、古藏文文书16件以及梵文残片50多件。由此,相关研究深入展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于2020年12月立项,2021年4月19日召开开题报告会,课题负责人孟宪实和子课题负责人段晴等发表计划。特邀专家郝春文、王素、张平、李肖、肖小勇等分别就课题进展、文书研究和整理提出建议。课题组成员荣新江、萨尔吉、史睿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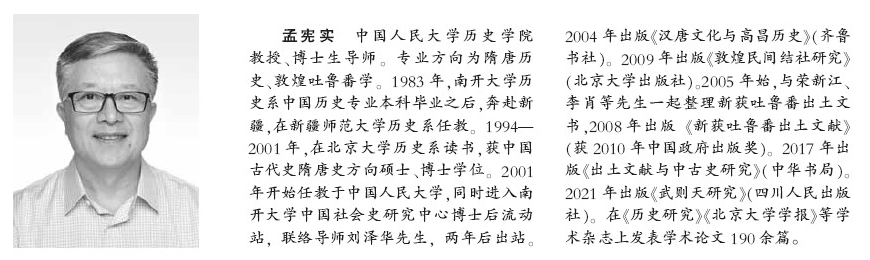
课题组成员随即展开工作,主要由张晓辉、张美芳老师负责,对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西域出土文书展开修复与整理。截至2022年6月,已经完成全部唐代西域文书本体的修复、测量、拍照、镶接等工作,在原有文书的基础上,竟然有了新的发现,一包文书碎片原来没有进行统计,通过修复,竟然发现新文书几十件。文书上新发现了汉文、于阗文、婆罗迷文等全新文字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本课题的重要新发现和新成果。研究按照计划逐步展开,如今,首批成果已经面世。
根据相关文书提及的时间和地名信息,推测这批资料来自唐代杰谢镇(今和田丹丹乌里克和老达玛沟一带)。因为这里曾经出土过文书,所以新资料的出现不仅带来新的文书信息,更能够推动原有文书研究的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以《新资料、新视野——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文书研究》为总标题,分别发表四篇论文,围绕这批珍贵文献的学术价值展开论证。
在这批文书中,于阗语文书对于了解于阗这片绿洲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于阗历史,于阗文具有特殊性,是汉文史料之外产生于当地的本土史料。于阗文与汉文文献交叉对比、配合研究,是研究于阗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段晴教授的《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文书的学术价值》一文,利用人大文书的相关材料和研究,积极展示了这批文书的重要学术性。比如,这批文书之中有一件《一万颂般若》的梵文残片,证明此经来自梵文世界,而此前一直有人怀疑该经的梵文来源,甚至认为此经出自西藏僧人之手。现在,一个梵文断片,证明了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原有的怀疑是缺乏依据的。于阗文《僧伽吒经》残片的识读同样意义重大。此前,学界通常的观点认为,佛教经典经过西域(包括于阗)传入中原,始终存在由西而东的过程。那么,在佛教传播史上,是否存在由东而西的问题呢?过去的研究往往从政治事件中探索这个问题,比如北凉余部从河西走廊退到高昌郡(今吐鲁番),河西佛教从而大面积进入西域。这可以看作是佛教由东而西的事件。但是,从佛教经典的视角,是否也能发现类似的过程呢?这件文书残片的意义,正在于此。通过研究得知,《僧伽吒经》的翻译首先有中原的汉译本,然后才有于阗语译本。这就告诉我们,西域与中原的佛教关系应该比此前的理解更加丰富多样,或许由西而东是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由东而西的传播进程。于阗的军政体制是如今许多人所不熟悉的,在唐朝被称作羁縻府。一方面,于阗的民政由毗沙都督府管理,都督的另一称谓叫于阗王。于阗国王和都督,在接受唐朝皇帝的册封之后才算合法。另一方面,唐朝中央在于阗有驻军,这就是于阗镇守军。那么,于阗百姓是怎样生活的呢?段晴教授通过人大文书具体生动地展现了一位名叫勃延仰的于阗人,他是在于阗官府与镇守军的双重管辖下进行工作的。这是很有历史感的画面,为研究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提供了重要证据。
孟宪实的《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以镇守军相关文书为中心》一文指出,人大藏的这类汉文文书不仅是所有藏家中件数最多的,而且有纪年标志的汉文文书就有20件,这在各地的藏家中也是最多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带有武则天纪年的文书记。在此之前,学界了解的于阗出土汉文文书,最早的属于玄宗开元年间。武则天时代文书的发现,证明在武则天收复并重设四镇之后,相应的管理工作已经开始。安史之乱后,中央与西域的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史籍关于西域的记载也十分缺乏。检核人大文书可以发现,人大文书主要是武则天之后和安史之乱之后这两个时期,这批文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对于于阗镇守军与于阗王府的互动关系、镇守军如何在与中央联系断绝的条件下守卫边疆等问题,这些文书都提供了具体证据,是我们了解当时西域情况的重要材料。安史之乱发生后,驻扎在西域的军队派出主力增援中央,导致西域的唐朝军力下降,保护西域的任务更加艰巨。但是,西域的唐朝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奋斗、加强团结,保卫西域长达四十年。这是十分难得的历史业绩,值得后人铭记。
粟特人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国际商人,对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多方面影响。虽然学界之前已意识到唐代于阗应该有粟特人光临,但直到人大文书的出现,学界才认识到于阗在粟特人商业世界的地位。毕波的《粟特人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粟特语文书为中心》一文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人大粟特文书中,有很重要的粟特人书信,清晰地表明粟特人拥有跨地区商业网络——该网络涵盖了从中亚到中国的广阔区域,西起粟特本土、七河流域,东至唐都长安,南入吐蕃控制的青藏高原,北及回鹘腹地的蒙古高原,而于阗就是粟特商业网络的重镇之一。对于粟特商人经营的具体商品及其经济实力,这些文书也有所反映。尽管信息有限,却强有力地印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状态。
于阗的唐朝守军,主要来自中原。段真子的《汉文典籍与书法帖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文书为中心》一文就讨论了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即中原的传统典籍在唐代和田地区扮演着何种角色。在人大文书中,既有《孝经》等儒家经典,又有《兰亭集序》《尚想黄绮帖》等书法摹本。安史之乱后,虽然昆仑山下的唐朝军队已与长安失去联系多年,前途未卜,但唐朝军人还有可能在背诵《孝经》、教孩子临写王羲之的书法。通过这些残纸断篇,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强大生命力,而所谓文化生命力,正在于一般百姓、普通士兵的坚持。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希望这批材料能为我们揭示更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当时该地区商业、军事、语言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了解,从而加深我们对唐代的西域管理和丝绸之路的认识。(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2日第25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