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
本书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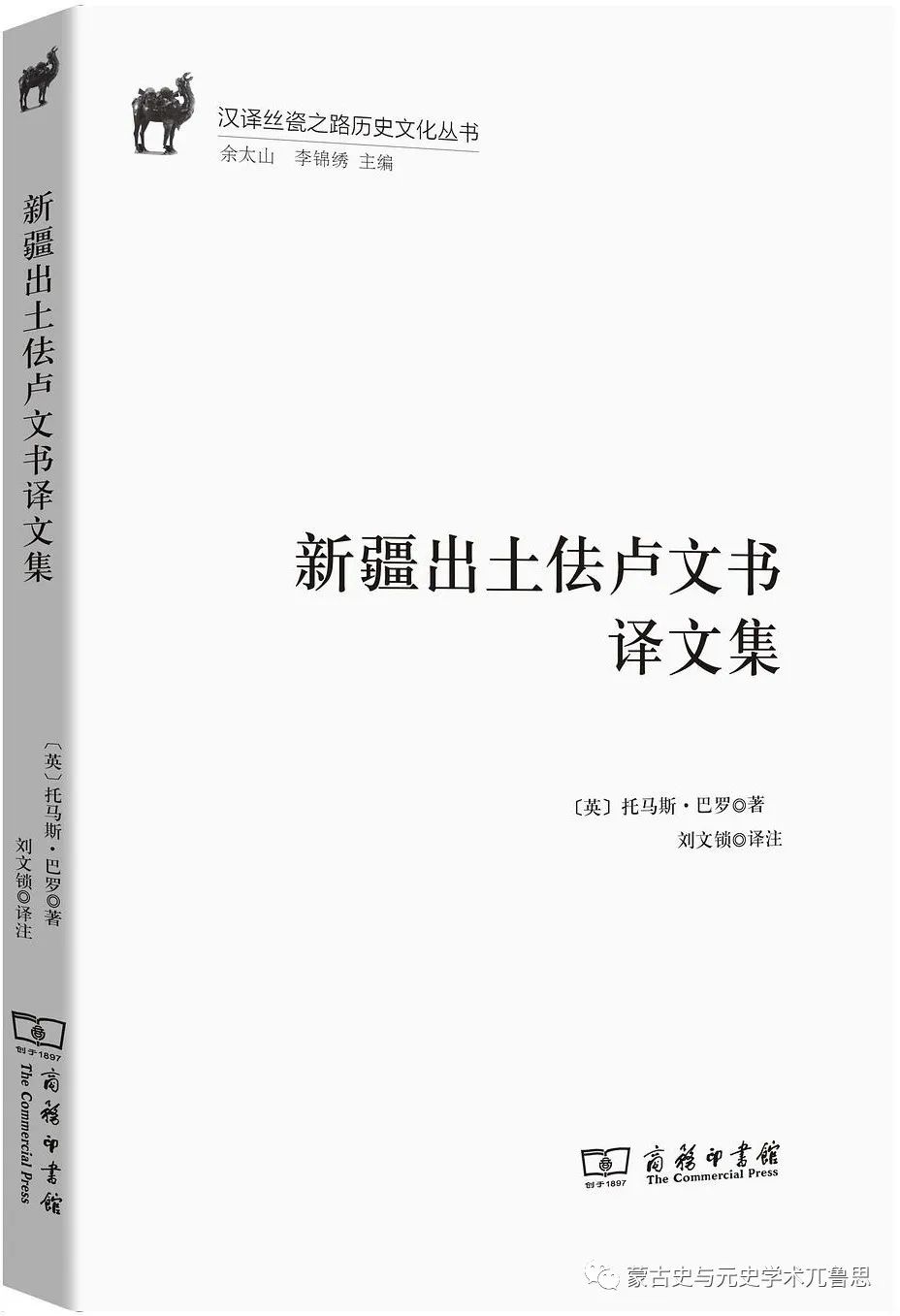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
作者:〔英〕托马斯·巴罗
译者:刘文锁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品方:商印文津文化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页数:308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120.00元
丛书: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ISBN:978-7-100-22635-6
作者简介
托马斯·巴罗(Thomas Burrow,1909—1986),梵语专业,1937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7—1944年间在英国博物馆东方书籍与写本部工作。1944年任牛津大学博登梵语教授(Boden Professor of Sanskrit),工作至1973年退休,为著名的佉卢文专家。
译者简介
刘文锁,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获学士学位。1988—1997年间,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任助理馆员、馆员。1994—1995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等访学。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博士学位。2000—2002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2002至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教研室主任。研究领域新疆与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发表过《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丝绸之路——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等若干论著,译著有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主要译者)、《理论考古学》(合译)。
内容简介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是关于新疆尼雅遗址等地出土的怯卢文书的译文集。原著于1940年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出版,是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巴罗(Thomas Burrow)对新疆出土怯卢文书中保存较好的490件文书进行的释读和英译。这些文书涵盖了怯卢文书的各种类别,具有西域史学和历史语言学等多方面的价值。译者在翻译原著时,根据自己对文书的理解尽可能做了注解,还收录了巴罗释译的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时在尼雅遗址获得的18件怯卢文书,并在文末对原著文书中的专有名词做了词汇索引,以便读者参考。
编辑推荐
★关于新疆尼雅遗址等地出土佉卢文书的经典译文集!
★原著于1940年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出版,具有西域史学和历史语言学等多方面的价值!
目录
本书前言
现时刊布一部完善的怯卢文书译文为时尚早。晦涩难懂的句子仍待澄清,诸多词语仍然不明。虽然如此,这是个尝试的时机,因为它对众多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来说是基本的,这些问题涉及语言学及其他与文书相关的方面,它们须得使一个更宽广的学者圈子加入进来,而非迄今所见的情形。这只能由一个在文字上尽可能精确的译文来实现。
当然,大量的文书都能够确切地译出,当此种情形下就径直给出了其译文。很多例子属于一个词语不明而整句的其余部分则是清楚的,在翻译上不明确的词就用斜体来表示。一些头衔如cozbo等,其意思大致可明,但也用斜体表示。凡在翻译一个特别的段落上出现疑惑之处,则在其末尾处用括号加问号标示。对于无法翻译的段落,则插入一个带问号的括号。原本残损的地方用方括号里加一行小点来表示。一再出现的固定词组,当第一次译出后就不再翻译,用“等等”及一行小点来表示。
我未能做广泛的注解。关于解释的基础,读者可参见我的《新疆出土怯卢文书之语言》一书。简注用于:(1)改正文本的读法;(2)凡前述著作里的信息需要补充或更正之处。书末附了一个在注解中如是讨论过的词语的索引。对从改进后的读法里产生的新词,在其前面则加了一个星号。一个小十字符号加在那些应当删去的词语之前。那里也吸收了关于单词的一定数量的其他信息。
当拉普森(E. J. Rapson)教授及其同仁编定之后,文书被分藏在了英国和印度。第213—427号文书和第510—565号文书现在收藏在英国博物馆,其余的在德里。由是,除了照相之外,我所见到的仅是上面提及数目的文书之原件。在这些文书的注解里的更正,是基于对其原件的核对。而其余文书的情况,其中大多数的照相都无法获得,它们要么是基于由其编者自己所建议的选项,要么就是推测。无法接触原件这一缺陷,对前面的二百件文书来说是个不利因素。后来在第二和第三卷里编者们对文书本身更确知了,因而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了。
那些仅包含人名的文书以及那些过于残损而不能翻译的文书,本著都略去了。
本书译注者导言
一、新疆佉卢文文献的发现与释读
在新疆获取的佉卢文(Kharoṣṭhī)文献资料,始于所谓的“和田藏卷”,即书于桦树皮上的佉卢文《法句经》(Dharmapada)残叶,发现于1890年代初。它包括俄国驻什噶尔总领事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 Peterovsky,1837—1908)购得的几叶,以及法国杜特雷伊·德·兰(Dutruil de Rhins)探险队所得的三叶残卷及若干碎片。埋藏的地点在和田喀拉喀什河岸的库玛日山石窟。这批早期佛经写卷年代约为2世纪,先后由奥登堡(S. F. Ol’denburg)和布腊夫释读与刊布。对早期佛典的研究来说,和田的佉卢文《法句经》残卷,可以与吉尔吉特的瑙普尔写卷(Naupūr manuscripts)、巴米扬写卷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出的两批桦树皮佉卢文写卷等相提并论。
另一类材料是和田等地出土汉佉二体钱(The Sino-Kharoṣṭhī Coins)上的佉卢文铭文,它们已得到释读并有所刊布。与写卷大为不同,这种钱币铭文数量和内容有限,通常也不受语言学家的重视。最具语言学和文献研究价值的,是出自尼雅、楼兰和米兰遗址的佉卢文书与题记等。这其中以尼雅遗址所出的佉卢文简牍与皮革文书为主要部分。其旧出者主要为斯坦因(M. A. Stein)所得;新出者系1950年代以来历次尼雅遗址探察活动中所获得的文书,数量上仅占一小部分。尼雅和楼兰所出佉卢文书的数量,迄今已有1200余件,内容上可以分作国王谕令、籍账、信函、法律文书(判决书)、社会经济文书(书面契约)、佛教文献、文学作品和杂类(占卜文书等)。其年代约在公元3—4世纪。上述佉卢文书的转写、释读和翻译工作,大致与文书的发现同步。第一批文书出土后,英国语言学者E. J. 拉普逊(E. J. Rapson)即受委托着手文书的释读。后来这项研究工作还有其他几位欧洲语言学者(A. M. Boyer、E. Senart、P. S. Noble)的参与。截至1929年,佉卢文书中的主要部分764件都得到了转写、释读和发表。这就是那部称作《佉卢文题铭》的著作。它刊布的文书绝大多数出自尼雅遗址(遗物编号N的文书,第1—659、709—751、758—764号),少数出自安迪尔夏阳塔格一带的遗址(遗物编号E的文书,第660—665号)、楼兰故城遗址(遗物编号L. A的文书,第666—701、754—756号)、罗布泊L. B遗址(遗物编号L. B的文书,第702—706号)、罗布泊L. M遗址(遗物编号L. M的文书,第752—753号)、罗布泊L. F遗址(遗物编号L. F的文书,第757号)、敦煌烽燧遗址(遗物编号T的文书,第708号)。另一位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巴罗(T. Burrow)选取了《佉卢文题铭》中转写的保存状况较佳的490件文书,加以自己的释读,做了英译和简要注释,即《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一书。在此之前的1937年,他还发表了《尼雅佉卢文书别集》一文,刊布了《佉卢文题铭》一书编号以外的18件文书(编号765—782)的释读和译文。这批文书系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时(1930—1931)于尼雅遗址所获者。根据《佉卢文题铭》,林梅村于1988年出版了《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收录了由他转写、译释的588件佉卢文书。这些文书分作三个类型:国王谕令、籍账和信函。它们在类型上与巴罗《译文集》所释译的文书有一些差别。
198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佉卢文书,曾由华盛顿大学邵瑞祺(Richard Salomon)教授做过零星的释读。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于1991—1995年新获的简牍,先由日本佉卢文学者莲池利隆氏转写、释译并发表,后来又由中国学者林梅村重新释读过,二者可以比照。最近,段晴教授刊布了流散到青海省藏医药文化博物馆的4件佉卢文木牍,皆属斯坦因分类中的矩形牍,采用封检式的双牍,内容皆为判文(判决书),据认为当出自尼雅遗址N. XIII(93A10)遗迹。它们在形制与内容、文书格式上,均与尼雅遗址所出的同类型文书相同。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以下简称《译文集》)是托马斯·巴罗教授 (1909—1986)的主要著作之一。他的著作《梵语》(The Sanskrit Language,1955)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他的专业是梵语,1937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7—1944年间在英国博物馆东方书籍与写本部工作。1944年任牛津大学博登梵语教授(Boden Professor of Sanskrit),工作至1973年退休。他的另外一部研究佉卢文的著作,是《新疆出土佉卢文书之语言》。这是部讨论新疆佉卢文的语言学著作,可以和《译文集》、《佉卢文题铭》一道相互参阅。关于《译文集》的刊布情况,前文已有所述。由于挑选的是《佉卢文题铭》里保存状况较佳的文书,所以文书的内容包罗了佉卢文书的各个类型,包括国王谕令、籍账、信函、法律文书(判决书)、社会经济文书(书面契约)、佛教文献、文学作品和杂类(占卜文书等)。这无疑提供了新疆佉卢文书的一个概貌,对于除语言学外的历史研究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是,巴罗的《译文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在释译时将几种格式化文书(国王谕令、信函、法律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的开头部分,大多都省略掉了,而这些格套化的用语都是文书接受者的头衔、名字等,当然十分重要。它们除了对研究当时的官僚体制有意义外,还可以对之开展年代学的研究,以及确定这些文书中所涉及的实务都是分别针对什么官员发布的。
《译文集》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巴罗在书末所附的索引太过简略。此外,他也没有注明每件文书的田野编号—这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文书的出土地点和共存关系等。鉴于上述的缘故,我在翻译《译文集》时,决定采取译注的方式,即除了照译巴罗的原文外,还增加了下述几项内容:
1. 增补了每件文书的出土遗物编号、简牍的形制类型、遗物和释文的出处等几方面基本信息。波耶尔(A. M. Boyer)等在《佉卢文题铭》里所做的释读编号,仍予保留。这个编号系统是国际上研究者们所遵循的。每件文书所对应的出土遗物编号,即是斯坦因的探险报告《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亚洲腹地考古图记》(Innermost Asia)里的遗物编号。这些增补的内容以“注”的形式,补加到每件文书译文之后。鉴于佉卢文书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相信这些信息对研究者来说是必要的。相应地,对于巴罗在一些文书的译文后所加的语言学等方面的简注,则以“原注”说明,以与译注者的注释区分。
2. 对巴罗英译中所省略去的一些格式化用语,都做了还原(以“〔〕”标记)。这些用语如楔形牍国王谕令、矩形牍信函的抬头和尾句等,无疑对分析各种文书的内容、格式等来讲是重要的信息,故依据《佉卢文题铭》并参照林梅村《沙海古卷》做了还原。
3. 以附录形式(附录一)增补译注了巴罗在1937年发表的《尼雅佉卢文书别集》一文。《别集》里刊布的是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时于尼雅遗址所获的18件佉卢文书的释读和英译,它们原本属于尼雅佉卢文书的一部分。
4. 以附录形式(附录二)做了一个尽可能详尽的专有名词索引,以方便检索。巴罗原书末附录的索引毕竟简要,对需要深度研究这些文书的人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我根据翻译时的理解,重做了一份索引,其范围包括各种专有名词(人名、地名、职官或职务名称、行政区名等)。由于我并不是佉卢文的专家,所以对它的编排规则采用的是英文字母的顺序,其中可以酌定其汉语意义者则加之汉译;各条后附上该词所出现的文书之编号,以便使用者核对或做有关分析时参考。我相信这个索引对于研究者来说会发挥有益的作用。
5.为便于读者认知尼雅遗址和出土文书,在书中正文前以图版形式补充了尼雅遗址和各类型文书的图片。需要说明的是,巴罗的《译文集》曾有一个非正式出版的汉译本,就是新疆社会科学院已故王广智先生的译本,收入韩翔、王炳华先生所编《尼雅考古资料》中。对王广智先生当年殚精竭虑翻译的译本,我愿在此借机表达衷心的敬意!
巴罗、贝利和林梅村等语言学家曾指出,尼雅和楼兰佉卢文所拼写的印度西北俗语或尼雅普拉克里特语(Niya Prakrit)或犍陀罗语(Gāndhārī),混杂有伊朗语、吐火罗语、于阗塞语、粟特语、希腊语、汉语等在内。除大量伊朗语词外,还有约1000个专名及150个词语,包括职衔、农产品名称、衣物等,与印度普拉克里特语不同,为鄯善国语言。这样复杂的语言情况,一方面反映出文书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对于文书从释读到翻译的工作,必然带来诸多历史语言学方面的困难。对此我愿向那些语言学家表达衷心的敬意!
新疆佉卢文书中提及的专有名词很多,包括各种职衔名称、地名、人名以及行政区名称等。除大量人名外,表述职务或头衔的名称达四十六种,其中一部分的意义可以大致推定,巴罗和林梅村教授都做过推测,这些职官名称的汉译在本《译文集》里主要采用了林梅村《沙海古卷》中的译法,诸如:apsu(曹长)、arivaǵa(向导)、ari(贵人)、aǵeta(税吏)、cuύalayina(监察)、divira(司书)、karsenaύa(甲长)、kori(御牧)、koyima(司谷)、mahatvana(大夫)、śadavida(百户长)、ṣoṭhaṃgha(税监)、tasuca(祭司)、toṃga(督军)、vasu(司土)、yatma(司税)等。另一些则难以确知,如acoviṃna、ambukaya、apru、aryaǵa、aṣǵara、caraǵa、daśavita、klaseṃci、masiṃciye、suύeṣta、vaṭayaǵa等。还有若干名称,按文书的上下文,可以理解为封号或爵位之类的名称,如埃卡罗(ekhara)、古速罗(guśura)、卡拉(Kala)、吉查依查(kitsaitsa)、柯罗罗(korara)、奥古(ogu)等。对此,孟凡人先生采取的是音译的方式,但其中的一部分被林梅村教授意译为侯爵等称号。作为最重要职称之一的cojhbo(cozbo),林梅村译为“州长”,研究者一般都予采用。不过,段晴教授在其著作中否定了这一译法,释译为“主簿”,以为是这一汉语职官的对音;她认为在鄯善国王治下的精绝,是以王土(raja)、封地(kilme,封邑)、聚落(avana)这几种形式存在的。由于cojhbo这个关键职官译法的改变,因此相应的,“州”的译法也被否定了。这个问题涉及了精绝的政治体制和行政区性质。
文书中提及的地名或部落名称,包括一些行政区或封邑名,数量也很多,大致有五十种以上。这些地名中,包括一些被称作“阿瓦纳”(avana)的行政区,如Ajiyama aύana(阿迟耶摩阿瓦纳)、Catisa deviyae avana(晢蒂女神阿瓦纳)、deviyae naύaka avana(王后之新阿瓦纳)、Deviyae Ogu Anuǵaya ni aύana(王后奥古阿奴迦耶阿瓦纳)、Deviae Peta aύana(王后毗陀阿瓦纳)、Paǵina avana(帕耆那阿瓦纳)、Peta avana(毗陀阿瓦纳)、Navaǵa aύana(那伐迦阿瓦纳)、Trasa avana(特罗沙阿瓦纳)、Vaṃtu avana(梵图阿瓦纳)、Yaύe avana(叶吠阿瓦纳)、Yiruṃḍhina avana(夷龙提那阿瓦纳)。对于avana,巴罗在《译文集》里有时意译作“村”,而林梅村则意译为“县”,段晴则译作“聚落”。因为鄯善王国的这个主要行政区,涉及其当时的行政体制和语源等目前尚不确定的问题,所以我决定沿用孟凡人先生的音译法(“阿瓦纳”)。
一些地名或部落名称,显然可以比对为汉文史书中所记载的西域地名或部落名称,如Calmadana(且末)、Khotaṃna(于阗)、Khema(扜弥)、Kroraina(楼兰)、Kuci(龟兹)、Khvani(扜泥)、Nina(尼壤)、Suliǵa(速利,粟特)、Supi(苏毗);但是,文书中也提及了鄯善王城扜泥的一个别称:mahaṃtanagara(摩诃那揭罗,大城)。但大部分地名都无法与史书比对,也无法确知其方位。其中也有富于意义的地名,如Bhoti(菩提)、Bhoti-nagara(菩提城)。
文书中也出现了若干王的尊号,如天子(devaputrasa)、王中之王(rayatirayasa)、于阗大王(Khotana maharaya)、天神(Deva)等,以及意义不明的为于阗王尉迟信诃(Vijitasiṃha)所享有的Hinaza(第661号)。此外是若干度量衡单位或价值单位的名称,包括diṣṭi、khi、milima、vacari、muli(价值单位);还有两种金币名称trakhma(德拉克马)和satera(斯塔尔)。它们的语源显然是多方面的。
对于每件文书里出现的专有名词,我在翻译时都依据《佉卢文题铭》,用括号列出了其拉丁文的转写。其目的是使研究者便于核对。所有这些专有名词在各件文书里的出现情况,读者可以对照我在附录二里所做的“词汇索引”。
对于理解新疆佉卢文书来讲,理解其类型和格式特征是基础。过去,我在学习这些佉卢文书时,曾经尝试在前人基础上再做分类。由于该时期中国内地早已进入纸张书写的时代,位处西陲的尼雅(精绝)等佉卢文书就具有了一种书写体系的研究意义。这些佉卢文书体现出了类型的多样性,较于阗语文书更为复杂。由于在文书形制与内容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几种主要类型的文书所具有的格式化特征,因而也反映出那时鄯善在行政和文化方面的成就。根据内容可以把全部文书分作国王谕令、籍账、信函、法律文书(判决书)、社会经济文书(书面契约)、佛教文献、文学作品、杂类等八类。国王谕令、法律文书(判决书)、社会经济文书(书面契约)、信函采用了保密的封检式双牍形制,而斯坦因所发现的25件皮革文书则专门用于书写国王的谕令,也采用了封泥印封方式。籍账则通常采用长方形木牍形式来书写。一篇佛教文献《浴佛节斋祷文》(拟题,第511号)和一篇《十二属星占文》(拟题,第565号),则书于长方形牍上。最具格式特征的文书之一,是封检式楔形双牍的国王谕令,通过保存完好的文书实例,其固定格式是:封牍(cover-tablet)正面:收件人职衔、名字;底牍(under-tablet)正面+封牍背面:正文;底牍背面:文书关键词。虽然巴罗的《译文集》未尝顾及这一方面问题,但是我们结合《佉卢文题铭》的完整转写,是可以复原的。
另一种格式文书的书面契约,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西域早期契约法以及法律—社会经济文书的悠久传统。其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在翻译时我很想对每件文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考释,内容包括该件之原始编号(遗址出土号)、释译情况、有关词语或语句及所涉问题的考证,以及一些曾由林梅村教授和王广智先生翻译过的文书与本译差异之比勘,诸如此类。然而这样一来,本著可能就不再是一部译注了。我相信将来会有感兴趣的人来完成这个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许由我本人来做也说不定。无论如何,它将是件有意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