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荣新江︱东国有高士 敦煌结胜缘——纪念池田温先生

池田温先生
2023年12月11日,日本著名史学家、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辞世,享年92岁。池田先生走完他丰满的学术人生,留给我们一本本传世名著,也留下许多促进中日敦煌学界亲密交往的感人事迹。我有幸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池田先生,承蒙他多方关照,所以这些天来和他交往的事情像电影一样一遍遍在脑子里播映,今日略作条理,写下来,以作纪念。
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选修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开设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就不断听闻“池田温”的大名。当时王先生给我们上课,总是拿着那本厚厚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封面上作者的名字赫然在目,而这本书中的计帐、户籍、差科簿及各种相关文书,是老师们为我们解读分析的主要素材。池田先生严谨的录文让我感触良多,其中有关归义军时期的《布纸破用历》《沙州百姓万人上回鹘可汗书》《押衙王文通牒》等,也是我后来研究归义军史时不断翻阅、引用的文献。但这本书当时北大只有一本,很难借到。当我1984年研究生阶段去荷兰莱顿大学进修时,兜里有了一点外币,我就从莱顿鲁莽地给池田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您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是非卖品,我现在有了外汇,想从他那边购买一本。结果很快接到他的回信,说他手边还有几本,可以送我,是寄到莱顿,还是北京。我大喜过望,赶忙回信,请他直接寄到北京,等1985年7月初我回京后,这本厚重的大书已经等在那里了。这是池田温先生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一份大礼,我迄今上课时还常常用到这本书,后来我组织课题组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也以这本大著校录的文书做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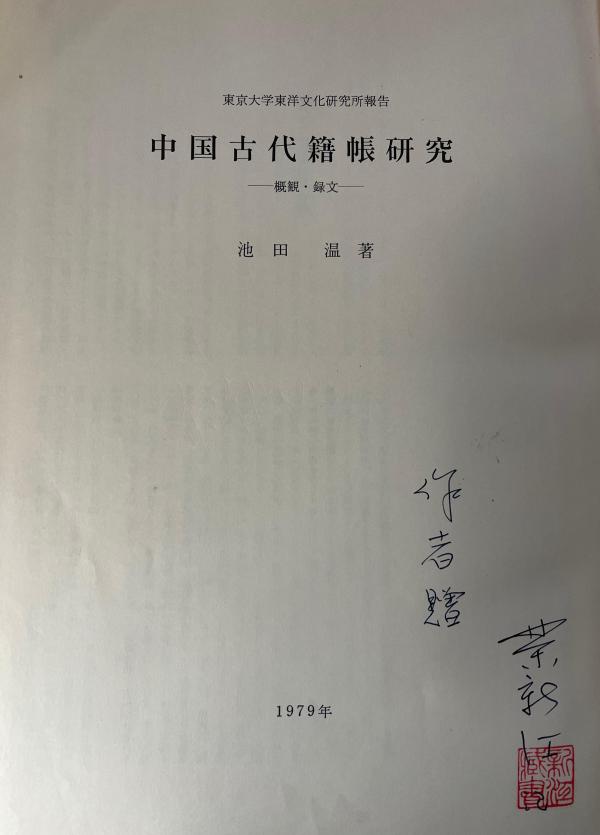
就在1985年7月我回国后不久,池田温先生到访北京,好像是参加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乌鲁木齐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之后,于9月16-24日之间,借回国途中顺路来访。当时周一良先生带着我,特意到北京机场去接他,可见规格之高。周先生的日语十分流利,他为尊重客人起见,用日语和池田先生讲话,但回过来的都是汉语。池田先生的汉语远没有周先生的日语流利,但他坚持用汉语说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心里不由得起敬。池田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场讲演,讲他指导自己的学生大津透拼接大谷文书一百余碎片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的初步结果,给我们展示了整理文书的一项“吉尼斯纪录”,更重要的是通过拼接后的文书,揭示出原本不知的许多唐代财政预算方面的内涵。此外,池田先生还和历史系师生座谈,报告有关苏联、英国、日本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最近刊布和研究情况,并就唐代田制问题做了讨论。
池田先生在京期间,历史系研究日本史的夏应元老师和我的导师张广达老师一起,凑钱请他吃了一席宴,我有幸作陪。现在还记得池田先生说他三十多岁才第一次出国,你二十多岁就出国了,大有前途。可见他对一位异国年轻学子多所鼓励,也为我后来继续“满世界寻找敦煌”增强了信心。我不揣冒昧,曾写了一篇《池田温教授谈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现状》,还附了《池田温教授主要论著目录》,我虽然尽力收集,但缺漏不少,曾寄给池田先生补充,他一一补正,并建议不收书评和讲演稿,计84条。此文收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这是我学习池田温先生学问的一份作业,也是我对池田先生的一个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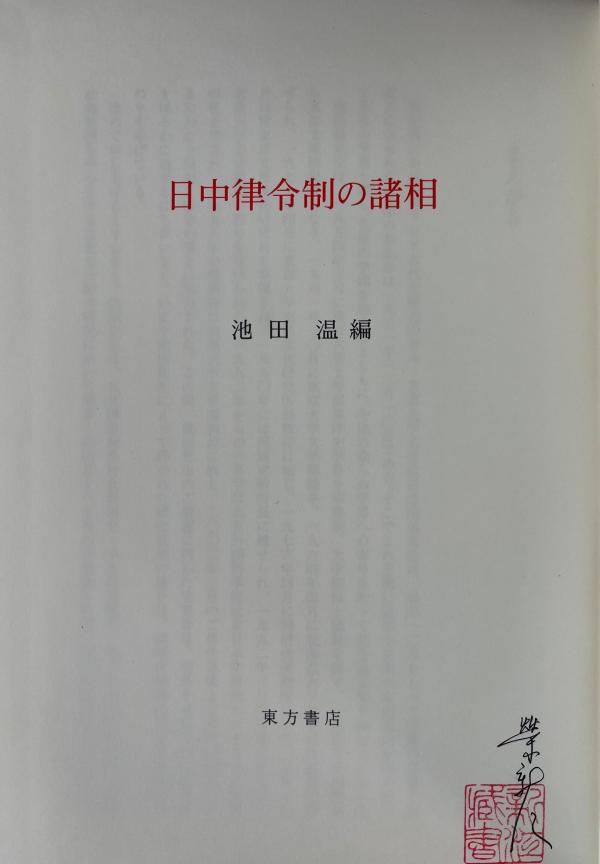
到了1988年8月,北京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会前季羡林会长就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消除了日本学者的顾虑,所以这次会议迎来了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和东京大学的池田温教授两位日本最著名的敦煌学家,使会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时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为了配合这次会议,特意在文津街图书馆的主楼内办了一个“敦煌文书展览”,陈列了一些《敦煌劫余录》编号之外的未刊文书,其中有一件《开元新格户部》残卷(周字69)引起池田温先生的注意。他会后特意到善本部,仔细观察了这件文书的正背面内容,回国后即写成《唐朝开元后期土地政策之一考察》,整理发表了这一重要文献,这是在他和山本达郎、冈野诚两位合作整理敦煌吐鲁番本律令格式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资料集》第一集之后的重要发现。我当时在帮学会跑腿,但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关照藤枝晃先生,所以池田温先生这边没有太多的接触,但看到他在展柜前抄录文书的身影,还是颇为感慨。
1990年8月底,我终于有机会访问日本,应百济康义教授邀请,在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做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这使得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池田温先生。记得我刚到京都不久的9月中旬,由京都大学文学部砺波护教授帮助联络,我有机会随藤枝晃、砺波护教授走访藤井有邻馆,这事确定后,我就通知了陈国灿先生,他从东京赶来,我们一起前往有邻馆。那天早上我们刚到有邻馆门口,就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走来,果然是一大早从东京乘新干线赶来的池田温先生。我们一起观看了有邻馆藏的长行马文书,并且听到藤枝、池田两位教授关于真伪的讨论,收获很多。下午,池田先生与砺波先生带陈国灿先生和我一起去游览平安神宫,池田先生招待大家吃茶点,送我一盒礼品果子,就赶往车站,乘新干线回东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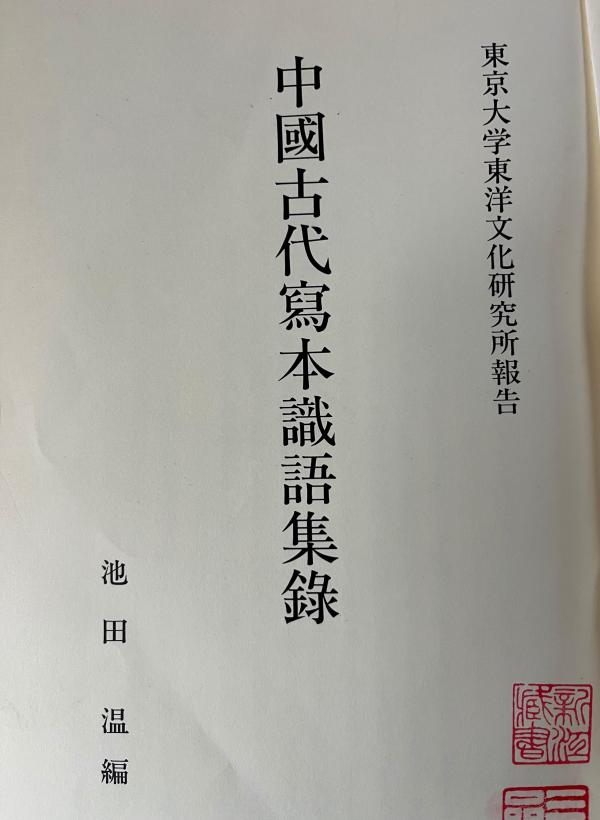
11月3日是每年京都大学举办东洋史大会的时间,池田温先生也照例来参加,记得当年做大会发言的有他的弟子大津透,不知是否他因此而来。中午时分,我跟随池田先生和龙谷大学的木田知生先生到京大对面的百万遍逛古书市。晚上他在一家高档的法国餐馆请我吃饭,新潟大学的关尾史郎、龙谷大学的北村高两位同席,他对我在京都的学习、研究、生活倍加关怀,我也乘机请他安排11月下旬走访东京,他满口答应。回东京之后,他就委托跟随他进修的关尾史郎帮我在新大久保订了一个旅馆,交通很方便,房费我也承担得起。
我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11月19日启程去东京。安顿好住处后,下午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池田先生那里报了个到,并大致讲了一下自己在东京考察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访书等方面的安排,他在百忙中帮我联系相关单位,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还让关尾史郎带我去静嘉堂文库。
11月25日下午,池田温先生专门抽出时间,陪我一个人活动。记得他带着我穿街走巷,穿过一段他说是情人旅馆的地方,来到破旧的书道博物馆。没想到在敦煌吐鲁番学界赫赫有名的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竟然如此败落,里面蚊蝇飞舞,陈列品大多数也常年没有更换。据池田先生讲,敦煌吐鲁番文献每年换五件,所以他每年都来参观一次。我赶忙抄录了陈列的五件写经题记,做了大致的记录,又走了一圈,浏览其他藏品。这里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私家经营不善,所以显得十分凌乱。池田先生说他也没有进过库房看其他敦煌吐鲁番文献,有些年轻学者甚至说可能有些文书已经出售,但学术界还是有一些与馆方关系密切的人,发表了一些回鹘文文书,让大家抱以希望。

1990年11月,作者与池田温先生在京都
从书道博物馆出来后,就乘车前往神保町书店街。池田先生先带我去一家旧书店,各种花里胡哨的书陈列在台子上,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绢の路》,说没有什么可买的书。从第二家开始,他带我走的都是学术书店了,包括东方书店、内山书店、南海堂、一诚堂、山口书店等等。我初来乍到,还是以观察为主,没有过多地购买,但这里有很多我十分想买的专业书籍。
到了晚上,池田先生带我到繁华的池袋,在小田急站大至满餐馆,与他夫人会合,原来他让夫人早早来这里排队,因为这家餐馆的一味汤很有名,可惜我现在忘记了名称。池田先生特别选择这家名店来举行欢迎我来东京的宴会,记得出席者有东大的熊本裕、早稻田大学的荒川正晴,以及关尾史郎三位,我为池田先生对我这样的年轻人的招待深深感动。
随后几天,我走访了国立国会图书馆,看了馆藏从滨田德海氏购买的部分敦煌文献;随关尾史郎参观静嘉堂文库藏宋版书,无意间阅览了八册梁素文旧藏的吐鲁番文书;又去了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大谷探险队所获和田、库车等地出土文物,还找到罗振玉旧藏的《刘子》残卷;可谓收获多多。
我来日本前刚刚获得霍英东基金奖,所有手里有不少购书经费,于是我就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请池田先生帮忙联系东大出版会、大东出版社、汲古书院、刀水书房等出版社,打算购买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已出的《讲座敦煌》、唐代史研究会报告集等有关敦煌吐鲁番和唐史研究方面的书。过了几天,池田先生把自己能够找到的一批副本书全都给了我,其他则联系打折购买,让我省了不少经费,其高情厚谊,至今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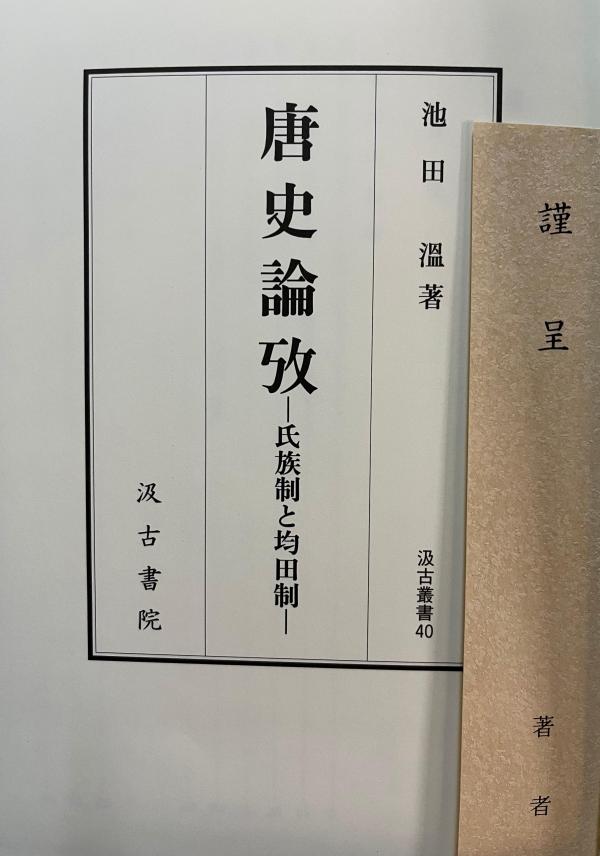
首次到东京,池田温先生还安排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做一次讲演,我事先考虑再三,打算用日本学者还不知道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籍》残卷为题,把这三个残片缀合而成的户籍介绍给日本学界。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其实也是给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和1984-1985年东洋文库出版的山本达郎与土肥义和两位先生共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第二卷《户籍编》捡漏。池田先生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当天还请来了日本学士院院士山本达郎先生来听我的讲座,让我感到十分荣幸。回国后,我从史树青先生重刊的《艺林旬刊》第29期(1928年)和第55期(1929年)上,发现了后分藏于北大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的四片同一户籍的照片,确定这是一件《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并撰写了正式的研究论文,发表在《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为了感谢池田温先生的帮助,我从琉璃厂专门购买了一册《艺林旬刊》合订重印本,送给池田温先生,虽然价格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菲,但池田先生送我的书更多。把这册《艺林旬刊》赠送给池田先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此前他在写《高昌三碑略考》时,曾托张广达先生到北大图书馆查阅原版《艺林旬刊》中发表的《且渠安周造祠功德碑》和《高昌主客长史碑》照片,当时张先生让我去图书馆抄录照片旁周肈祥的跋语,这本大开本的画报不易保存,不仅不能复制、拍照,而且只能由馆员翻到你要看的那页,其他不允许翻阅。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这里面会有《开元二十九年籍》,现在把这个礼物送给池田先生,在高昌碑刻和唐代户籍两个方面,都可以供他参考使用。后来2001年山本达郎等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的《补编》时,根据我的文章收录了这件《开元二十九年西州籍》,我想当年在东京大学的讲演还是有结果的。
我走访东京的时候,正好赶上池田温先生的另一本大著《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出版,他送了我一本,成为我后来寻访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等工作的重要参考书。此后池田先生每出一书,不论是自己写的,还是他主编的,都会送我,这包括《敦煌的汉文文献》(1992年)、《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1992年)、《唐与日本》(1992年)、《中国史》2《三国—唐》(1996年)、《唐令拾遗补》(1997年)、《東亚文化交流史》(2002年)、《日中律令制的諸相》(2002年)、《(以学习日本古代史为目的的)汉文入门》(2006年)、《敦煌文书的世界》(2003年)等,直到2014年由大津透整理的《唐史论丛——氏族制与均田制》出版,他也特别寄赠给我一册。这些书在我研究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日关系史方面都给予了很多学养,有些内容也通过我传达给我的学生或国内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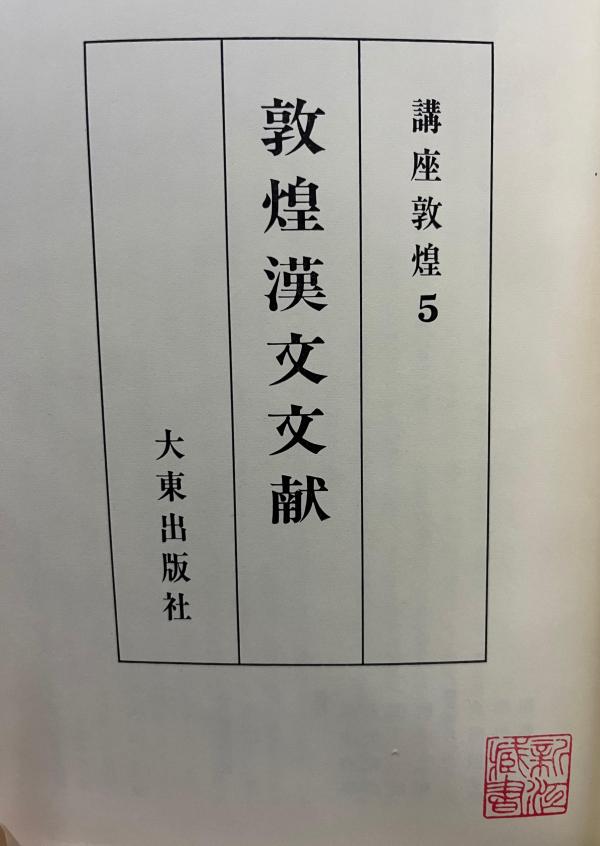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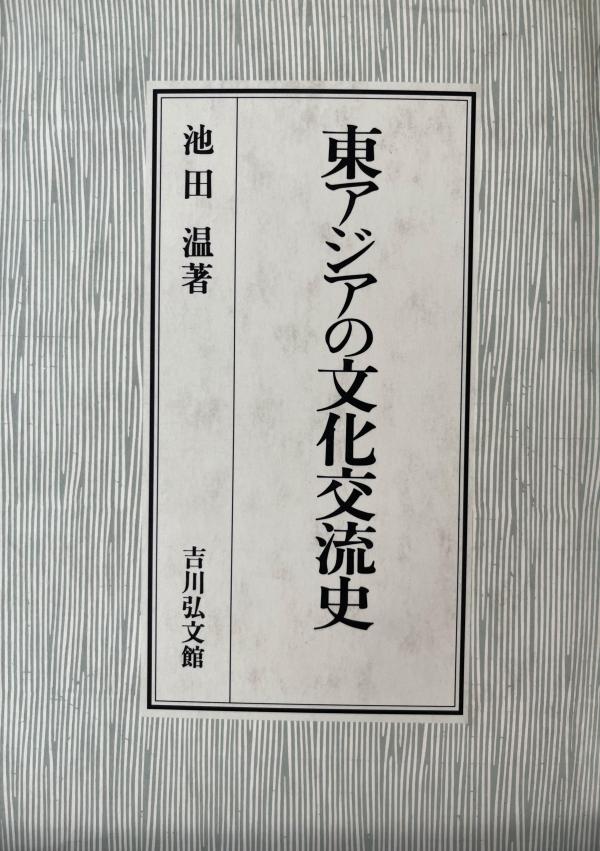
1995年以后我是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唐研究》主编,我与孙晓林女史一起,极力推动编译了一部池田温先生的《唐研究论文选集》,得到唐研究基金会资助,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收集了池田先生有关唐史研究的许多经典论文,相信对中国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也利用《唐研究》的新书目,及时发表池田先生论著的消息;还约请相关学者,给他的新著撰写书评。我本人则接受香港大学黄约瑟先生的约请,为他主编的《东方文化》撰写了池田温编《敦煌汉文文献》的书评,刊于《东方文化》第XXXI卷第1期(1993年)。书评系我一贯的风格,有表彰,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发表后寄给池田温先生,一直忐忑不安,后来听说池田先生把我的书评复印若干份,分送给该书每一位作者,我略有安慰。由此也可以看出池田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有气量的大家。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也是敦煌学研究一百年纪念的时间点,各国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我收到日本东方学会的邀请,在5月东京日本东方学会第42届东方学者会议主会场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分会场里做主旨发表。这次东方学会的邀请规格很高,要给我买全日空的头等舱,我和具体接待我的大阪大学荒川正晴教授商量,能不能买个经济舱的票,剩下来的钱我在东京买书。他说不行,这次接待是东方学会评议员们定的调,不能降格。我只好听从安排,但我当时不知道是谁在后面安排的这件事情。我对此行做了充分准备,5月19日当天,会场坐满了人,我以“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为题做了讲演,我讲演的主持人是荒川正晴教授,池田温先生评议,他当着一众日本老中青敦煌学研究者说:“今天我们请来的讲演者,虽然只有40岁,但却是国际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在中日敦煌学界有个传说,即1981年藤枝晃教授到南开大学讲学,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引起很多中国学者的不满。虽然后来在场的学者说这是介绍藤枝晃的南开教授讲的,但中国学者仍然把这话当作藤枝讲的,后来藤枝也无可奈何地说这就是他讲的吧。其实这背后有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敦煌学中心上的较劲,双方都有一些人利用这个话题来炒作。池田温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却做这样一种表态,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也十分感动。但这也无疑引起一些日本敦煌学研究者的不愉快,所以我随后也经历了几次挑战和博弈。池田先生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由此可见一斑。
上午会议结束后,老同学李开元约我一起去吃午饭,但我被工作人员截住,她引导我到一个大房间里吃东方学会准备的便当。我巡视一周,有荒川教授事先带我拜见过的东方学会的领导人:理事长服部正明、事务局长柳濑广、交流主任河口英雄,此外我能认识的就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池田温和砺波护两位先生了。这下我才明白,我这次受邀来东方学会做主旨讲演,应当是池田和砺波两位先生推荐的,而获得东方学会评议员们的同意。
回国后,我收到东方学会寄来的《东方学会报》,上面刊载了池田温介绍我的文字,其实这是我在敦煌学领域“为国争光”的原始记录,但做敦煌学史的人一般不会看到。我的发言摘要按照东方学会的要求,以英文“More on the Nature of the Tun-huang Treasures: Three Stages Monastery and the Library Cave”,发表在东方学会编的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第XLV号(2000)。这个事情讲起来有点自吹自擂,我只是在喝酒的饭桌上和一些朋友说到过,但这件事可以看出,池田温、砺波护等先生对我此前学术研究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中国敦煌学所取得的成绩的肯定,是以国际视野破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说法的努力,与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是具有同样宏大胸怀的做法。

1992年,他从东京大学退休,先是在北京的日本学研究中心任主任一年。1993年接受创价大学的非常勤教师的职位,每周到距离东京不近的八王子市去上课,尽心尽力帮助创价大学的东洋史和丝绸之路的研究,这一阶段他主要兴趣在唐令的订补和新出《天圣令》的研究,我不断蒙他赠送有关唐令的新作。
后来我去日本的机会多了,每次过东京,方便的话都会去拜访池田先生。2006年3月,我应关尾史郎教授邀请,到新潟参加他主办的“絲綢之路的文化与交流——吐魯番文物的世界”学术研讨会。会后前往东京,特意去已经转归东京都台东区所属的书道博物馆,参观“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古写经”展。池田温先生不知从哪里得到我来这里参观的消息,事先和馆方讲过,所以该馆研究员锅岛稻子特别来关照,并赠送《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图录》。这个特展一共陈列了25件敦煌吐鲁番资料,比以前随池田先生来看的多得多,赶紧抄题记和跋文。当天下午,我在东洋文库“內陆亚洲出土古文献研究会”发表讲演,题目是《近年来新出吐鲁番文献简介》,土肥义和先生主持,关尾介绍我的情况,张娜丽翻译,池田温先生也特别赶来参加,并赠送给我一册《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池田先生处理事情非常之细,于此可见一斑,我也想学习他的做法,但一直也没有学到家。
2007年1-3月,我受妹尾达彦教授邀请访问中央大学和东洋文库。年初一到东京,我就找机会到八王子市创价大学文学部,拜访池田温先生,赠送给他《唐研究》第12卷,其中有他关心的《天圣令》研究的一组文章,都是整理《天圣令》的社科院历史所同仁所写,他拿到十分高兴。这个月底,池田先生从创价大学退休,很少出门。但3月初我受邀在东洋文库做“丝绸之路的新出文书——吐鲁番新发现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讲演,文库长斯波义信先生主持讲演,土肥义和先生主持讨论,很少露面的池田先生突然来到会场,让众人也吃了一惊,而我感到了池田先生对我关怀的温暖。
后来听说他有点老年痴呆,所以家人不让出门。我曾在2017年走访京都和东京,想利用这次机会与砺波护和池田温先生见面。在京都通过高田时雄教授的帮助,约到了砺波护先生。他从宇治过来,比我们俩早到一步,我望见他慢慢行走的步履,颇为感动。我们三人一起在京都四条的河边餐馆,畅谈了一晚,然后依依惜别。到东京后,我请大津透教授约池田温先生,结果家人不放心,说现在不太认得人,怕客人失望,所以没有让他出来,我感到非常遗憾,祈愿他健康长寿。
现在,池田温先生走了,国际敦煌学界失去了一位权威学者,中日学界之间少了一座牢固的桥梁。
2023年12月23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