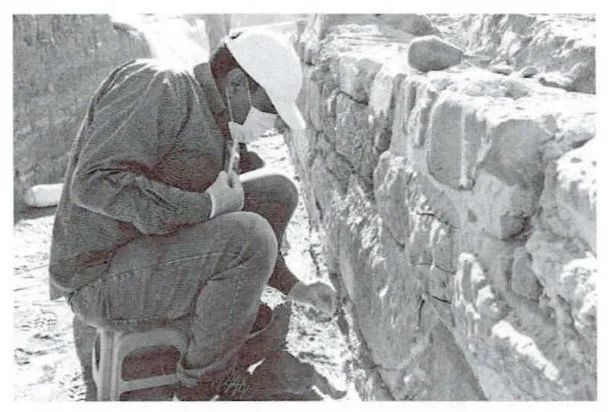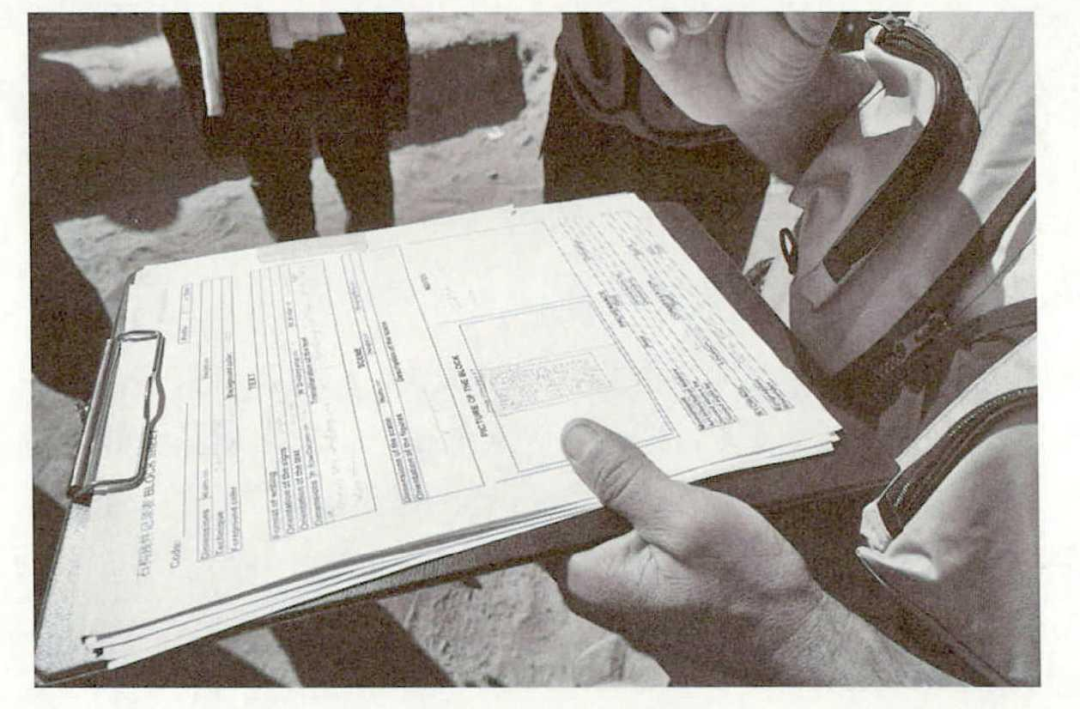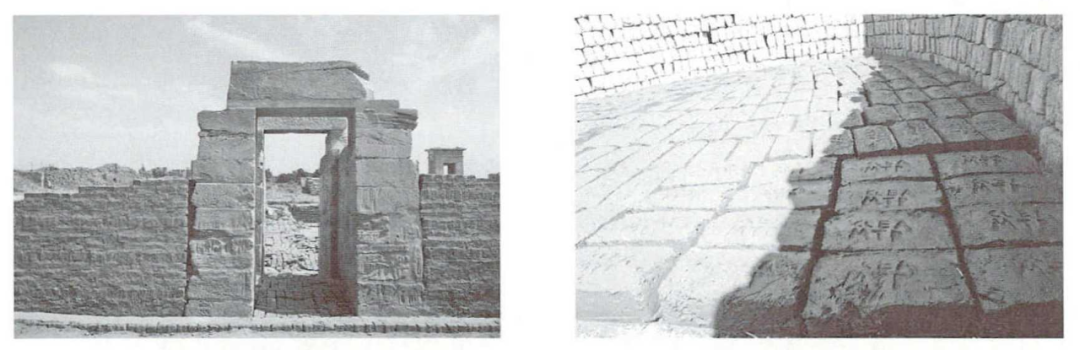[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埃及考古专题十三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4-35.
[2]Mariette A. Karnak, étude topographique et archéologique[M]. Leipzig:J. C. Hinriches, 1875.
[3]Legrain G. Notice sur le temple d'Osiris Neb-Djeto[J].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1904(4):181-184.
[4]Pillet M. Rapport sur les travaux de Karnak(1923-1924)[J).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1924(24):84-86.
[5]Varille A. Karnak I[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3.
[6]a. Robichon C, Christophe L. Karnak-Nord III(1945-1949)[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51.
b. Robichon C, Barguet P, Leclant J. Karnak-Nord IV(1949-1951)[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54.
[7]Jacquet J. Karnak-Nord V,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83.
[8]a. Jacquet J. Karnak-Nord V.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83.
b. Jacquet-Gordon H. Karnak-Nord VI.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 La décoration[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88.
c. Jacquet J. Karnak-Nord VII.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 Installations antérieures ou postérieures au monument[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94.
d. Jacquet-Gordon H. Karnak-Nord VIII.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 Statues, Stèles et blocs réutilisés[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99.
e. Jacquet J. Karnak-Nord IX[M]. 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2001.
f. Jacquet-Gordon H. Karnak-Nord X.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er. La céramique[M]. Cairo:IFAO, 2012.
[9]Gabolde L, Rondot V. Le Temple de Montou n'était pas un temple à Montou(Karnak-Nord 1990. 1996)[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égyptologie, 1996(136):27-41.
[10]Ashton S-A. Karnak-Nord[C]. Travaux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2008-2009.2009:576-583.
[11]Masson E.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a dégradation des grès de Karnak[J]. Revue d'Archéométrie, 1985(9):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