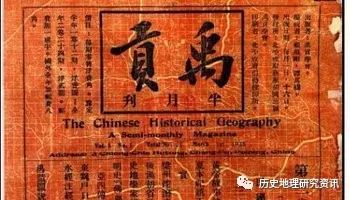研究前沿
学术研究|近20年来两汉西域治理问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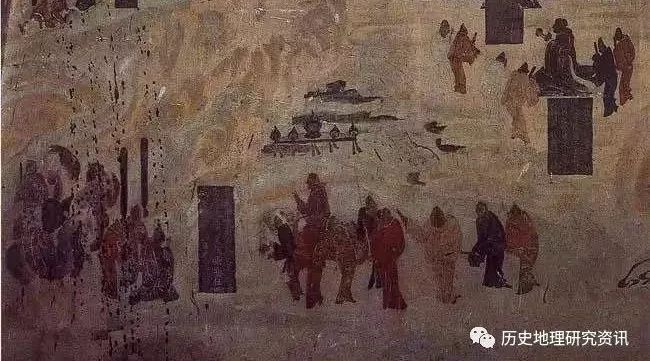
西汉以来,“西域”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使用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以至于更远的中亚地区。狭义的西域则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南北,葱岭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本文所讨论的西域,即为狭义之西域。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西汉王朝积极经略西域,到汉宣帝时期,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并将其作为汉朝管理西域地区事务的行政机构,从此西域正式被纳入西汉的版图。至新莽时期,由于王莽采取了“贬抑侯王”等错误民族政策,导致西域怨叛,遂与中原断绝了来往,匈奴势力再次控制了西域。东汉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朝廷对西域的重视程度不及西汉,加之西北羌乱迭起,对偏远西域地区的控制远不及西汉,以致出现“三绝三通”的动荡局面。两汉在西域地区的行政建制,可谓开历代之先,不仅在两汉西域史和边疆经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对当今处理民族与边疆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对两汉西域史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西域考古、中西交通与民族关系等主题,对两汉西域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尚未能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前辈学者,如王国维、曾问吾、张星烺、冯承钧、黄文弼以及日本汉学家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羽田亨等均对古代西域问题有过细致的研究,但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多停留在史料的搜集和细节的考证,在理论构建和系统论述方面尚有可议之处。而一些西方学者,如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等,更是直接将其作为中亚史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所得结论自然也与史实有所出入。20世纪中叶以来出版的汉代西域史研究专著,如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岩南堂,1968年)、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食货出版社,1977年)、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邵台新《汉代对西域的经营》(辅仁大学出版社,1984年)、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侯丕勋《历代经略西北边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等,对西域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有所涉及,但却没有系统的论述。就此而论,加强和推进汉代西域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学术探索。近20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不少成果,笔者谨就此间汉代西域治理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述评。
一、两汉王朝西域治理理论与策略。作为两汉边疆与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王朝之于西域的治理策略,是随着两汉的边疆和民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齐清顺和田卫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专著对此均有所涉及。至于论文方面,有的学者在宏观上论述了两汉民族国家边疆思想,如黎小龙、徐难于《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从宏观上探讨了包括西域在内的汉代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有的学者则专门对汉代经营西域的策略和民族政策进行了探讨,其中,侯晓星《略论西汉武昭宣时期的西域民族政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06年)对西汉武昭宣时期西域民族政策的变迁作了系统的论述。马智全《论汉简所见汉代西域归义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4期)整理了20世纪西北出土的汉简中一些关于汉代西域大月氏、乌孙、车师等地民众“归义”现象的记载。胡岩涛等《论汉武昭宣时期的西域羁縻策略》(《新疆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分析了汉武昭宣时期在西域地区实施的羁縻策略,认为其对西域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贾文丽《对东汉时期张珰经营西域之“三策”及相关史实的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认为敦煌太守张珰上书“三策”为汉朝政府正确决策及时提供可行方案,阻止了西域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崔明德《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则系统地考察了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两汉某些帝王在西域的民族与边疆政策的研究,如陈立柱《王莽与周边民族关系新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崔明德《王莽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东岳论丛》2007年第3期)、张安福《汉武帝经略西域的策略研究》(《史林》2009年第6期)等均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
二、王朝对西域的行政管理。两汉于西域设立的军政机构,其核心是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直接由中央任命,行政级别略与内地郡太守相当。西域都护之建号与都护府之设立,是西域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因而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自20世纪中叶起,学界对西域都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间发表的著作有安作璋《西域都护的建置及其作用》(收入安作璋《汉史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卢苇《论两汉西域都护府》(《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贾应逸《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新疆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张维华《西汉都护通考》(《汉史论集》)、刘锡淦《关于西域都护与僮仆都尉问题的质疑》(《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刘洪波《关于西域都护的始置时间》(《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李大龙《西汉西域都护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以及日本学者高桥融《西域都护创设の一考察》(《东洋史苑》第1卷,1968年)等均为研究西域都护问题的代表论著。
2000年以来,对于西域都护的研究热度虽不似从前,但仍旧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对西域都护的始置年代及其职责、职称等方面的研究,如洪涛《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其历史地位》(《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论述了汉代西域都护建立的背景、职权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孟辽阔《西汉中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及其重要意义》(《宁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指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随着敦煌悬泉汉简尤其是其中部分西域简的公布,学者又开始利用简牍资料来考证一些依靠传世文献难以解决的问题。刘国防《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将西域都护最初设置的时间定为地节二年。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综合文献资料和新近出土汉简,指出地节、元康年间,汉廷已默认都护一职的存在。李炳泉《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对西域都护的称谓和建置时间问题作了探讨;他的《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则利用悬泉汉简材料,对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史实进行了考证。谢彦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晋阳学刊》2007年第1期)和《西汉中垒校尉职掌考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两文从文献入手,肯定了李炳泉对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考证,并就相关问题进一步分析与阐述。
戊己校尉是汉元帝时期设置的重要职官,秩比二千石,与都护相拟。关于其命名、性质、职能、属官以及隶属关系等问题的探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考察了戊己校尉的职数情况与隶属关系。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利用新出汉简指出戊己校尉隶属于中央北军而非敦煌郡。赵贞《汉代戊己校尉阐释》(《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认为戊己校尉代表中央行使汉王朝对西域的管理权,其主要职能是屯田。高荣《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戊己校尉之设起于车师屯田,故其职以屯田为先。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高昌戊己校尉研究系列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探讨了戊己校尉的建置,认为戊己校尉具有“寄居治理”的性质;他的《高昌戊己校尉的组织——高昌戊己校尉研究系列之二》(《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则又对戊己校尉的设置员数和组织结构进行详细的研究。
此外,马智全《戊己校尉的设立及其属吏秩次论考》(《丝绸之路》2012年第6期)、贾丛江《西汉戊己校尉的名和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等也对戊己校尉的命名、性质、职能、秩禄、属官以及隶属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也对两汉设置于西域的其他官职作了探讨。李炳泉《两汉“西域副校尉”略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系统地考证了两汉西域副校尉建置问题。申超《汉代西域长史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1期)通过对比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西域长史的建置始于汉代,原为西域都护的属官,后来才发展成为独立的官僚机构,代行西域都护之职权。薛宗正《西汉的使者校尉与屯田校尉》(《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系统探讨了西汉使者校尉与屯田校尉的职责与隶属关系,并认为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脱胎于使者校尉与屯田校尉。贾丛江《西汉伊循职官考疑》(《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认为西汉所设伊循都尉属于敦煌郡的部都尉。此外,俄琼卓玛《汉代西域译长》(《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对汉朝西域都护所属诸城邦中设置的译长作了研究。
三、西域屯田与边疆开发。屯田西域,是两汉管理和经营西域的重要手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对两汉在西域屯田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彭慧敏《两汉在西域屯田论述》(《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主要论述了两汉王朝在西域屯田的原因及屯田的区域分布。施丁《汉代轮台屯田的上限问题》(《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通过对《史记》与《汉书》有关汉代轮台屯田的记载,指出汉代屯田仑头(轮台)的上限是在天汉年间。
随着大量考古资料尤其是汉简的出土,一些学者开始运用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来论述西域的屯田问题。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利用新出土的悬泉汉简,论述了西域屯田的总体面貌,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张运德《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亦从屯垦戍边的源流、目的以及文化价值三个方面揭示了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
与以上对两汉西域屯田的宏观研究不同,一些学者则详细考证了西域某一具体地区的屯田问题。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和《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两文运用传世文献并结合敦煌悬泉简资料,对西汉西域渠犁、伊循屯田组织和管理系统进行了探讨。刘国防《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考证了比胥鞬屯田的地望与规模,并指出该地屯田最终被戊己校尉所整合。侯灿《楼兰研究析疑——楼兰问题驳难之二》(《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利用考古发掘资料考证出两汉王朝的屯戍重地楼兰城,即为西汉元凤四年前楼兰王国的都城。梁安和《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开发》(《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认为西汉朝廷在西域屯田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及把新疆地区纳入我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四、中原与西域的多元化交流。1.政治互动。两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互动,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刘春雨《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认为西域使者派遣的主体多样性特点,证明了汉朝在西域实施了成功的民族政策,反映了西域与内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沟通交流程度的加深。
由于汉与乌孙之间的关系在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早在20世纪40年代,手冢隆义《乌孙の国内事情と西域都护の成立》(《史苑》第14卷第1号,1941年)就对汉与乌孙的关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大河内隆《前汉の西域进出と乌孙の动向——汉の乌孙支配に关连して》(《史丛》第26卷,1980年)也对西汉时期的乌孙问题进行了探讨。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与西汉和乌孙关系有关的敦煌悬泉汉简“长罗侯费用簿”的公布,一些学者们就其年代、性质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张德芳《〈长罗侯费用薄〉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就《费用薄》所反映的内容进行了考证,并结合悬泉出土王莽简所反映的史实,理清了汉与乌孙的关系状况。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和《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利用新出土的悬泉汉简,着重探讨了乌孙历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石少颖《乌孙归汉与西汉外交》(《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梳理了西汉、匈奴与乌孙三者之间微妙的外交关系。何海龙《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求索》2006年第3期)也根据悬泉汉简中几条有关乌孙的史料,结合《汉书》的相关记载,对西汉与乌孙交往关系进行梳理。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4号,兰台出版社,2002年)结合汉简材料,考证了长罗侯常惠在西域的活动以及汉与乌孙的关系;他的《汉与楼兰(鄯善)车师(师姑)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4号)不仅考述了汉与楼兰(鄯善)、车师的关系,而且还就戊己校尉及其属吏构成等问题作了探讨。
随着敦煌悬泉简相关资料的公布,两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关系也日益受到关注。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论述了西汉时期楼兰(鄯善)与汉朝的关系。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结合悬泉汉简的记载,考察了西汉宣元成时期康居与汉王朝的关系。利用悬泉汉简研究两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关系的还有张德芳《悬泉汉简和西域诸国》(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王旺祥《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1期)、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等。
对两汉通西域人物的研究,仍旧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李炳泉《甘延寿任西域使职年代考——兼及冯嫽在册封乌孙两昆弥事件中的活动》(《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运用《汉书·西域传》及目前所见悬泉汉简中的有关史料,对《汉书·甘延寿传》进行补充和考证。郝树声《浅论李广利伐大宛的功过是非》(《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阐述了李广利伐大宛的动机、经过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刘光华《关于西汉郅支城之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对西汉郅支城之战的原因、过程及重要意义进行了考证,肯定了陈汤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将《汉书》中的“北胥鞬”考证为“比胥鞬”,并指出郑吉封侯的时间不会早于神爵元年。王欣《常惠综论》(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高度评价了常惠对西域的贡献。张德芳《郑吉“数出西域”考论》(《西域研究》2011年第2期)通过对文献的排比分析,认为《汉书·郑吉传》所载郑吉“数出西域”,很可能是指他曾参加过太初元年击大宛、元凤四年刺杀楼兰王、本始二年护乌孙击匈奴等事件。
“和亲”与“纳质”也是汉代中原与西域政治互动的重要内容。王嵘《西汉和亲政策与汉文化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分析了西汉基于政治婚姻的和亲政策及其对汉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影响。葛亮《论汉代的民族“和亲”并非民族间的政治联姻——释两汉时期民族“和亲”之含义》(《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认为汉代所谓民族之间的“和亲”主旨是实现和平,与民族政治联姻性质不同。汉与西域和亲的实现,离不开细君、解忧、冯嫽三位女性人物的努力。为此,一些学者将关注点集中在这三位女性人物身上。王庆宪《匈汉争夺中活跃在西域的三位汉家公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即高度肯定了细君、解忧、冯嫽三位公主在促进中西交流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袁延胜《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结合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记载的西域史实,探讨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以及汉朝诛灭郅支单于的重要历史意义。成琳《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新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系统考察了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质侍”现象。中村桃子《前汉时代の“质子”(“侍子”)外交:汉の匈奴、西域诸国との关系を中心に》(《アジアの历史と文化》第19卷,2015年)也就西汉时期与匈奴及西域诸国的质侍问题展开了探讨。
2.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王子今、乔松林《“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认为“译人”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突出的表现,是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仓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精绝城邦当年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汉王朝统辖西域时,他们曾经以汉文作为自己的文字工具。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探讨了悬泉汉简中出现的少数民族人名问题。贾丛江《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则指出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在于西汉末年“去二名”改制措施的实施。王泽民《汉代西域屯田与汉语汉文的传播使用》(《新疆地方志》2003年第3期)认为自汉代在西域屯田始,汉语汉文开始在西域广泛传播与使用,一度成为西域的通行语言。关于汉语言文字在汉代西域传播的论文,还有高列过《从被动式看东汉西域译经者的翻译风格》(《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和廖冬梅《汉语文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与民汉双语现象》(《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中西人口交流。袁延胜《〈汉书·西域传〉户口资料系年蠡测》(《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对西域一些国家户口资料及人口状况作了分析。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的记载,全面考察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及其留居情况;他的《关于东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则在前文基础上,详尽论述了东汉时期活动于西域的汉人情况,并指出在东汉军队构成发生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其驻屯西域的汉人士卒社会身份较之于西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五、结语。综合以上诸论著,学术界对汉代西域问题的研究仍多集中于汉与西域的关系史和民族史方面,对汉代在西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则略显滞后。而且已有的著作也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鲜有研究专著出版。就目前学术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言,其中不乏一些精辟的论述,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推究。
1.学界对两汉西域地区治理理论与民族政策问题作了探讨,但对两汉中央针对西域地区民族政策的特殊性,以及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比较研究尚待推进。对西域都护的重要性探讨较多,而对其在整个西域地区的行政建置及其在汉代边疆管理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探讨较少,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2.对汉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更多是从经济开发角度探讨,而对屯田的管理体制、制度本身的运作,以及从中体现出的中央与西域地方互动关系、屯田对整个西域边防建构等问题的研究仍存有较大的讨论余地。这与西域屯田制度的重要性很不相称,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3.对西域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研究较多,尽管涉及汉王朝在西域的军事活动,但对历次战争的性质、过程以及影响等问题有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对两汉西域战争史与军事史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两汉西域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4.对一些传统问题的研究,诸如中西关系史与交通史等方面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过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是研究观点与视角略显陈旧,所用资料亦多为传世文献,对新出考古资料的应用较少,且多有一些观点相近的文章被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造成极大的浪费;二是学术界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探讨,或囿于资料不足,或囿于缺乏新角度与新解释,往往显得不够深入,更多类似于宏观性或普及性的文章,缺乏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微观性考察。可见,在今后对两汉西域史的研究中,应该在进行宏观性讨论的同时,加强对微观问题的考察;在加大使用新出资料的同时,注意发掘已有的旧材料,通过转换视角对其作出新的解释,将会成为今后两汉西域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两汉西域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问题的深化与拓展,期待研究视角的转换。两汉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实践,作为中国传统的治边实践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几乎都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边疆治理问题,尤其是秦汉时代尚处于古代的前期阶段,其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包含着诸多大胆的开拓与宝贵的创新,既奠定了中国传统治边基本方略的基础,又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以及具体的个案分析。二是两汉对西域的治理实践,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是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探索方才逐步形成的,不仅对当时的边疆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处理诸多边疆问题亦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学术界至今对我国古代的治边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民族轻边疆的倾向,具体到对两汉西域治理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因此,汉代西域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或许可以作为两汉西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加以深入探讨。
作者介绍:
李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信息来源: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第14-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