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

近代科学范畴内的中国考古学有了70多年的历史,经过三四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对各古文化的谱系、基本面貌、历史特点有了大致了解;对于这些古文化在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位置及其价值,已开始思考;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必能对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在全人类文化的谱系树上加以定位并做出准确评价,成为未来的人们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共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考古学的建设来说,似乎需要一种和平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是在这70多年中,至少有30年以上是在战争与社会动乱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只要我们想到80年代初英国的丹尼尔在论述全球考古学史时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就不能不对曾为中国考古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一批前辈学者李济、梁思永、石璋如、夏鼐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并且自50年代后期起,不断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设做出有全局性意义的指导,所以当他走完一生之路后,千百名弟子尊称他为“一代宗师”。
秉琦师之所以能做出一系列重要贡献,我感到,一是因为他几乎经历了中国考古学自奠基至今的全过程,还几乎一直处在核心圈内,理解不同时期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客观需要;二是他有独特的敏锐眼光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头绪众多的新发现中,善于找出当时的学科生长点和概括大量分散的材料;三是他的“有教无类”品格,同许许多多奋斗在考古工地第一线的人员,长期保持着师生般的关系,可以经常及时了解到各地的考古新发现和由此得到的新认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终生一心为重建中国古史、为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为中国考古学能更好地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奋斗不已。
秉琦师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贡献,主要结集在以下三本书中。第一本是1984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反映了他最初40年在发展考古类型学方面的成就。第二本是1994年9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主要反映了他在以后10年间为寻找中国古史发展的轨道和模式所做的新探索。第三本就是1997年6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现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是自述体裁的叙述毕生考古经历和研究内容的系统总结,篇幅不大,却反映了我国考古学近60年来的时代精神和秉琦师对其研究成果的自我归纳,对于了解他的学术思想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
本书在香港出版后,内地的许多学人很想阅读,但购买不便,所以北京决定重版。三联要我写一篇介绍,我想,全书既然概述了秉琦师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全过程,我就需要对反映秉琦师主要研究成果的三本书,都做些背景说明,便于大家更好地了解他的学术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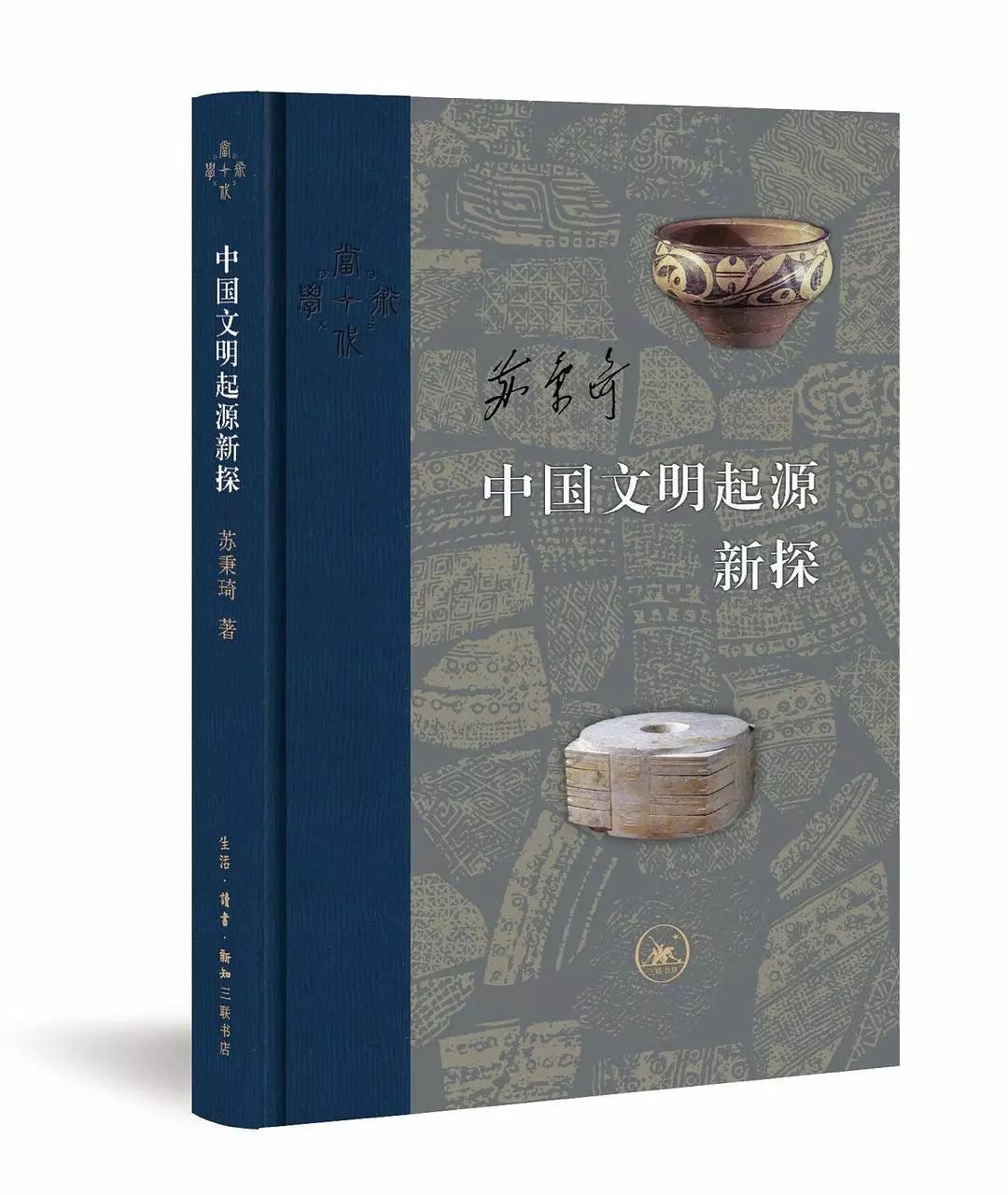
《考古学论述选集》收录了1941—1983年的23篇著述,反映了秉琦师创建中国考古类型学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考古类型学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的,主要研究考古学遗存外部形态的演变过程,所以又被称作形态学或分类学。在欧洲,从15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收藏罗马古物的热潮,逐渐形成了古物学;18世纪扩大到收藏希腊古物,进而又扩大到古典世界以外。19世纪初,丹麦注意收藏北欧古物,为了探求古物的年代和族属,从韦代尔·西蒙森和汤姆逊开始,对古物的形态和装饰进行分类研究。最明显的差别自然是质地,于是,提出了工具和武器经历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时代说。这种意见很快就在瑞典、德国等得到承认,从此,类型学研究在北欧就成为一种学术传统,终于出现了一位大师蒙德留斯。他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明诸时期》的首章中,系统叙述类型学理论,并把此章叫作“方法论”,标志着考古类型学理论已经成熟。
差不多同时,英国的皮特里用类似的方法研究陶器形态演化序列,寻找出了埃及的前王朝时期。蒙德留斯是在同一种器物内分出型别,再在同型内寻找演化序列;皮特里则主要是笼统地在同一种器物内排列形态的演化序列。蒙氏的方法当然更完善些。
在我国,1930年梁思永先生首先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陶片,进行形态分类,把口缘、底部、柄或把手等部位依其形态差别,给以不同符号,用一种多层符号来标记陶器形态之别,但这样的符号,并不能表现出器物的形态演化顺序。当时发掘到的西阴村仰韶陶片,并未复原出什么完整器形,仅仅面对着一大堆碎陶片,当然难以找到合理的形态分类法。可是10多年后李济先生在进行殷墟铜器和陶器的形态分类时,尽管见到的是一大批完整器,但仍用着类似的多层符号记录法。李济和梁思永先生都是赴哈佛留学归来的,他们所以使用这种方法,也许来自师承。但这种方法没有寻找出器物的演化顺序,所以,这种最初的尝试,并未成功。
秉琦师在40年代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等地的陶器时,则找出了同一种器物(如鬲)的不同演化轨道,因而先区分为不同的类(即型别),再在同一类内寻找演化顺序,依次编号,由此而使用两层符号(即型、式)来表示器物的演化顺序。50年代以来我国一系列类型学研究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方法是合理的。秉琦师并未出国留学,但蒙德留斯的“方法论”于1935年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译本(郑师许、胡肇椿和滕固的),他是参考了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1959年时,他在《洛阳中州路》一书中,又把260座东周墓分为大、中、小三型和七个期别,即将每一座墓当作一个整体来分型、分式,不仅找到了演化顺序,还看出了墓主身份的差别。如果说,类型学本是为了寻找考古学遗存形态变化过程而出现的,现在则上升到了可以探索人们社会关系的高度。这是类型学的一大进步。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洛阳中州路》全书中的资料介绍部分,并未按秉琦师心目中的方法来分类,所以在此书出版前的半年多,他曾在办公室中手持一大沓中州路器物卡片遗憾地对我说:“真是没有办法。”此书中真正表达秉琦师想法的,是由他亲自撰写的“结语”部分。
他对考古类型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65年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表达出来的。此时,他又找到了对考古学的文化要划分区域类型、再按类型划分期别、依期别来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就揭示出了考古类型学具有为寻找文化前进轨道和社会发展规律做好基础准备的能力。
这个评论,我在1983年写作《考古学论述选集》的“编后记”时已经提了出来。但现在还必须说明,秉琦师早在1951年调查西安沣西的古文化遗存后,已经有了一点仰韶文化应该划分(区域)类型的想法,而自50年代末以来,便一直把半坡和庙底沟视为仰韶文化中两个并列的类型,从未动摇过。可是在60—80年代,我国的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包括我自己,都把这两个类型静态地当作仰韶文化前、后两阶段的遗存,因而在当年写的“编后记”中,对此问题故意含糊其词,回避明确说法。直到90年代初,看到山西垣曲古城镇东关等地仰韶文化的材料后,我才确信并列类型之说,懂得了原来以为证明半坡在前、庙底沟在后的一些地层关系,只是因为庙底沟类型后来曾将其分布范围扩展很大,把以前曾是半坡类型的活动区都包括在内,才出现了早期半坡在下、晚期庙底沟在上的地层。
全国考古学界对于半坡、庙底沟相互关系的模糊认识,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始终占有主要地位,秉琦师是唯一的清醒者。现在回想起来,他当年坚持自己意见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根据器物形态演化的原理,在没有外力影响下,半坡类型的杯口尖底瓶,不可能变成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尖底瓶;半坡类型彩陶的鱼纹、宽带纹等,也不会变为庙底沟类型的鸟纹和圆点弧线勾叶纹,等等。这一事例充分表现出秉琦师对类型学原理的把握是如何严格,也再一次说明真理有时确是在少数人手里。
秉琦师对发展考古类型学的思考,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未停止。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就在1981年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这篇重要文章,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做了全局性的归纳和区域类型的划分,引起了我国新石器研究的极大变化。
此文发表后,首先产生的影响是,迅速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从20年代以来陆续找到的仰韶、龙山、良渚、红山等文化,由于分布地区不同,当它们刚被发现后,很自然地被认为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但当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发掘了华县元君庙、泉护村和洛阳王湾等地的遗址后,因为大家不仅普遍误认为半坡和庙底沟是仰韶文化前、后阶段的遗存,还因见到嵩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是从当地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遂出现了一股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潮,以为马家窑、龙山、马厂、红山,乃至新发现的大汶口和大溪等彩陶发达的文化,都是从仰韶文化蔓延出去的地方变体;山东的龙山文化,甚至江南的良渚文化和甘青的齐家文化,也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这种思潮随着各地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后来已慢慢退缩,但直到80年代初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我记得此文发表后的一个多月,在王府井大街的考古所中,作铭先生刚从国外回来,看了这篇文章,就到秉琦师的办公室里对秉琦师还有安志敏先生和我说:“你(面对秉琦师)的文章很有意思,和你(转而面向安志敏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你是讲大一统的。可惜这篇文章没有附图,别人不容易看懂。”另据1983年冬我在哈佛大学接触到的情况,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当时也有相当影响。只要知道这种背景,便能明白正因为此文冲破了30年来大一统思想的樊篱,并相当准确地把我国境内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划为六个大区和概括为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两大片,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建立起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