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信息
一份不能错过的宾大历史保护学习指南


三年前,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毕业,在宾大第一次见到Fisher Fine Arts Library的时候,对这些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文丘里的手稿,梁思成、林徽因、童寯、杨廷宝等大师们的档案就在这里保存着,只是惊讶于这座建筑的美好。当时我只是一个单纯喜欢老房子的商科生,怀着有些盲目的热情和破釜沉舟式的执念,就放弃了去伦敦政经(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继续读商科的选择,转而申请到了宾大的历史保护与城市规划的双硕士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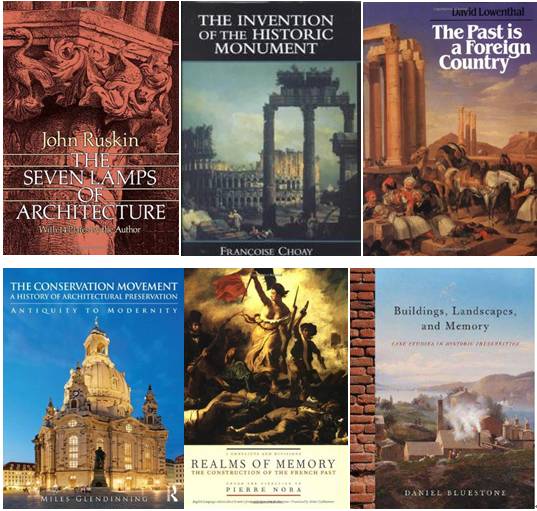
在必修课之外,我们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专业方向,比如保护技术(Building Conservation)和我学习的保护规划(Preservation Planning)等。景观保护(Landscape Preservation),场地管理(Site Management)和保护设计(Preservation Design)等方向选课则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更灵活一些。保护规划方向下的“历史保护经济学(Preservation Economics)”课程我在申请的时候就格外留意,一来是我本身就有经济学背景,二来这门课可能只有宾大开设。授课老师Donovan Rypkema大概是我在宾大遇到的最有故事的老师了。他年轻时是房地产估价师,据他说,他那时对历史保护一无所知,不过是在90年代敏锐地感觉到了当时新出台的历史保护税收减免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去哥大读了历史保护项目,便从此做起了历史建筑再利用成本估算的事情。现在他大约花甲,有两个自己的公司,只做历史建筑经济价值评估这一个小众市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接手了这个领域几乎世界各地的项目。13年的夏天,他带着我们去贝尔格莱德做暑期实践,在当地的美国使馆我们见过他的护照,是所谓的“double book”,厚得像一本书。我们笑称,他是我们学院里唯一一个在说去Georgia的时候,需要说明去的是格鲁吉亚还是佐治亚州的人。他一年中200多天都在世界各个我们想像不到的地方工作,而每周二上午,他则会提着拉杆箱出现在PennDesign幽闭无窗的小教室里,教我们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去审视当今社会的遗产保护。用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东西作为回答问题的小奖励。

他坚定地反对写了那本《城市的胜利》的哈佛教授Edward Glaezer,尤其对书中认为历史保护法案限制了纽约发展的论断极力批判,并不惮于在公共场合表达他对这位畅销书作家的异议。最后一个学期里,我做了他的助教,更明白了这个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一个遗产保护者,只懂得房地产和税法的老人,内心其实是个十足的遗产保护者。与建筑或者建筑史出身的遗产保护者相比,他更懂得如何说服别人历史建筑的价值。他研究历史建筑再利用带来的就业增长和经济效益;他相信保护历史建筑的最好方式是使用它;他也相信虽然再利用项目通常成本高、风险大,但无所作为的风险更大。他让我们了解历史保护行业在资本社会所处的弱势,因此在资本社会中必须以资本的逻辑来说服很多人。但他同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建筑的美和包含的历史记忆才是我们真正要去保护的东西。

必修课和各方向选修的课程修满后,剩下的学分选课就更自由了。我上了建筑病理学(Building Pathology),从工程技术的角度去理解遗产保护。其实知识本身并不难,无非是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力学和材料的知识。连没有建筑和工程背景的我都可以保证高中物理知识就已经绰绰有余。但是这门课绝对不仅是背背材料性质,看看湿度测定图足够的,核心是学会把一幢建筑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这门课让一幢建筑在我脑海中第一次以一个类似生命体的形象出现,不仅会受外界影响,也影响着外界环境。我也第一次在看一幢建筑时,不仅看到了构成建筑材料,还看到了使用它的人和它所在的环境。我记得教授Michael Henry曾经说,你们在进入一幢建筑的时候,要用整个身体去感受,要记得皮肤、鼻子和身体的感觉,因为你感觉到的温度、湿度,闻到的气味都会是判断的依据。

在宾大的三年,我从一个商科生成为了遗产保护工作者,遗产保护对于我也从情怀变成了专业。必修课上的训练成为了每天工作的基础,而其它的课程提供的视野则让我对现在做的事情保持着求知欲与思考的动力。用我妈也能明白的话来总结,是值回学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