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库
舞阳贾湖
摘要: 《舞阳贾湖》详细记述了在河南省舞阳县发掘出土的八千年前贾湖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资料。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系统地阐述了该遗址的文化内容、分期、年代、性质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下卷对其自然环境、人种及人类体质、经济结构、技术工艺、聚落形态、原始宗教、音乐文化等进行了探讨。本书对研究中原地区及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稻作农业起源、音乐起源 ...
舞阳贾湖(套装上下册)作者: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1999-1
定价: 400.00元
ISBN: 9787030069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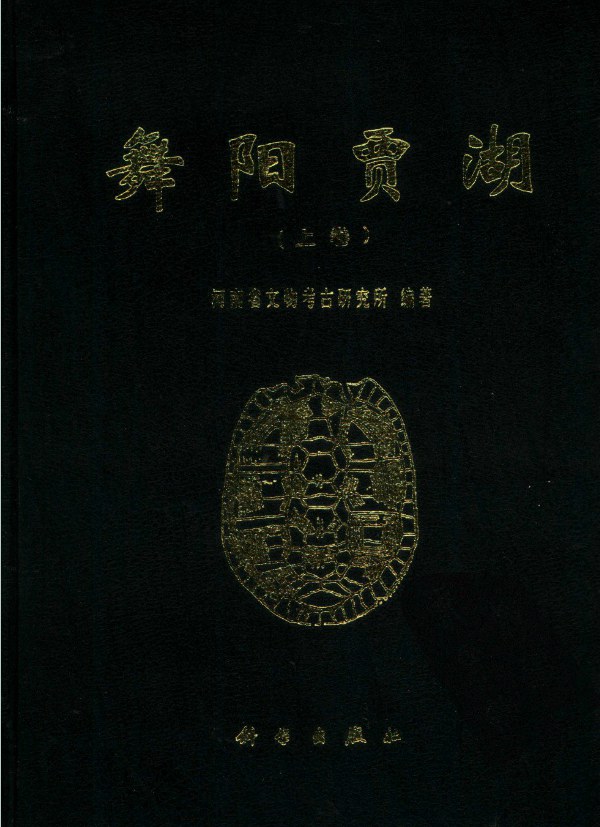
编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年2月
ISBN:9787030069238
✪ 感谢科学出版社对本次推送的大力支持。
内容简介
《舞阳贾湖》详细记述了在河南省舞阳县发掘出土的八千年前贾湖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资料。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系统地阐述了该遗址的文化内容、分期、年代、性质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下卷对其自然环境、人种及人类体质、经济结构、技术工艺、聚落形态、原始宗教、音乐文化等进行了探讨。本书对研究中原地区及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稻作农业起源、音乐起源、原始宗教和卜筮起源、原始契刻及汉字起源、全新世气候与环境演变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录
序 俞伟超(i)
前言张居中(v)
上 卷
第一章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3)
第一节 现代自然环境(3)
第二节 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 (8)
第三节 周围古代遗址分布(9)
第二章 发现、发掘与资料整理(11)
第一节 发现与发掘经过(11)
第二节 资料整理 (12)
第三章 地层堆积(14)
第一节 遗址保存状况与探方分布(14)
第二节 地层堆积与分布(17)
第三节 地层成因 (25)
第四章 居址与窑址 (27)
第一节 房址(27)
第二节 灰坑(66)
第三节 小坑与灶 (127)
第四节 濠沟(128)
第五节 兽坑(130)
第六节 陶窑(131)
第五章 墓葬(139)
第一节 分布(139)
第二节 墓葬形制 (140)
第三节 随葬品及其组合(145)
第四节 葬式及葬俗(151)
第五节 分类(151)
第六节 瓮棺葬 (198)
第六章 遗物 (200)
第一节 陶制品 (200)
第二节 石制品(344)
第三节 骨、角、牙制品 (401)
第四节 骨笛 (447)
第五节 龟、鳖及其它动物骨骼 (455)
第六节 炭化稻及其它植物遗骸 (462)
第七章 分期研究 (465)
第一节 陶容器主要器类演变趋势(465)
第二节 典型地层关系与典型器物组合(466)
第三节 分段讨论 (495)
第四节 分期讨论 (499)
第八章 14C年代学研究(515)
第一节 14C测年数据 (515)
第二节 各类样品14C年龄的分析 (516)
第三节 贾湖遗址各期段的绝对年代 (518)
第九章 文化性质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520)
第一节 文化因素与文化性质(520)
第二节 贾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 (531)
第三节 贾湖文化的去向(538)
附表(545)
附表一 房址登记表(545)
附表二 灰坑登记表(562)
附表三 小坑登记表 一(650)
附表四 兽坑(SK)登记表(651)
附表五 陶窑登记表(652)
附表六 墓葬登记表(656)
附表七 瓮棺葬登记表 (702)
附表八 陶系统计表(703)
附表九 陶系统计表(709)
附表一〇 陶片器形统计表 (715)
附表一一 陶片器形统计表 (723)
附表一二 完整陶容器称重统计表(730)
附表一三 陶制品标本统计表(732)
附表一四 石制品标本统计表(748)
附表一五 石料、废料岩性分类重量统计表 (755)
附表一六 石制品岩性分类统计表(756)
附表一七 石制品岩性器形对照表(757)
附表一八 骨、牙制品标本统计表 (765)
附表一九 陶制品标本分期一览表(771)
附表二〇 各探方遗迹分期分段一览表(774)
序
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80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现在,这批材料经张居中等同志用十年以上时间的整理,终于编纂成一部大型报告出版,自然是我国新石器考古事业中的一件大事。
贾湖遗存内涵丰富,价值很大,今后肯定会引起长时间的关注和多角度的研究。就此报告而言,即使仅作概略的观察,至少有以下三大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首次提供了能理解黄河中游至淮河上游和黄河下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主要是早、中期)关系的一个联结点。
关于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文化,自80年代以来已经认识到存在着老官台-仰韶(半坡)、垣曲东关-仰韶(庙底沟)、裴李岗-仰韶(大河村)、磁山-仰韶(后岗)和后李-北辛-大汶口等系列。统观这些系列,大汶口和仰韶及其前身诸系列,是差别突出的东西两大片,但相互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所以存在这种共同点,无非出于三种原因:一是不同文化在发展水平相同时,可以出现类似的文化现象或文化面貌;二是可能有共同的族源,尽管当分化成不同的族群以后,不同族群的差异会慢慢扩大,但总会保留一些共同点;三是不同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因相互影响而会形成一些共同点。抽象谈论这些原因,大家很容易取得共识,但在讨论某些考古学文化的具体现象时,如无实际材料作例证,任何推测都不会是能令人心服的解释。
就我国新石器文化的整体而言,其起源阶段至今还处于几乎是空白朦胧状态之中,因而不敢轻易对不同文化系列(特别是其早期阶段)产生异同之处的原因,作出具体推测。但贾湖遗存的发现,则在这方面向前走出了一大步。
贾湖遗存的年代大致在距今9000~7800年之间,同时包涵着黄河中、下游至淮河流域的东、西两大片文化系统的若干因素。例如其陶器(圆腹壶、罐形鼎、三足钵),同裴李岗文化的相当接近,而以占卜用龟和獐牙随葬之俗,又和时代要晚一些的大汶口乃至安徽薛家岗文化的风俗接近;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是和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一致而不见于黄河流域。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不能处处以陶器特征作为判定某一考古学文化属性的主要因素。贾湖遗存如仅从陶器出发,很容易被认定是一种裴李岗式的亚文化;如从随葬占卜用龟和獐牙着眼,又会看到这和山东至苏北的大汶口文化同俗,并且安徽的薛家岗文化中也有随葬占卜所用玉龟之俗(安徽含山凌家滩M4),可是裴李岗、磁山、老官台等黄河中游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恰恰都没有这种葬俗;再如其水稻耕作,更是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新石器文化中不存在的。只要综合以上现象,就可认为本报告把贾湖遗存命名为贾湖文化是非常正确的;报告中所作这个文化后来曾向淮河中下游和汉水流域等地区发生过迁徙的推测,至少就部分文化因素而言,也是有根据的。
如果对贾湖文化得到如上认识,就能感到即使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其文化的动态状况已是很强的。在建立考古学文化谱系时,为了确定各考古学文化的系列,着重考虑的自然是对各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进行静态的分类。但一当进而探求各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过程,特别是追索其变化原因时,又一定会仔细分析各种文化因素的变动情况,并在广阔的空间范畴内和自然环境同人们生存
能力的关系方面来寻找其原因。贾湖农业同江淮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一个系统的,贾湖陶器却和黄河中游是一个系统的。这可暗示出,有的地方,当农业发生后制陶术是从他处传入的,而有的地方则是从本地发展出来的。这种考虑,如从纯理论思维的角度来设想,似乎早就可以发生。但实践确实是理论的基础,甚至是其前提,所以至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中,上面谈到的那些看法,就是因为知道了贾湖等遗存才出现的。我以为,这是贾湖遗存最重要的价值。
第二,本报告提供了一个我国黄河、长江之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于当时文化发展前列的相当完整的实例。
贾湖发掘对于我国新石器早期遗存来说,得到了一处迄今为止最丰富的材料。就其内涵而言,刻符甲骨,五至七声音阶的骨笛,占卜用的龟甲,陶窑的出现,居住区从早期的与墓区混杂到中晚期的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的相对集中,农业同狩猎、捕捞、畜养并存的经济形态等等,表明其文化所达到的总体高度,远远超出了过去的想象。
贾湖遗存的最早年代,可达9000年前。这距离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发生年代,或是农业起源的年代不会太远了。如果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相比较,判若两种世界。这就清楚地表现出,农业的出现的确是一场大革命,迅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
二次大战后,西方学者因西亚等地的新发现,对距今万年左右的文化划出了一个无陶新石器时代的阶段,其标志就是农业或畜养业已经出现而制陶术还没有来到。从文化进步的逻辑过程来说,这应当是一个规律。但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只有依靠发掘材料,才能知道。例如在欧洲的广阔地区内,其农业和制陶业要到距今7000年前才从西亚一带逐步传播过去而发生的。在我国,从地理环境来考虑,农业和制陶业应该是自身发展出来的。贾湖陶器中的泥片贴筑法,就是中国和南西伯利亚至日本一带特有的。贾湖陶器中的泥条圈筑法,在欧洲是最早的制陶术,见于线纹陶文化,但贾湖所见的应当是从自身更早的泥片贴筑法发展而来的。另如贾湖的水稻农业和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谷子种植,也是中国自身出现的。由此可见,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独立过程,在贾湖遗址一带,或是包括更为广阔的地区,是否存在一个无陶新石器时代;或者说,这个时代发生于何时,时间有多长,农业、畜养业、制陶术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都已经是当前需要着重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这种看法出发,今后在寻找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发端期的过渡文化时,贾湖遗存因其时间之早和文化的发达,自然是一个重要的认识基点。我以为,这是贾湖遗存的另一最重要的价值。
第三,本报告除了分类发表原始资料外,又从讨论贾湖文化的总体面貌出发,列出下卷,分章研究其自然环境、居民体质、生业方式、工艺技术、生活状态和精神信仰等内容。
6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发生的扩大考古学文化研究范畴的趋向,自80年代以来日益对我国发生影响,一批年青学者正在努力从各方面作新探索。本报告的主要作者,近十年来就一直为此而不停顿地思考。他在繁重的整理贾湖资料期间,还多次挤出时间,参加渑池县班村遗址的发掘,和一批志同道合者从田野到室内,长时间地反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本报告体例的确定和内容的叙述,就是他长期思考后的一种表达。
科学研究当然有其国际性,但即使是正确的理论,如果没有和实际结合而实现了本国化、本地化,又难以取得成功的效果。对于人文科学来说,尤其如此。因此,任何合理的探索,不必有固定的模式。这本报告,就是作者根据发掘材料的实际,拟定了自己的模式。这当然会受到现有认识的限制,论述也不一定都妥当,但在当今沿袭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体例的多数发掘报告之中,毕竟又提出了一系列应该注意的新的观察角度,扩大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范畴,带来了不少新启示。我以为,这就是本报告的第三个重要价值。
有此三点,这当然是一本意义重大的考古发掘报告。
俞伟超
1998年9月22日凌晨
前言
在经历了4年发掘,11年整理,前后15度春秋之后,这本书终于脱稿,将要付梓啦!但是,我虽有瞬间的如释重负之感,却无法真正的感到轻松!
有人说,电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那么,考古学就是一门遗憾的科学。面对着那么多待我们进行解读和阐释的无名氏先民的永远沉默而又绝对真实的遗迹、遗物和丰富的信息,我们的知识显得如此之贫乏,我们的思维显得如此之苍白,我们的方法是如此之单调,自知我们的结论距客观真实岂只差之千里!然而岁月如流,已不容许我无限地思考下去,只得把这些不成熟的思考结果和盘托出,敬请学术界师长和同仁品头论足,就像一个刚交了答卷,等待评判分数的小学生,心情怎不紧张呢?
贾湖遗址的发掘是在80年代中期,刚刚跨出校门不久的我,尚无田野考古经验可言,可以说,我的田野考古经验的积累,是在摸索中和无数的遗憾中进行的。如房址的发掘、陶窑的确认,都是在发掘的中后期才逐渐掌握其规律的,而聚落的布局、环濠的走向,则始终未能进行全面的了解。更不用说与周围聚落的关系的研究。如果让我从头开始,肯定会比当时做得好得多,因此不得不留下深深的遗憾!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虽然也想尽可能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全部已占有的资料,同时,查阅了大量中外考古学家关于理论与方法的论著为借鉴,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最终未能实现。如陶器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和动物骨骼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即是如此。在陶片统计中,虽试行了重量统计的计量方法,但其器形统计结果似乎与传统的数片法差距过大,虽然认为称量法统计结果可能优于数片法,但似乎缺乏衡量的尺度,因而也不能说不是又一个遗憾!
另外,因本书篇幅较大,写作时间较长,前后在行文风格与体例上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又因时间较紧,未来得及认真斟酌修改,故而显得比较粗糙,乞望读者诸君多多原谅!
这里还需声明一点,就是凡过去发表的贾湖遗址的资料,若有与本书不一致的地方,均以本书为准。
二
当基础资料整理接近尾声时,如何介绍这批材料,曾使我颇费心思。纵观国内已有的考古发掘报告,都有可借鉴之处,但采用哪种体例,才能更适合介绍这批材料呢?为此事我曾先后请教过严文明先生、俞伟超先生、王象坤先生、孔昭宸先生等,他们都曾给我不少宝贵启示,陈星灿先生、曹兵武先生、李永迪先生还提供了不少参考材料,几经修改,才确定了现在这种格式。
本书上卷是传统考古报告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有三点:一是鉴于有些考古报告对现代自然环境部分过于简略,无法与遗址形成时期的自然环境因子进行对比研究,这里适当增加了现代自然环境因子的介绍篇幅。
二是由于贾湖文化遗存虽可分为三期,但并不为学术界所熟知,这种分期意见能否为学术界所接受,也是个未知数,如果按分期来介绍所有遗迹和遗物,不仅拉长了篇幅,割裂了资料的完整性,而且会有强加于人之嫌。因之,就采用了系统介绍材料,之后用专章讨论分期的形式。但由于陶器的变化远较其他遗物频率为快,这里的分期主要以陶器的变化为依据。并对各期的不同遗迹进行了归纳,而对变化不太明显的遗迹和石、骨器等遗物则归纳不够,这也是遗憾之一吧!
三是把¹C年代研究作为独立一章进行介绍,有两个原因:一是¹⁴C年代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与其他章节确有不同,在全书中又具有重要的地位。二是这部分研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文物科研专题经费和香港谭耀宗先生的双重资助,理应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这样就使上卷拉成了九章。
本书下卷的内容,传统考古报告是作为附录列入的。但实质上,这些内容都是考古学研究的不同侧面,是考古报告的有机组成部分,决不是游离于考古学研究之外的可有可无的点缀和附庸,况且,考古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一道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所获资料进行全方位的阐释,与考古工作者将所获涉及其他学科的标本送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鉴定,由考古工作者收入考古报告作附录的方式相比,是不能等而视之的。作者参与了下卷所有相关学科的研究,有些章节还是作者独立完成的。鉴于上述考虑,就未再称为“附录”,而以“下卷”统之。
这个决心下了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用什么体例来进行编排呢?
大凡人们选择聚居地,首先考虑的是该地是否适合人类的生存,换言之,环境是人类选择聚居地的第一要素。那么,贾湖人为什么要选择此地为其聚居地,并在此生活千年之久呢?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在贾湖人的生存和发展中曾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贾湖人离开这里而导致聚落的废弃呢?所以,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应当首先研究的对象。鉴于此,古环境研究就被列为本书下卷的第一章。
有了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着一个什么样的人类群体呢?换言之,是什么样的人选择了这个优越的生存环境呢?他们的体质特征如何?人种特征又如何?于是,人种和体质人类学研究就被列为本书下卷的第二章。
一定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在这一环境中生存的人类群体的生业形式。那么,在这一环境中生存的人类群体,又是如何适应这种环境而采用何种生业形式谋生的呢?其主体生业形式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本书下卷第三、四章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稻作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具有突出的位置,并且此项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因而进行了专章研究。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产规模的大小,收获量的大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工艺水平的高低。技术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是人类千百万年无数经验的积累,更是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之一。那么,贾湖人的技术工艺水平如何呢?这是本书下卷第五章要回答的问题。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从大量材料可知,贾湖人已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用考古学的材料对社会关系的研究”(BruceG.Trigger,1967)或“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①是聚落考古学的基本定义。本书下卷第六章试图运用聚落考古学的方法对贾湖聚落的布局、社会组织、人口及人们的生活状态进行初步探讨。
本书下卷第七章就贾湖遗址有关原始宗教的材料进行了阐释。这些材料与其说是原始宗教的,不如说是巫术的,但有些问题,如巫术仪式、巫术道具、巫师等,据已有材料,还难以说得清楚,因而就笼而统之称为原始宗教。
第八、九两章虽与第七章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因内容丰富,且在贾湖遗址的研究中地位重要,因之分别用专章进行了探讨。这样下卷就也拉成了九章。
纵观下卷九章,可分为六个内容相对独立的板块,其中第一章可称为环境篇,第二章为人类篇。第三、四章为经济篇,第五章为技术篇,第六章为社会篇,第七、八、九章为思想篇。主意虽是如此,因限于种种条件,加之本人驾驭材料的能力有限,所做尝试仍很肤浅,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所幸承担许多章节执笔的作者有不少是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有他们的精辟研究成果,使这本书增色许多,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本人水平低下所造成的损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
下面着重谈一谈本书对考古类型学的理解和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考古类型学作为考古学的主要方法论之一,自从19世纪中叶在生物进化论和生物分类学的启示下诞生以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安特生等西方学者将其介绍到我国也有70多年了。但是由中国学者掌握并运用于中国的考古学实践,则肇始于李济,完成于苏秉琦先生。纵观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其成败得失的关键,莫过于正确的分类。事物本身有不同的外在形态,其间又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又有着一定的规律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目前,分类的基本手段是分型定式,因之分类又要建立一定的标准,标准的建立又是主观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外部形态及其规律与主观的标准之间的一致性愈强,分类结果的正确性也就愈高;而主客观的一致性愈低,分类结果的客观性和正确性也就愈低。因之可以说,正确的分类首先揭示的应当而且只能是事物的演化规律亦即其演化的逻辑过程。
正确的分类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应是为了取得秩序从而进行正确的描述、分析和阐释。比如器物的分类,就应是为了正确的归纳描述其外部形态,揭示其逻辑过程和历史进程,分析其原料、制作工艺和功能,进而阐释其主人的生活内容、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①②。某一类事物演化的逻辑过程,通常与其历史进程有一定的联系,有时甚至是重合的,但不能将其等同看待,因为逻辑过程是可以重复的,而历史进程是无法重复的。一般来讲,变化速度较快的事物,其逻辑过程与历史进程的重合率也就较高;而变化速度较慢的事物,其逻辑过程的重复就可能长时间内反复进行,其逻辑过程和历史进程的重合率也就较低。比如陶器的分类与阐释,因陶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演化速率较快,且破碎率又高,所以,我们往往以陶器演化的逻辑过程作为某一考古遗存分期断代的标准。但石、骨器的演化速率较慢,且其逻辑过程最容易重复,因受原材料的限制,制作过程中的随意性也较强,所以其演化的历史进程往往较难以被把握和揭示。有时器体形态的变化是制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反映,其逻辑过程便很难与历史进程相一致。比如贾湖石器坯料的不同式别,分别是石器制作过程中不同加工阶段的产物,这种制石工艺技术传统只要不改变,无论哪一期制作石器时都仍然会重复这一逻辑过程,因此我们见到的I式石坯料的绝对制作时间就不一定早于V式,V式的绝对制作时间也不一定晚于I式。又如陶鼎足由长到短的被截过程,本书中之所以作为亚式来描述,乃是鉴于器体的外在形态的形成过程与器体本来的历史演化进程并不是一致的,这种器体外在形态的形成过程只是在使用中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种逻辑过程无疑也是不断被重复的,只要这类器物仍然存在,其用途和使用方法不改变,这种逻辑过程的重复就不可避免。虽然就某个鼎足来讲,仅存根部的肯定要晚于它的完整形态,但就众多同形态的鼎足而言,其形成的历史进程绝不会是同步的,并非都是被截的晚于完整的。依上述原则,本书所记述的大量陶器和石、骨器的分析结果可能分别反映该器类的演变规律和历史进程,具有分期断代意义,而其他部分石、骨器如石坯料的分式和陶鼎足的分亚式结果,反映的只是其制作和使用过程,只具有文化意义,并无分期意义,不能用来作分期分段的标准。所以笔者认为,在考古类型学的实践中,既要防止为分类而分类的倾向,同时也要防止把分类和阐释看做只为分期分段而分类的简单化倾向。揭示古人的生活内容、技术工艺、人际关系和社会状况,与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样,都应是考古类型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当然,正确揭示事物演化的逻辑进程,则是这些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以上理解是浮浅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或片面的,按此理解而进行的分类实践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之敬希考古界师友和同仁不吝赐教。
四
细心读者会发现,在这本一百多万字的书中,有几个传统考古报告常常论及的问题这里没有涉及,一是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二是族属问题,三是贾湖文化的来源问题。这里想就此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1.关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这个问题在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学界可以说是热门话题,其理论基础和立论依据主要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有关论点和材料。几十年来大量新材料证明,关于人类史前时期分为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大段的论点似乎把复杂多变的人类史前史过于条理化了。且不说婚姻制度与社会发展阶段本身并不一定是同步的,就是婚姻制度本身也是复杂的,在许多情况下,父系、母系和双系是并存的,原来作为划分父系、母系社会标志的一些考古学现象,如并非太大悬殊的随葬品多寡不一现象、少量的异性合葬现象和个别的儿童厚葬现象等,往往与各个人类群体的埋葬习俗有关,而与婚姻形态并无直接或必然的联系,更不能用来说明该考古学遗存属于何一社会发展阶段。若按以前的观点,贾湖遗址大量的同性和异性合葬及随葬品有一定悬殊的现象,是属于父系社会呢?还是属于母系社会?似乎都难以自圆其说。这些现象只可能与当时贾湖人的埋葬习俗有关,是当时的原始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甚或就是一定的巫术仪式的反映,比方说,某一多人合葬墓,可能就是某一扩大家庭某个时间范围之内(譬如说是一年)去世的所有成员的一次集体慰灵仪式的结果。但由于作者精力和能力有限,对上述问题只是一些朦胧的认识,并无成熟的观点,目前很难对贾湖遗址复杂的埋葬习俗进行深入而有价值的剖析,所以只将原始材料进行详细记述,而对于上述问题,只有留待有兴趣于此的同仁进行深入探讨。至于是属父系社会还是属母系社会的简单划分,似无再费笔墨之必要。
2.关于族属问题
贾湖文化是哪一个古代部族所创造的呢?换言之,谁是贾湖文化的主人?笔者自知文献功底太浅,本不愿附庸风雅,但考虑到重建中国史前史不仅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目的之一,也是史前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就不揣冒昧,想谈一些粗浅认识。但文成之后,总觉得问题说不清楚,不成样子,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就把这一部分从正文中删除了。现在又觉得这个问题不提一下,总感到意犹未尽,就把我的不成熟想法在这里作一概述。
如本书上卷第九章所述,贾湖文化主要分布于淮河上游主要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包括现代的河南省中、东、南部漯河、驻马店、周口和许昌、信阳一部分,影响所及可达皖中一带。据徐旭生先生考证,这一带是传说时代东夷部族的势力范围,东夷集团在传说时代有三大部族,即太昊、少昊和蚩尤。从分布地域和古文献所示时间序列上来看,贾湖文化的主人以太昊氏部族的可能性最大,主要理由是:
(1)贾湖文化的分布地域与传说中的太昊氏地望大体一致。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昊之墟也。”即在今日淮阳县一带,与贾湖直线距离仅100余公里,且都在33°40'N附近,属于同一纬度的同一地理单元。其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也基本一致。如大量的夹蚌陶、宽扁形鼎足及石磨盘等。
(2)贾湖文化早于被认为属少昊氏所创造的大汶口文化,并与之关系密切。在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普遍分布着大汶口文化和龙虬庄文化(或称“青莲岗文化”),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它的大量埋葬习俗如随葬龟、狗和獐牙等作风具有鲜明特征。而这些因素并不见于大汶口文化的前身北辛文化,更不见于后李文化,却普遍存在于贾湖文化之中,表明大汶口文化与贾湖文化也有某种文化传承关系。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氏部族所创造。经唐兰先生考证,“太昊和少昊可能有先后之分,太昊在前,当少昊强盛时期,它已经衰落了。”那么,贾湖文化早于北辛——大汶口文化二千多年,从贾湖和大汶口各自强盛时期的先后顺序、分布地域和文化面貌的相似性来看,早于大汶口文化的贾湖文化为太昊氏部族所创造,是完全可能的。
(3)关于太阳神崇拜的传统。贾湖文化陶器刻符、龟甲刻符都有与太阳有关的内容;稍晚于贾湖文化,文化面貌相近的安徽侯家寨遗址也发现有与贾湖相似的太阳形陶器刻符。大汶口文化的带有与太阳有关的陶文更为学术界所熟知,这应与他们都存在太阳神崇拜有关。据古史传说,两昊集团都与太阳的神话有关,九夷之中就有一阳夷。从字形上看,“昊”字就是“天”上有一“日”字。两昊之所以都称昊,表明太阳神崇拜是两昊集团的共同崇拜形式。如果大汶口文化属少昊氏部族所创造可以确认的话,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贾湖文化为太昊氏部族所创造。
(4)都有与鸟神崇拜有关的内容。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太昊氏风姓。笔者认为至少太昊氏的一支系风姓。九夷之中就有风夷。风,凤也,即为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又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昊氏以鸟名官。从郯子所述少昊氏的一套以鸟命名的政治或历法体系来看,已相当成熟,似经历了相当长的历程,很可能来源于风姓的太昊氏。今查贾湖遗址中出土的鸟类骨骼中,只有丹顶鹤、天鹅和环颈雉三种,均为美丽的观赏鸟类。我们且不说天鹅和环颈雉骨骼的埋藏原因,至少用丹顶鹤肢骨所制的骨笛,已具备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对美妙动听的音乐与仪态优雅的仙鹤的联想,自然可使原始人达到崇拜的程度。当然它与两昊集团的崇鸟传统可能也有一定的联系。
以上几点使我们有理由推测,贾湖文化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太昊氏部族所创造。但这些想法肯定都是不成熟的,朦胧的,证据不足,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只在这里把自己的思路谈一下,表明笔者愿与有兴趣于此的专家、师友共同探讨的愿望而已。
3.关于贾湖文化的来源问题
在本书上卷第九章,笔者对贾湖文化的去向进行了剖析,但对其来源却未提及。并非笔者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经认真思索,仍未理出个头绪来。
从距贾湖遗址仅数公里的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的文化面貌观察,与北方更新世末的细石器遗存如灵井、下川、虎头梁等基本一致,所反映出的生业形式应是适应于荒漠草原的游猎经济,而再向南迄今未见类似遗存,因此推测大岗所在的33°40'N一线有可能是更新世末最后冰期盛期时荒漠草原的最南边缘。从大岗细石器遗存的文化面貌分析,很难将其与具有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的贾湖文化联系起来。似乎贾湖文化不可能由当地的旧石器末期文化发展而来。这就自然引起了贾湖文化南来说的话题。但是,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纵观北方地区的更新世末期,基本上都分布着以细小石器为代表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模式是与当时特定的气候环境相适应的,即适应于荒漠草原的游猎性经济。但是,当更新世结束,全新世开始之后,气候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特别是一万年以来,气温迅速转暖。与此同时,各地的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果与当地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细石器遗存相比较,似乎均会遇到与贾湖文化同样的难题。这些以栽培旱作植物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农业文化的来源,很难都用南来说、西来说来解释,更不用说北来说。这样以来,产生原始农业的机制只能从当地的旧石器末期文化中寻找原动力。
一般来讲,人类受求生本能的驱使,适应环境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在原始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中,唯一的中心和目的就是两个字——生存,直到今天,生存权仍是人权的核心和重点。因之,原始人类的一切日常活动都是围绕着生存而展开的。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人类都千方百计适应它,从而顽强地生存下去。因此我想,在最后冰期盛期的数千年艰难岁月里,人们的生业形式应是多元的,食谱应是广谱的,应该包括狩猎、捕捞、采集等多种可能,甚至不能排除初期的栽培植物和训养家畜的实践。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大岗、灵井、下川、虎头梁那样的旷野型地点,均属于在游猎活动中的临时营地性质,而其较为固定的居住地可能因地貌变迁、埋藏、居住时间等种种原因而发现较为困难,而这些居址可能正代表了反映当时的人们生业形式的另一个侧面。这种材料上的原因可能正是造成上述错觉的关键所在。
试想在最后冰期期间,由于御寒的需要和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人们只能寻找那些天然的避寒地点,而天然的洞穴、岩厦等正是理想的聚居点,不仅北方的山顶洞、小南海、织机洞、小空山等如此,南方的仙人洞、甑皮岩等也如此。太行山、嵩山、伏牛山等众多的石灰岩洞穴为人类提供了理想的避难所。人类不仅在这里生息繁衍,而且积累经验,积蓄实力,特别是那些能够果腹且食性较好、又便于储藏的植物种籽可能早已被人类发现并长期反复栽培,这些在采集中产生的重大发现可能只是因为当时的恶劣气候和环境所限只能在个别地点像试验田一样地零星种植而无法普及。正是这些无数代的经验积累才能使全新世之初北方地区原始农业部族戏剧般地发展壮大起来。由是可以说,在靠近太行山、嵩山、伏牛山地区产生具有较为发达的磁山、裴李岗、贾湖等原始农业聚落绝非巧合。这些人类群体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来源于当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完全可能的。如贾湖出土的打制石器与南召小空山上洞的旧石器在制作工艺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就反映出二者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性,暗示我们如果到南阳盆地去寻找贾湖文化的源头,可能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上述认识只能是无据的推测而已,故不敢写入报告之中,只能在此略陈己见,以做引玉之砖。而这一推测尚需大量的考古学新材料来证实。目前,在华南地区已发现许多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而北方地区这个时期的遗存已被人们所认识的只有河北徐水南庄头一处。但这不能说明北方地区缺乏这个时期的遗存,而是它还未被人们所认识而已。相信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工作的深入,这个历史之谜的谜底被揭开已经为时不远了。
张居中
1998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