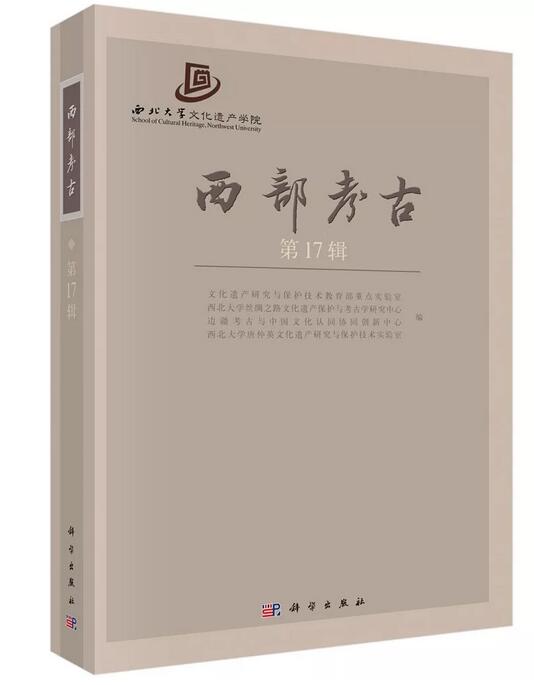专家观点
中古时期活跃在西南地区的粟特人
早在汉晋时期,已经有迹象表明,胡人可能已经循青海道南下抵达成都平原。作为非统治中心的四川地区,胡人入蜀的原因之一可能与商业利益的驱动有关。《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向汉武帝汇报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可见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大夏与蜀地之间已经有了民间的贸易往来,虽然当时是否已有大夏商人曾经来蜀,还无直接的证据,具体的路线更无法做进一步的推测,但这种胡人商贸在张骞开通西域之前便已经存在可能是历史事实。不排除当中许多路线是通过中转贸易来实现的,这些善于经商的“胡人”为3 世纪以后中亚一带的粟特人凿通了来华路径并非没有可能,这应在今后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两方面进一步加以注意。
汉代以来,由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以入西域,是内地和西北边区间乃至中外间的交通要道。但这并非唯一的通路,根据史籍记载,我们看到,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通行历史悠久,张骞在大夏见到来自身毒的邛竹杖与蜀布是人所共知的事,以后虽然不那么显赫,但南北朝时对南朝来说却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它联结了南朝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曾经起到了颇大的作用。例如,三国时期诸葛亮于蜀后主刘禅建兴五年举兵北伐时,《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记载:“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 马雍先生认为《三国志》中所提到的“凉州诸国王”当指西域鄯善、于阗等国王;“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很可能就是当时侨居于阗、鄯善的中亚移民;“凉州诸国王”很有可能是凉州、张掖、酒泉乃至敦煌一带居住的月氏、康居等胡人聚落的首领,推测这些人中间已经有不少昭武九姓的粟特人。《隋书·何妥传》载:“(何妥)西城(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隋书·何稠传》记载:“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何妥的侄子何稠,自幼受家庭熏陶,少年时就随何妥进入长安。他先在朝中获得了职位,后来负责王室的御辇工作。隋朝建立,他供职于太府监,掌管皇室的器物营造。由于他具有专业知识,曾经在宫廷作坊制造出“波斯国尝贡、以金钱与厢珠圆饰做成的金绵锦袍”,受到皇帝的赏识。6 世纪90 年代,何稠因再度发现代替琉璃的化学制法而名动一时。何稠的祖父就是来自西域何国的粟特商胡,他很可能是通过当时的河南道由西域进入益州的。何稠家族定居的郸县可能存在粟特聚落。西南地区还出现了祆教痕迹,如祆教赛神曲《穆护歌》的流行与灌口祆神庙的存在。因灌口祆神庙与郫县相邻,故而郫县可能存在粟特聚落。西南地区的粟特人在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经历了汉化的过程,何氏家族因为掌握了西方的工艺技术而发家致富,获取官职,但以儒学为官,史书将之列为《儒林传》暗示了何氏家族的汉化程度。
《续高僧传》卷二五《释道仙传》记载:“一名僧先,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值钱数十万贯。”这位名为“僧先”的僧人原籍系胡商,本康居国人,即为昭武九姓胡人,善经商为其特点,往来于吴、蜀之间,江海上下,大约便主要是利用了“青海—岷蜀道”这条路线。推测粟特商人以蜀锦等丝绸这类珍贵的商品进行中转贸易。
《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蜀部沙门释明达传》:“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严持斋戒……以梁天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时巴峡蛮夷,鼓行抄劫,州郡征兵,克期诛讨。达愍其将苦,志存拯拔,独行诣贼,登其堡垒,尉喻招引,未狎其情。……达乃教具千灯,祈诚三宝。……以天监十五年,随始舆王还荆州。” 释明达这样的康氏僧人同僧先一样,其先祖也来自康居,虽然他不同于僧先以经商为业,而是在益州、巴峡一带传授佛法,但可知其当系粟特系统的胡僧,所谓“来自西戎”,应当理解为沿丝绸之路自西域而达益都,这条路线大约也应当是走的青海至岷蜀一线。粟特人主要是经过河南道进入四川盆地,当然,吐谷浑境内也有不少粟特人。从今四川松潘进入“青海路”可以到达西域,也可从川南进入陕西再走丝绸之路绿洲路主干道。巴蜀自古就是重要的丝绸产地,更是商业繁荣昌盛之地,商旅往来十分频繁。因此,南北朝以来,巴蜀即为西域胡人行贾之地。但是,长安、洛阳两地的粟特人应该是从金牛道或米仓道进入四川盆地的,南朝时期益州与建康关系密切,一部分粟特人也有可能通过长江水路来往于益州与建康两地。
《南史》卷五三《武陵王传》称:“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由此可见,武陵王发展经济的措施之一是利用巴蜀的有利条件,与西域国家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这些商人活动于岷蜀一线,主要经营何种贸易史无明载,但从汉晋三国时代成都已成为中国西南最为发达的蜀锦产地这一点推测,大约与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的传统习俗一样,其可能仍以蜀锦之类的丝绸中转贸易为大宗。南北朝时期,在吐鲁番境内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出土了一批蜀地生产的丝织品。有学者认为,它们有可能便是通过丝绸之路河南道由蜀地运往高昌的,粟特人成为中间的转手贸易者这种可能性很大。
四川的粟特商人可能未经甘肃通道,而是从其他途径进入中国的。其中一条为从于阗到达柴达木盆地,绕经河西走廊,向南穿过吐蕃地界,到达青海湖(Kokonor Lake),再到兰州,之后要么到中原,要么直达四川。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敦煌烽燧发现的粟特文第5 号古信札提到某商队从敦煌进入阿尔金山(Altun Shan),城镇和柴达木由此被一分为二。另外,藏语中的“医生”一词很可能源自粟特语(bitsi 源自粟特文βyč,它本源于印度语),将医学研究传入吐蕃的人中就有几个粟特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大事记年”694 年条下载:“噶尔·丹古为粟特人俘去。”《汉藏史集》中记载刀剑在吐蕃的传播时提到了“索波剑”,所谓“索波”,是藏语对粟特的称呼“sog-po”,这种刀剑应该产自粟特地区,后传入吐蕃。吐蕃王朝时期曾一度攻陷并控制了“丝绸之路”,在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木简中多次出现了“Sog”一词,学术界倾向于其指的是粟特人,这说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与新的占领者吐蕃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丝绸之外输并非自汉唐开始,它的起源,见诸经史所传者,一直可以上溯到战国和秦汉。因为从文献史料看,《山海经》所记的朝鲜、身毒、大夏、月文以及《穆天子传》所记的“旷野之原”大多不在中国,说明自古即有中西交通,决非从汉唐伊始,而蜀锦之外输,其年代也颇为久远。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 年),博望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见到蜀布,说明蜀地到西域的商道在张骞之前即已开通。以成都为中心,蜀陇道和蜀身毒道纵贯全川,北接秦陇,南通缅印,不但成为四川境内丝路的主干道,而且更是我国陆上丝路中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国际干道。这一干道就是中国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在印度河河谷,主要是吉尔吉特下游的荒凉地区,发现了一系列岩刻题记,这些题记中以粟特文最多,超过650 处。其中,以夏提欧(Shatial,约550 处)、达丹达斯(55 处)、欧希伯特(Oshibat,26 处)、索尔(Thor,19 处)、塔班(Thalpan,8 处)、罕萨— 海德奇石(Hunza-Haldeikish,6 处)、坎巴里(Khanbari,1 处)和坎普塞(Campsite,1 处)为代表。夏提欧是沿印度河顺流而下发现岩刻和铭文的所有地点中最远的一个。夏提欧是粟特商人的最终目的地,他们在此地和印度商人交易商品。这条道路的南北两端分别联系着新疆与西藏西部,北可通向中亚,南可抵达印度,古代曾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同时也为商业民族——粟特人往来于这条路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伊朗语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有90% 的粟特语铭文是在此地发现的。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夏提欧发现的粟特文题记为:“(我),纳里萨夫(Narisaf)之(子)娜娜盘陁(Nanai-vandak)于十[年(?)]至(此),并请圣地K’rt 之魂予以恩赐,让我快些顺利到达渴盘陀(xrβntn),去看望(我)健康愉快之兄长。” 这些题记应该是商人所刻,由此可以看出3 世纪粟特人在印度的重要性,其中的一些粟特文题铭比在甘肃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要早。
季羡林先生曾从经济关系、来源关系、意识形态、共同的历史使命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佛教和商业在印度发挥的重要作用,说到:“商人们积极出钱出物,供应僧伽。结果是佛教徒得到衣食之资,商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甚至物质上的好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玄奘特别提到了商人在佛教信徒中占了大多数,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征祥,示祟变,求福德。8—9 世纪的一份吐蕃文书《于阗国教法史》(Li-yul chos-kyi lo-rgyus),讲述了500 粟特(Sog-dag)商人前往印度,途中在大山迷失的故事。当新罗僧人慧超726 年穿过犍陀罗时,就在《往五天竺国行纪》的文字中提到了当时的粟特——汉地的兴胡。在与西藏西部相毗邻的印度河上游一带除了发现了汉文“大魏”使者的题记外,还发现了粟特人的崖刻题记,这条道路的南北两端分别联系着新疆与西藏西部,北可通向中亚,南可抵达印度,证明其在古代曾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
本文由孙莉 摘编自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西北大学唐仲英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实验室 编《西部考古》(第17辑)之《粟特人在西南地区的活动追踪》。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