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思考

【作者简介】陈雍,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1年秋季,一群年轻人聚在山东兖州,本来打算就他们共同关心的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并展开讨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时学术界和与会者的情绪大概是主要的原因。一晃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那次会议内容和中国考古学的思索,时时驱动我们思索的不是某种兴趣,而是一种无法逃脱的责任感。
在这里有必要对当时会议的学科背景作一下简单的回顾。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里产生的对自身的认识和要求,以及受外界刺激引起的浮躁和兴奋,使它强烈地感到理论的重要。在80年代的10年里,理论性和理性思维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时期,中国考古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标志是:
1.以《什么是考古学》为代表,对考古学自身的全面认识。
2.以《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为代表,对考古学方法论的总结。
3.以《探索与追求》为代表,对中国考古学的体系与学派的意识。
这些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假如把欧美考古学走过的历程分为三期,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整体状况,大约和欧美考古学的第二期相当。这是我们当年在兖州会议上提出的现下依然坚持的看法。在兖州会议上,我们试将世界范围的考古学的发展过程和语言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不尽贴切的比较。语言学大体经历了历史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以转换生成理论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三个阶段。如果把成熟的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学相对应,那么,以建立人类行为一般法则为目标的“新考古学”大体跟转换生成理论语言学相对应。从语言学的发展过程看“新考古学”的产生,显然是跳跃式的,或者是早产的或不成熟的。但它却可能代表了学科发展的方向。由于它的不成熟性,所以才遭到人们的非议。在兖州会议上我们还提出,起码目前在中国不宜提倡尚未成熟的“新考古学”。
上述两点对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看法,是我们对于以下三个跟中国考古学有关问题思考的基点。这三个问题是:
1.中国考古学家是怎样认识考古学的?
2.中国考古学从20年代到今天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3.当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论有怎样的内容?

一 通过考古学家对考古学的认识了解中国考古学
早在60年前,李济在《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编辑大旨”里开宗明义地指出:“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超过尝试阶段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需的哲学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这是中国学术界对于考古学这门新出现的学科最早的认识。今天由这段话不难看出,当时已经认识到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材料”,它的研究手段是自然科学技术,它的理论基础是哲学。
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考古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学家们对考古学的内涵认识越来越清楚了。1984年,夏鼐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指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部门。”他还指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即物质遗存。包括古代器物、人类居住及其他活动的遗迹以及反映古代人类活动的自然物。考古学不仅研究物质文化,而且还要研究精神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阐明历史过程的规律。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对这种看法进一步发挥,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这是迄止目前关于考古学最系统的论述。
在考古学的内涵里,性质和对象对于考古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似乎比起其它来都要大些。关于考古学的性质,60年来一直是明确的。虽然新近颁布的学科分类把考古学改订为和历史学属同一类级的学科,但在实践中,人们仍然习惯地把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学科,从而决定了中国考古学跟历史学一样属于个案研究类型。因为它不属于研究法则类型,所以它只能采用归纳法对单个的或集体的事例做出描述,对历史做出一般性概括。由此看来,考古学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不在于人为的分类,关键是要看它的研究类型是否改变。假如有一天,中国考古学变成了研究法则类型,那时考古学的性质也将随之改变。为把考古学从研究个案转为研究法则,国外的考古学家们做出了许多努力。目下且不论他们究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是第一个吃蜘蛛的,至少他们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思索的东西。
关于考古学的对象,60多年前考古学刚刚出现的时候,只能模糊地认识到是“人类历史材料”。现下一般的看法跟夏先生的说法一致,即古代物质遗存。但现下也有对遗存是考古学对象提出疑问的。之所以产生疑问,主要是对遗存内涵理解的分歧。
遗存是古代人类文化行为的产物。按一般分类法,遗存分为遗迹和遗物两个部分。任何遗迹、遗物只要没有脱离原来的堆积,就应当具有位置、形态、联系三个方面的属性。位置,包括遗迹、遗物在依次堆积顺序中的位置和同一平面上的位置。形态,即遗存由线和面组合的外部形状。联系,指一系列位置或形态的归集和联想。我们平常说的遗存的层位、类型和年代,就是依据这三种属性确认的。这里,类型是有形的,层位、年代是无形的。
考古学在不同的背景中有着从具体到一般不同的含义,但都离不开遗存。我们平常说的遗址发掘、墓葬发掘,就是从堆积中揭露出遗存,并揭示遗存的属性。这是具体意义上的考古学。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遗存而不是书写的文字资料来重建过去历史的学科,它的基本内容是解释遗存,根据遗存构造过去。考古遗存不仅为组织和解释提供了资料来源,而且还是重要的手段。考古学家就是凭借这个手段去重建或解释人类史前史的。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只由解释那些保存在遗存中关于过去的证据来实现。如果考古遗存能够被用作概括文化性质的基础,那么仅凭概括和关于现代条件的知识就不能重建和研究过去。
在20世纪前期的欧美考古学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考古学文化,如今人们开始对它表示不满,甚至提出疑问。并非考古学家喜新厌旧,而是考古学文化面对日益发展的考古学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究其原因,考古学文化不过是有限区域反复出现的特征联系,并不能代表遗存的全部,而遗存所包含的内容,随着学科的发展将逐渐扩大,考古学文化概括的遗存将更有限了。欧美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的不满和疑问,引起在中国考古学界首先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夏先生的注意。他提醒大家:“这些问题的提出,虽还不足以否定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性,但促使考古学家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时要作周到、灵活的思考,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因此,对于肇始于20年代而今还在表现出对考古学文化浓厚兴趣的中国考古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评价。
一般说来,考古学的对象决定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对象内涵的不断扩大,将导致研究范围的扩大。若对象范围变得很窄,研究范围也将随之缩小。在目前中国考古学文献中,包容最广的遗存含有以下的内容:
1.人工制品(分为遗物、遗迹、遗址三个层次);
2.古代工业制造过程中的废弃品;
3.与遗址有关的动物骨骼、牙齿和植物茎杆、籽实;
4.古代遗存中许多物质(如花粉、木炭)通过实验室所提供的资料。
根据上述考古遗存内容,可以把考古学分为狭义考古学和广义考古学。按照这种分类,在目前中国考古学文献中见到最多的是研究古代人工制品的狭义考古学。对于非人工制品的研究,近年取得令人注目的进展,并且初步形成不同的分支。如果我们承认“科学考古学与狭义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从这点来说,科学考古学的出现,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关于什么是考古学的答案。
由此我们联想到本世纪20年代以来形成的法国年鉴学派。这个学派对法国等地的历史研究方式极为不满,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太注重事件,太偏重政治,而且有狭隘性,同时又过分地脱离了相邻的学科;主张摆脱传统史学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束缚,把人类过去的所有方面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今天了解一点这种被称为“现代式”的历史研究,读一读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对我们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或许多少会有一点启迪与帮助。

二 通过历史的途径认识中国考古学
在对中国考古学进行历史的考察时,以下四点特别提请注意:
1.中国考古学的75年历史,不只是一连串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这些事件中蕴含的科学发展规律和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逻辑,尤其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才是它最精彩最诱人的部分。
2.《当代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序言”列举的三种考古学史分期的方法都可用来做中国考古学史的分期:
1)《美洲考古学史》依研究方式的分期法;
2)《丹麦考古学的社会历史》依发展程度的分期法;
3)《对考古学解释的反思》依理论解释的分期法。
此外,《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一文提出的区分考古学自我意识的标准,也可以用来对中国考古学史分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虽然在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有时甚至影响还很大,但是以政治事件为标准划分考古学史的发展阶段,并不符合考古学发展和变化的实际情况。
3.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应当是狭义考古学和科学考古学的历史。仅有研究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史是不够的。
4.以田野发掘为基本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跟宋代以来形成的金石学没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在中国考古学史里不应把金石学作为考古学的前身或考古学的萌芽。对此,李济早在60多年前就已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学者,有好些对于考古学尚有一种很普遍的误会。他们以为考古学不过是金石学的一个别名”。“其实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之关系,好象炼丹学之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与现代植物学。炼丹采药,自有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然而决没有人说它们就是化学或植物学。”
考古学史的发展,首先应当是它的思想的发展。考察欧美考古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在“新考古学”出现以前,大体经历了“觉悟”和“自我”两大阶段;“新考古学”出现以后,开始否定“自我”,表现出可能向“无我”方向发展的趋势。这第三个境界,在目前还只能说是一种追求。其它学科的思想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尤以艺术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考古学的思想发展也大体经历了“觉悟”和“自我”两大阶段。目前仍处在第二阶段。在“自我”阶段,中国考古学相继表现出比较强烈的自我觉悟、自我完善、自我满足(甚至是自我陶醉)的情绪。现下这种情绪正在慢慢地冷静下来,开始思索了,思变了,但似乎还接受不了或不愿接受否定“自我”的痛苦。
考古学方法论是考古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古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能够大体反映出考古学发展的过程。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主要是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发展的逻辑过程可概括为:
1.地层学:地质地层学—考古地层学—考古层位学
2.类型学:古器物形态学—考古类型学(器物类型)—考古类型学(文化类型)
3.年代学:古器物年代学—考古年代学(遗址年代)—考古年代学(文化年代)把以上三个逻辑序列按中国考古学经历的纪年对应在一起,便能得出以下二期:
一期20年代:地质地层学\古器物形态学\古器物年代学
二期30—50年代: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器物类型)\考古年代学(遗址年代)60年代—: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文化类型)\考古年代学(文化年代)
20年代为“觉悟”阶段,30年代至今为“自我”阶段。其中30—50年代主要表现为“自觉”(自我意识),60年代至今主要表现为“自在”(自我完善)。进入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希望这些变化能把中国考古学带进一个新的阶段。
(一)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考古实践和认识都刚起步。这一阶段的地层学以河南仰韶村遗址发掘(1921)和山西西阴村遗址发掘(1926)为代表。
仰韶遗址采用地质地层学的知识发掘,着眼于地层,按水平等距深度自上而下揭露,按深度记录土质、土色和出土遗物情况。实践表明,这种方法不适合考古发掘。西阴村发掘的地层学,虽然我们仍把它划在地质地层学的范畴里,但西阴遗址的方法跟仰韶遗址的方法却是有着明显的区别:1)探方揭露法,2)三维坐标记录法,3)复式地层划分法。所谓的“复式地层划分法”,即按水平等距深度(1米)划分大层(A、B、C),按土质、土色划分小层(a、b、c、),大层包含小层。这种复式地层划分法为考古地层学的地层划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形式。
20年代的类型学,我们称之为“古器物学”。需要多说几句,这“古器物学”,既不是金石学的别称,又不是欧洲上个世纪的古器物学。中国的“古器物学”自有它的来源;一是安特生的仰韶陶器研究,另一是李济的殷墟陶器研究。安特生用看地层中化石的眼光看待仰韶遗址地层里的陶器,在他的研究里带有明显“标准化石”的思想,可看作是一种带地质学色彩的器物学。李济《殷商陶器初论》的起点比安特生的要高。他试从陶器的名称、形制、用法、制法、年代几个方面考察,并指出研究陶器应象埃及考古学家那样,“凡是同样形制的,都编成一个目;分成时代,互相比较,由此定那形制的演化。再由形制的演化,转过去定那时代。”这些重要的认识和初步尝试,为下一阶段出现的器物类型学奠定了基础。
20年代,由于缺乏地层学方面提供的可靠依据,年代学只能靠器物形态的对比来推断相对年代。用简单进化思想排列不同的器物,或根据已知器物推断未知器物,是那时年代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二)30年代至50年代,中国考古学开始按照历史时期考古和史前时期考古的不同取向发展,学科方法论初步形成,进入“自觉”阶段。
地质地层学被考古地层学取代了。考古地层学出现的标志是1931年河南安阳后冈发掘。后冈发掘第一次获得了仰韶、龙山、小屯三期文化先后次序的确然的地层根据。这就是被考古学界所称道的“后冈三叠层”。后冈遗址的发掘,首先根据遗址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和厚度划分出层层叠压的地层,然后根据各个地层的包含物(主要是陶器)将所划分的地层归并为三个不同的文化层,即小屯文化层、龙山文化层、仰韶文化层。一个文化层可以包含一个或几个地层。依照三个文化层的叠压次序,分别称作“后冈上层”、“后冈中层”、“后冈下层”。在这里,有三个和“层”相关的概念:1)地层、2)文化层、3)遗址上、中、下层。三种“层”划分的根据不同:地层是土质土色,文化层是地层内的包含物,遗址层是文化层的堆积顺序。不难看出,后冈发掘采用的也是一处复式地层之间的关系就是遗迹之间的关系,遗迹从属于地层。这种内容的地层学流行于五六十年代,其延用的时间较长,在80年代出版的考古报告里还能见到。
蒙特留斯的类型学和生物学的分类学,对于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类型学以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以下简称《记小青》)和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以下简称《斗鸡台》)为代表。这两部著作都选择出土单位明确、器物关系清楚的墓葬器物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器物形态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把器物分成不同层次的类别,并用符号或数字表示不同的类级。《记小青》的分类系统是:目\式\型,式用序数(如277式)表示,型用拉丁字母(如R、F)表示。这种表述方式后来演化为式A型。这种式含型的表述方式,延至70年代的出版物里还能见到。《斗鸡台》的分类系统是:大类\小类\组。这个分类系统实际包含着“分类”和“排序”两个内容:“类”即“型”,用A、B、C表示;“组”相当于后来的“式”,用a、b、c表示。然后根据所分的器物把墓葬分成时间不同的组别。《记小青》特别注意到同一墓内各种器物的“共存的现象”和“有机的联系”。《斗鸡台》则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瓦鬲的谱系。各自不同的研究特点是和两位研究者的人类学出身与历史学出身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年代学的主要内容是,把地层学和类型学作为手段,对遗址和墓葬进行分期,用“期”这种不确定的时间概念来表达遗存的相对年代。
(三)60年代至90年代,考古学对自己“自觉”的感性表现渐渐感到不满,一方面在研究中不断完善学科方法,一方面不断对自身进行理性总结,从而转化为“自在”。
60年代以来形成的考古层位学,不再是靠新的发掘来充实它的内容,而是得益于对原有资料分析和认识上的进步。考古地层学最先在《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以下简称《论殷墟》)里得到改造。《论殷墟》是《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的地层学思想的发展,又是对《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一文关于小屯地层堆积认识的重要修正和补充。《论殷墟》把“地层关系”改为“层位关系”,初步形成以考古单位的层位关系为核心的地层学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1)遗址堆积的单位,2)诸单位之间的层位关系及表述方式,3)遗址堆积的层次。这种地层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单位”而不是“地层”。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为把这种内容的地层学跟上一阶段的地层学相区别,出现了“层位学”的叫法,90年代以来则明确地称作“考古层位学”。“地层学”改称为“层位学”,不仅是用词的改变,把“地层”改为“层位”,既表明了层位学的思想核心所在,又表明了中国考古学关于遗址堆积的认识已完全蜕掉从地质学脱胎出来的痕迹,真正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论。
进入60年代以来,器物类型学逐渐走上成熟与规范。《洛阳中州路》“结语”把一种器物的分型分式法扩大为包括成组物品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论殷墟》把器物的分类和排序规范地表述为:类\型\亚型\式,用器名\大写拉丁字母\小写拉丁字母\大写罗马字母表述这一系统。这种型含式的表述方式,逐渐取代了式含型的表述方式。
本世纪前期,在欧洲,考古学“文化”取代了“时期”,于是确认和区分考古学文化使考古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在中国,《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提出以后,使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随后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考古类型学由包括成组物品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推进到考古学文化的分型分式法,并初步形成一套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分类系统,即区系类型。
这一时期,考古年代学关于遗存相对年代的研究出现了用考古学文化序列表示时间划分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绝对年代的研究。我国于1965年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法测定考古年代。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25把碳-14年代跟考古学文化序列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体系,标志着年代学已由相对年代研究发展为绝对年代研究。目前中国考古学利用绝对年代体系进行年代学研究,已经由史前时期逐渐扩展到历史时期,夏商周三代的绝对年代体系的确立,已经为时不远了。
近几年来,中国考古学逐渐认识到,在它的方法论里,除了层位学、类型学和年代学以外,还应有一种解释考古遗存、用遗存重构过去的方法。其实解释的方法早在殷墟发掘时就出现了,不过这种方法分别零散见于个案研究里,现下还没总结出来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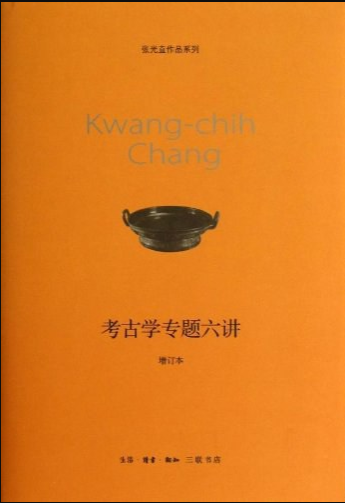
三 通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把握中国考古学
方法论或称方法学,是方法的系统和对方法的解说。方法论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方法论指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它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唯物辨证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广义的方法论是指科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可以大体分为:1)通用科学方法论,如自然科学方法论、人文科学方法论;2)专门学科方法论,如物理学方法论、生物学方法论、语言学方法论、历史学方法论等。考古学方法论即属于这一范畴。专门学科方法应当包括: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方法论的原则,方法论的具体内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跟“实践”相对而言的“理论”,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识的总结与规律的把握。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法论属于理论范畴。因此,有时或将方法论称作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的理论,是狭义的,它决定了方法论的思想原则与内容。
当前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理论主要有进化论和传播论,历史唯物论则是它唯一的指导性理论。尽管中国考古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跟外界隔绝的状态,但是闭门造车出则同辙,它的进化论也大体经历了自简单进化而多元进化的发展过程。“区系类型”的文化分类和“满天星斗式”的文明产生,均可视为多元进化论的产物。传播论的内容主要是文化的传播与迁徙。“文化因素分析法”就是基于传播论提出的。
从前面第二部分内容里我们已经知道,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全部研究活动总结出来的方法论,主要有层位学、类型学、年代学和有关解释的方法。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范围,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都不相同,但它们总是通过共同的研究对象——遗存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联系。
考古层位学是关于遗址堆积的单位和单位在堆积顺序中位置关系的学说。考古层位学特别注意被地层学所忽视的遗迹,认为无论是地层还是遗迹,对于堆积来说,都具有同样的分类级别,它们各自构成一个独立的堆积单位。诸单位在有序堆积中都具有一定的层位。一系列层位组成遗址堆积的次序。围绕这些内容,考古层位学起码应当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堆积的定义和性质,
2.关于堆积的分类和堆积单位的划分,
3.关于堆积单位在遗址堆积里存在的形式,
4.关于堆积单位在堆积中的层位和层位关系,
5.关于遗址堆积的层序和层面。
考古类型学是关于遗存分组归类和排序的方法体系。分类和排序的主要根据是遗存的形态和形态之间的各种关系。根据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所要研究的现象,可以把遗存分成不同的类级和次序。这种类级和次序能够对现象进行解释,同时对解释的方法有所限制。考古类型学至少应当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遗存形态的要素,
2.关于遗存形态之间的各种关系,
3.关于器物分类的原则和方法,
4.关于器物排序的途径和方法,
5.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分类和分类的概念。
在过去的类型学里,常常把排序和分类相混淆。其实,分类和排序属于两种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抽象地讲,分类是把遗存样本按照一定的属性划入最优集群的一些子集里的逻辑方法。排序是把遗存样本作为点,在以属性为坐标轴的空间里,依其相似关系把它们依次排列的逻辑方法。我们平时所说的“分型分式”,实际包含了分类和排序两种不同方式的类型学研究。只有从思维方式上搞清分类和排序的区别,在具体操作时才不会把它们搞混。
考古年代学是计算遗存时间和排列时间顺序方法的总和。用不同计时方法得出的时间概念不同。依靠层位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得出的遗存时间,是相对年代。用自然科学方法以及历史学方法得出的遗存时间,通常是绝对年代。不管用哪种方法计量时间,不论得出的是哪种年代,都必须有一定的计时单位,都必须按照遗存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这是考古年代学必须遵守的原则。考古年代学至少应当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概念,
2.关于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时限,
3.关于相对年代的计时单位、排列时间顺序方法、判断时间早晚方法,
4.关于判断绝对年代的方法。
目前中国考古学关于遗存“解释”的研究,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利用历史文献解释的方法,
2.运用历史唯物论概念解释的方法,
3.通过其它人文学科知识解释的方法,
4.通过自然科学知识解释的方法,
5.通过模拟实验解释的方法。
为了尽快地把解释的方法总结出来,这就需要抓更多的个案研究,使这一方法更加丰富;通过理性的分析,使这一方法逐渐形成体系。
通过对中国考古学的一番思考使我们感到,中国考古学离“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已经不远了。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文物季刊》1997年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您的稿件和服务意见请发往"民族学与人类学"微电子杂志服务邮箱: mzxyrlx@126.com
您的支持和鞭策将会是我们进步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