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从社区角度认识文化遗产的保护
从社区角度认识文化遗产的保护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贵州黎平地坪侗寨的风雨桥, 2004年曾遭遇洪水冲毁,当地侗族群众有的舍身跃入洪水中打捞,有的沿着河岸追赶,有的提着电筒彻夜搜寻,硬是从洪水中“捞”回大部分桥的构件,并将其复建起来。
当年媒体将故事阐述为“向世人展现出当地侗族群众视文物为生命的精神风貌”。对于地坪人,风雨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巨大的荣誉,反映其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但是,侗族群众的英勇举动,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风雨桥是宝贵的国家财产么?
还有一类现象,城镇乡村中,有很多老的建构筑物,目前没有各级政府任何的保护身份认定,它们曾在所处城镇乡村中充当过祠庙、乡学、防御等重要的公共服务功能,也伴随了当地几代百姓很多年的生产生活,但是今天它们散落在现代建筑为主的聚落环境中,因为没有头顶政府颁发的金字招牌,在新的建设开发面前被无助地拆除,开发者没有歉意,政府没有责任,当地百姓虽然会多少表达遗憾惋惜,但也觉得似乎理所当然,就像面对一般的危旧房、棚改区被拆除,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

遗产保护,是否只是国家或各级政府的责任?城镇乡村,是具有千百年历史的“物质空间实体”以及“社会组织单元”,它们的后人,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在那里生产生活过一定岁月的迁入者,共同形成了“社会共同体”,也就是久已有之、近年来越来
越多被提起的“社区”。这些社区及其居民,曾经是这些文化遗产真正的创造者与维护者,也一直是这些文化遗产的使用者,与这些文化遗产相伴相邻,它们是否应该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起到积极作用呢?如果没有,为什么?从国家政府的角度来讲,是否需要来自这些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如何激发这些参与?
社区在人类聚落中普遍存在。无论是在传统礼俗社会(Gemeinshaft),还是在现代法理社会(Gesellshaft),都存在社会学家F·滕尼斯所说的“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是社区。但同时,所谓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又是相对的、分层级的。具有一定历史的稳定的城镇村,都可以是地方社区,村相对于镇是地方社区,镇相对于城是地方社区,城相对于国家是地方社区,国家相对于世界也可以被理解为地方社区。社区成员可以具有多重社区属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张三是中国人,山西人,运城人,东张岳村人。
但是文化遗产在被保护管理的过程中,往往只是强调它的单一社区属性。以我国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制度为例,总体而言是国家文物局负责国保单位的保护资金与相关保护项目审批,省文物局管理省级文保,市局管理市级文保,虽然日常监管是属地管理,但职权小,责任大。因为明确划分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级别,经常会看到国保单位的保护修缮“等靠要”的情况,以及国家文物局下拨的保护经费花不出去,而很多省保、市保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的现象。

文化遗产能否同时拥有不同的社区属性?回答是肯定的,至少是有可行性。美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联邦、州、地方三个系统管理,因为联邦、州、地方均有立法权,且往往地方的管理权限更大,所以可以说联邦、州、地方是三个平行的管理体系,并不是上下层级的关系。联邦登录说明被登录的遗产对于整个国家具有价值,“为美国的漫长历史作出过贡献并与其中的历史事件相关”、“与美国的重要历史人物相关”。地方登录则说明被登录的遗产对于所在城市或社区具有价值。因此一处文化遗产是联邦的登录遗产,并不影响它同时是地方的登录遗产。
比如麻省Worchester的Massachusetts Avenue历史地区,即是联邦登录保护街区(National RegisteredDistrict),也是地方登录保护街区(Local Historic District)。这样,Massachusetts Avenue历史地区需要满足联邦和地方两方面的保护要求,也可以申请来自两方面的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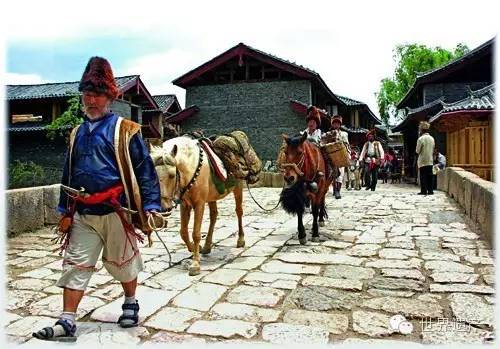
当然,中美两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差异与国家管理模式、历史成因及文化遗产总体状况相关。中国强调保护应具有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历史大视野与格局,美国则希望同时考虑国家与地方两个维度的价值取向。但对于我们而言,无论如何,强调或保证文化遗产对于当地社区的意义,保护管理对于当地社区的责任,利用对于当地社区的获益,对于自下而上地激发更广泛的保护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可能需要从以下角度加深认识或采取措施:
1. 社区角度对文化遗产认识与保护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我们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范围内街道村庄等社区的自我认同与管理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良知的基础。文化遗产,作为增强社区凝聚力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具有其他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替代的精神感召力,也是塑造具有物质与文化层面的社区特色的重要切入点。
2. 文化遗产的保护整个过程应该鼓励社区的参与。在申报与认定环节,鼓励社区参与文化遗产的申报,遗产的认定应该吸纳社区力量,被认定的遗产应该被社区代表认可并公示。即便是高级别的文化遗产,也应该让社区认识到,遗产是国家与社区共同的资源。在保护与利用环节,应该引导社区参与保护及利用,成为遗产日常的保护者与利用者,采取文化节庆等宣传手段、参与保护利用决策的管理手段、获利回补共同受益的经济手段使社区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也是社区的责任。
3. 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认同的基本载体,应该在各级政府主体认定基础上进一步向下游延伸,鼓励或允许街道乡村等社区级的遗产,通过街道条例、村规民约加以界定,明确它们的保护责任,鼓励社区的资金募捐与行动参与,同时也鼓励通过合适途径申请各级财政的帮助。
一个国家,可以有“九鼎”之类的国之重器,一个村落,可以有土地阿公与村口的大槐树,一个家庭,可以有敝帚自珍的“传家宝”。它们都很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