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
On the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作者简介】 陈星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认为,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就是指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广泛征引民族志文献,用以解释考古遗存的文化现象;二是综合考古学与民族志中的同类现象,对文化进化过程或某种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过程进行总结,从而抽象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表现在:①汉族民俗(包括文献、实物及其他遗留的文化现象)的关注;②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③对人类学一般文献(包括国内、国外、古代、现代)的征引和与考古学材料的对比分析;④对民族志类比分析方法的认识和强调。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古老而灿烂的中国文化积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在学术思想领域,尤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具有浓重的历史学倾向,以至有人宣称中国的一切学问都是历史学。这自然有些矫枉过正,但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倾向却是不可否认的。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将之名为“历史编纂学传统”,大约就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公允评价。考古学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与西方的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学传统。但是,在我们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人类学倾向。在世界考古学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这种倾向,分析它的作用和地位,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因此作者不避浅陋,提出这个问题,向考古学界的前辈和同事们求教,敬祈指正。

一 、 何谓人类学传统
人类学即“人的研究”。1501年德国人亨德(M·Hunt)在所著《高尚人类的人类学》一书中,最初使用该词的本义限制在人体构造研究的意义上。但是稍后,随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科学的发展,人类学的研究便涵盖了人的生物的(体质)和文化的两个方面。不过由于欧美各国学术传统的差异,人类学的意义及研究的范围也自不同,这种情况影响到欧美以外的其它地区。一般说来,美国的人类学由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部分组成,后者又包括民族学、语言学、史前考古学三个分支。体质人类学研究古代以至于现代人的体质,文化人类学则是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三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各有侧重,并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与美国类似的分类方法是英国。不过英国用社会人类学代替文化人类学,侧重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德国、奥地利及苏联则采取另一种分类方法,他们所谓的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文化方面的研究以民族学代之。由于民族学侧重于文化史的研究,所以史前考古学一般也包括在内。法国、荷兰、比利时采用美国的用法;欧洲其它国家则沿用德国的用法。因为日本在战前引进德奥式的思维方式,因此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通称为民族学。随着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思想的浸染,这种分野在日本日益弥合,现在则几乎可以换用了。我国的情况稍有不同。1949年以前,我国接受的人类学既有德奥式的,也有英美式的,所以当时没有哪一种分类方法一统天下。1979年以后,受苏联的影响,人类学系被取消,人类学成为体质人类学的专用名称,文化人类学归属于民族学,史前考古学则被划入大学的历史系。从此,成了三支几乎互不相关的学科。1979年以后,由于英美主要是美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相继恢复了人类学系,既开设体质人类学的课程,也讲授文化人类学的课程,呈现出与日本战后类似的情况。但是在大多数学者的心目中,人类学也就是体质人类学,所以要讲人类学,必须解释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因为德、奥、苏等国的民族学专门研究人类的文化,与英美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相对应,所以人们一般把民族学称为文化人类学;反之,所谓文化人类学一般也被认为就是民族学。但是,从纯学术的角度讲,这是不完全成立的,因为文化人类学的范围要更宽泛一些。本文所谓的人类学传统其实就是文化人类学传统,而实质则是民族学传统,也即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材料解决考古学问题的一种传统。
考古学家援用人类学文献,以解决考古学中的问题,从考古学诞生之日起就已开始。哥伦布发现美洲不久,英国学者即已把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古代的不列颠的布里吞(Britou)人相比较。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人们又从欧洲之外的民族志材料中得到启示,否定了雷斧(Cerauiles)的传说,辨认出所谓雷斧原不过是上古人类的武器和工具。十九世纪,史前考古学和民族志的材料进一步增加,一些考古学家在处理考古遗物的名称、用途、功能、制作方式及至精神层面的问题时更注重与民族志材料类比分析。1851年,英国史前学家丹尔尼·威尔逊(D·Wilson)在所著《苏格兰的考古学和史前史年鉴》一书中,在理论上强调了民族志研究对文物研究的价值。另外两位英国著名的史前学家泰勒(Tylor)和拉伯克(Lubbock),更是溶民族志与史前考古学的材料于一体,对于丰富人类的史前知识,推动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以后,由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相继形成,使原来紧密相关的学科分开了。考古学对人类学材料的援用,只停留在零星的点缀的水平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中期,美国考古学界的一批年轻人受新进化论的影响,对传统的文化史模式,即对文化遗物遗址的分类、描述和编年感到厌倦,对文化的解释、变迁而不是静态意义上的重建感到兴趣的时候,考古学和人类学才又走到一起。1961年,出现了专门讨论考古学与民族志类比的方法论的文章,标志着考古学中新的方法——民族考古学的形成。美国考古学家威利(G·Willey)和沙巴罗夫 (J·Sabloff)走得更远,他们宣称,“美国的考古学就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与以前简单援用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材料不同,许多考古学家从考古学的目的出发,深入到一些尚处在原始状态的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和记录,以期对远古人类的各个方面进行复原和解释。考古学家不再局限于对具体的物质遗存的解释,而是整体地动态地透视远古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目的是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学为考古学在理论上提供了研究人类行为的整体观和透视观,考古学家发掘的文化遗物不再是观赏的对象,而主要是那个产生了它们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通过它们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乃至思想,最后,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目的是了解世界各地区的人们在不同时空中应用不同方法解决类似问题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家才成为人类学家,这是与以前零星援用民族志材料所根本不同的。
利用人类学文献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在西方或者称为“民族考古学”,或者称为“活的考古学”(Living Archaeology)。这固然强调了不同于传统考古学的新的研究方法,但是其实质却仍然是考古学与人类学材料怎样结合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张光直专门写过“考古学与民族学内在联系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文,另有 “考古学的人类学”, “考古学家的人类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等不同说法,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人类学材料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一般认为,下列几种著作标志着重视人类学文献的新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成立。
其一是1966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林厄姆·克拉克(G·Clark)发表的《石斧及石锛的贸易》一文。克拉克在过去也曾零星地援用过民族志材料,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讨论了民族志的运用,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民族志 ,把民族志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整体地考察了原始社会的石斧贸易,包括石斧的生产、流通、分配等方面的情况。该文被视为新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转折点。
其二是1968年由李(Lee·R·B)和德沃尔(I·Deoyre)主编的《人——狩猎者》。这本论文集收集了大量的现代狩猎民族的材料,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问题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李等人对非洲布须曼人的狩猎采集生活的研究,对于了解旧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特征具有开拓性意义。
其三是1969年由乌斯克(Ucko)和地木布里贝(Dimbleby)主编的《动植物的驯化与利用》一书。该书主要讨论从狩猎向农业的转化原因、时间、地点、方式等问题。这本来是一个考古学的问题,但是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动植物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参加了讨论。研究视野的拓宽,不仅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而且对考古学其它问题的解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入手。综观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将之大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具体问题的研究。广泛征引民族志文献,用以解释考古遗存的文化现象。第二是综合考古学与民族志中的同类现象,对文化进化过程或某种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过程进行总结,从而抽象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对人类学和社会文化进化的一般理论作出贡献。

二、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
中国现代考古学从1921年安特生(J·G·Andersson)发掘辽宁锦西沙锅屯和河南渑池仰韶村始,至今已经70周年了。这期间虽然历史学传统占据优势,但利用民族志文献以解决考古学问题的人类学传统却也涓涓不断而且呈现出日益壮大的趋势。考古学家的人类学传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汉族民俗(包括文献、实物及其他遗留的文化现象)的关注。
考古学家的一切工作以解决问题为旨趣。因此,只要是可以利用的材料,就可以拿来利用。1921年安特生发掘出中国第一个史前的村落遗址——河南仰韶村遗址。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刚刚萌芽,能够参照对比的资料苦少,安特生为了确定仰韶遗址的年代、文化的属性以及遗物的功能,特别注意收集汉族的历史文物及现代的民俗遗物,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便是将这些资料与仰韶遗物类比分析得出的。
半月形石刀和长方形石刀是中国史前时代的典型器物。1915年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在《南满远古人种考》一书中即有记述。1920年安特生在华北旅行,发现北方农民所用割高梁的刀(统称铚镰)也有长方形和半月形的,也都有两个穿孔,刀背上还包裹着皮或布,有绳子穿过两孔结成绳套, 以备使用时缚在手上。安氏认为这就是中国史前遗物的孑遗,所以购买了很多种类型的铁镰,作为研究时的参考。安特生又发现北京街头的磨刀人把四个有刃的石刀绑在一起,晃动起来清脆有声——称为铁滑链——以此用做磨刀人的招牌。磨刀人已经不知道何以把四个石板的一面磨成刃状的缘由,但是安特生由此推断,这就是上古石刀的遗留。安氏由此受到启发,又注意调查了中国北方农民的其它工具,如锛、凿、钻;他又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物比如铜戈和金文中的戈的各种用法,推断石铸和石斧的安柄方式和使用方式。从周代的铜鬲以及金文中的鬲字与仰韶村所出陶鬲(安特生误以为是仰韶文化遗物)的相似,陶鼎与北京所用铜锅的相似等等,判断仰韶文化的性质和年代。正是基于这种发现,安特生才敢把仰韶村的文化遗物名之为 “中华远古之文化”。这种以历史文物或民俗追溯史前时代历史的方法被西方人称为民族史方法,在研究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三洲那些具有文化连续性及保留有相当古代文化传统的地区史前文化时尤其富于成效。
由安特生开创的这一传统,被我国考古学家继承了下来。如石璋如就曾专门调查过酒泉的制玉工艺,著有《酒泉的制玉工业》,又曾对昆明的制铜工艺做过调查。梁思永在抗战前调查过北京的制玉技术; 郭宝钧专门调查过河北磁县的瓷业,并著有《磁县瓷业调查记》。虽然中国现代社会发生了剧变,一些原始的文化尤其是物质方面的文化趋于消失,但是仔细调查农村的婚丧风俗,一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一些原始工艺如制陶、制玉、建筑等等,仍能对考古文化现象的解释和复原 作出积极的贡献,所以仍是我们考古学家需要加以注意的对象。至于以汉语的文献及历史时代的文物制度论证史前的文化现象,则更是为考古学家所常用,这个领域的工作有必要上升到理论高度,需要更深一层的开掘。

(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
早在本世纪上半叶,一些著名的民族学家就曾深入到我国西南、东北、台湾、两广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涉及的面非常之广,因而为考古家的类比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材料。抗战期间,前中央研究院转移到西南大后方,也曾有考古学家对当时的民俗文物制度作过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调查报告。除此之外,一些大学和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也曾多次组织调查团深入民族地区,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参与这些调查的也有一些考古工作者,由于他们与一般的历史学者和民族学者兴趣不同,出发点也不同,后来都从考古的角度出发,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在这方面贡献较大的如冯汉骥、梁钊韬、汪宁生、童恩正、宋兆麟、李仰松等,除了利用一般的人类学材料对考古遗物的用途、使用方法等进行解释和复原外,还有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的综合研究。如汪宁生的《傣族的原始制陶术——兼谈中国远古制陶的几个问题》、《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法——兼谈中国古代取火》、《云南永胜县他鲁人的羊骨卜——附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 、《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习俗》、《纳西族的仪式用木牌和汉代烽隧遗址出土的人面木牌》等一系列论文,都是从考古学的目的出发,有意识地调查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类似文化现象, 从而对考古学中的制陶、取火方式、占卜及汉代烽隧出上的人面木牌等问题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解释。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比如石璋如到台湾后也非常重视对台湾民间和高山族的风俗进行调查。石璋如还专门著有《瑞岩民族学初步调查报告》(合著)、《杨梅的砖瓦业》、《莺歌的陶瓷业》、《杨梅土葬三步骤》等多篇调查报告。这种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调查现代活体民族的材料,最后又回到考古学中去的方法,是所谓正宗的民族考古学。由考古学家执行的民族学调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调查者对被调查的对象的一系列行为特征做过详细的观察和记录,所以往往能为被解释或待复原的考古现象寻找到一种贴切的解释和复原模式,在实物与行为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比如上述汪宁生用纳西族仪式用木牌对汉代烽隧的人面木牌的解释,用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对古代占卜习俗的解释,就不仅为考古遗物的用途寻找到一种解释的方式,而且也为理解古代人们在从事这项活动时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模式,为我们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开辟了道路。
民族地区的考古研究往往也要借助于与当地民族志的类比分析,这也属于民族史方法的一部分。在这方面的工作,比如童恩正、汪宁生等对西南地区铜鼓的研究,冯汉骥等对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的研究,宋兆麟等对左江岩画的研究, 都是在广泛调查当地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精细的类比分析完成的。由于地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再加上共同的地理和经济背景,所以尽管已有变化,却仍能在古代与现在之间找到许多共同或共通的东西。这种具有相似的生态背景、技术背景、经济背景甚至历史背景的古今民族文化的对比,既使是最谨慎的学者也持肯定的态度。张光直先生将之称为“直接历史方法”(Historic App-roach)。这种方法在中国民族地区的考古中尤其具有优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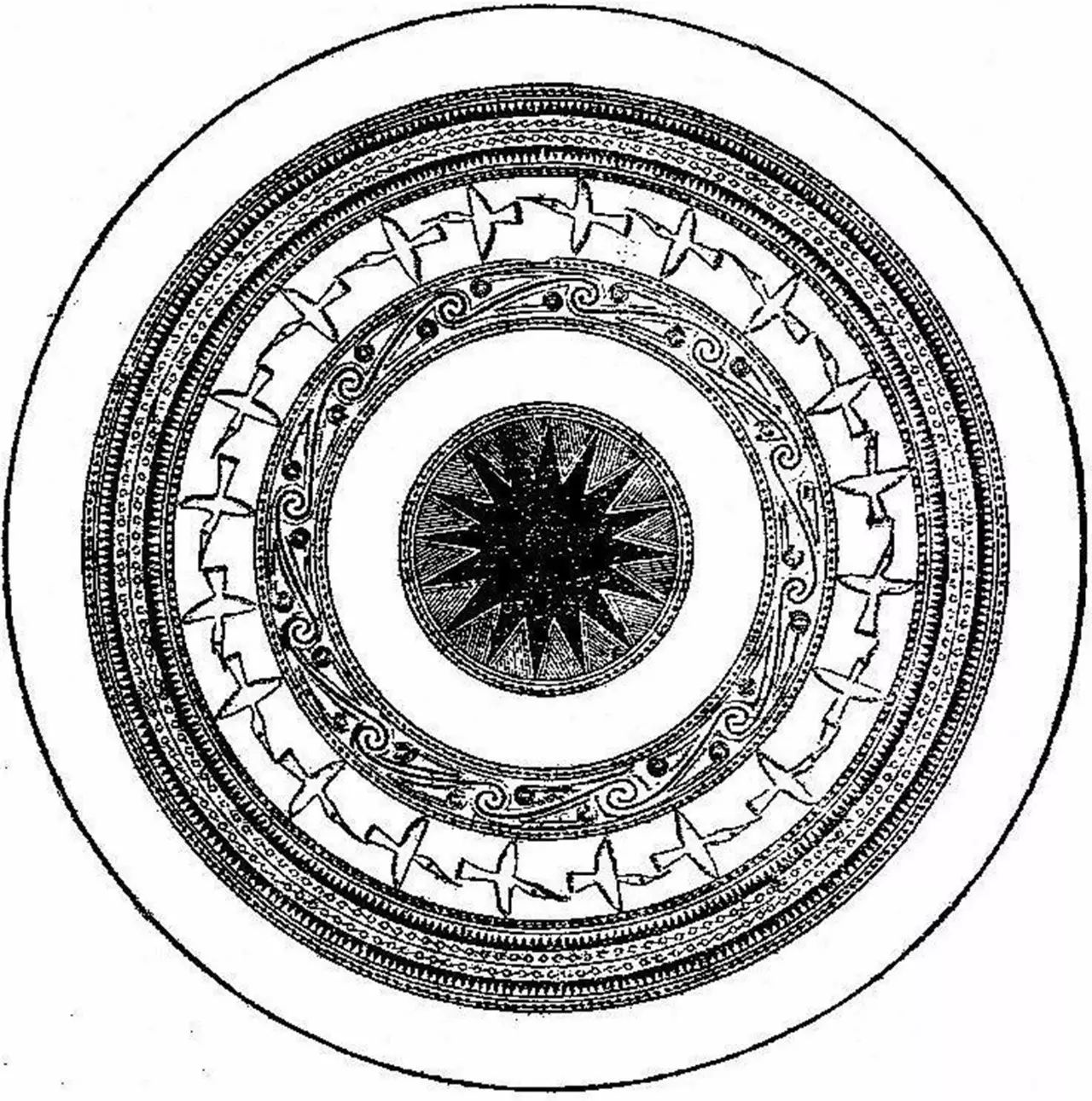
(三)对人类学一般文献(包括国内、国外、古代、现代)的征引和与考古学材料的对比分析。
考古遗物遗址是古代社会的遗存,要寻找它们的解释和复原,如果没有文字的证明,就必须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因此一般考古学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家都非常注意运用民族志中的材料来复原和解释考古现象。大部分考古学家只是为了解决某一个考古学问题。而寻找零星的民族志方面的佐证,也有一些引用了大量的民族志对比材料,材料的来源十分广泛,古今中外皆有引证。如高去寻写作的《黄河下游的屈肢葬问题》在详细描述了中国黄河下游从史前到春秋战国的屈肢葬后,又征引了世界各地的屈肢葬风俗,对屈肢葬的意义进行了推测。李济的《跪坐蹲居与箕距——殷墟石刻研究之一》 广泛收集了世界古今民族志的材料,对商代出土石刻的蹲居形象进行了解释。六十年代关于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论战,七十年代关于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讨论;八十年代日益兴盛的专题研究,比如关于史前埋葬制度、居住习俗、宗教艺术遗物等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应用了民族志的对比材料,虽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把考古学材料同民族志材料结合起来,从而为解释人类某种共同的文化现象如原始文字的起源,为解决人类文化进化的一般法则比如东西方不同的演进模式,则更是溶人类学的理论和材料于考古学中,将考古学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前者如汪宁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就是先叙述了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原始记事方法,再结合中国考古发现和古文献中所见的原始记事方法,最后为文字的发明提出了几种可能途径。另一篇《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也采取了类似的论证方式,为度量衡制度的形成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凌纯声早年关于宗庙、社稷、酒、玉石礼器以及猪头方面的考证,也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典范。后一种是将考古学材料放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对人类进化的阶段或模式提出规律性的认识。比如李济研究商文化就把商文化放在整个太平洋的文化圈中考察,凌纯声考察中国文化也具有人类学家的整体观,把中国文化放在东亚乃至整个太平洋区域的背景下,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近年来,张光直更提出考古学家应该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做出贡献,他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人类学与考古学资料的类比分析,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法则是世界式的,即连续的,与西方式的突破性的文明产生法截然有别。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将中国置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而且也为考古学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任务。

(四)对民族志类比分析方法的认识和强调
中国的考古学家无论是所谓历史学派的或是人类学派的,大都认识到人类学的即民族志类比分析的重要性。人类学出身的李济一生都在强调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古史。 早在1923年他发表在《哈佛毕业杂志》上的《中国的一些人类学问题》一文就指出,目前需要进行人类学工作,包括考古调查,民族志调查、人类体质的调查以及中国语言研究四个部分。在他的晚年,他更强调整体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梁思永也认识到,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在民间手工艺的技术入手。吴金鼎更明确指出,要了解古代陶器的技术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所谓的实验,二是与现代制陶术进行比较。尹达也曾十分强调考古学与民族志材料的结合,他早年撰写的《中国原始社会》、《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都运用了古代的或今天的体质人类学的和民族志的材料,不仅如此,在晚年他更指出“希望着我们的史前考古学者、民族学者、古史学者密切配合,从各个角度深入探索下去,使祖国有文字以前的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再现于世。” 夏鼐一生谨慎为学,他所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使他很少运用民族志类比分析的手段,对考古学界影响很大。但是在晚年他给汪宁生的信中也承认“利用民族材料以研究考古学上的问题,为一很有前途的途径”。关于民族志材料的重要性,历史学家范文澜形象地指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和种种法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八十年代中期,关于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无论如何,争论双方都认为民族志的类比分析,可以为考古学做出积极的贡献。近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使更多的考古学者注意到用人类学的材料和方法研究问题,一些前人未曾触及的新问题正由于这种新的方法和材料的运用而逐步得到解决,呈现出可喜的局面。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编辑说明:篇幅原因,注释从简。
文章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编 辑:高朋 李联廉
助 理:张智林 李宗朋
您的稿件和服务意见请发往"民族学与人类学"微电子杂志服务邮箱:
mzxyrlx@126.com
您的支持和鞭策将会是我们进步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