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燕海鸣: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命景观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和海洋相关的生命历程的集合,是围绕海洋、港口、船舶、货物的“海洋栖居者”通过行动交织而成的生命景观。本文以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远航者的生命体验为脉络,聚焦唐代广州城和“黑石号”沉船为代表的相关海丝遗存,通过挖掘海洋栖居者的生活世界,将生命景观与文化遗产交织串联,提出挖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的新路径。作者认为,崇高雄伟的文化遗产,首先是有血有肉的生命经验和情感的产物。文化遗产在人的生活中诞生,也只有回归生活视角本身,才能洞见那些宏大叙事之下的生命活力。

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命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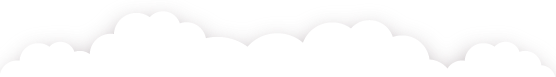


在构建国家和民族大历史叙事时,我们往往通过辨识度高、简单明晰的名词,将复杂的历史遗产的意义高度凝练。比如丝绸之路、大运河,这些概念早已和民族情感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历程中最典型的面貌。而揭示文化遗产崇高的意义,则有助于聚焦其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一面。
不过,仅强调文化遗产的崇高性,难免令其形象单薄,和人们生活相疏离。崇高的意义需要通过价值来支撑。周孟圆和杜晓帆提出,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人的行动中产生。文化遗产拥有多重、多维度的价值,遗产的意义蕴含在这些层层叠叠的历史信息之中。认识文化遗产,不仅要建立起宏大的家国情怀,也要激发个体身心的共鸣。崇高雄伟的建筑和遗址,首先是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历程中的经验和情感的产物。文化遗产在人的生活中诞生,也只有回归生活视角本身,才能洞见那些宏大叙事之下真正的生命活力。
因此,要在“意义”之中发现“多重价值”,需要回到那些真正创造这些遗产、生活在其诞生发展历程中的人的身上,走入他们的脑海和心灵,感受他们的情绪。我们可以追问:如果换作是我,在同样的情境下,会做出怎样的行动和抉择?这种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对于那些跨越空间、体系复杂的文化线路类遗产而言尤为重要。文化线路遗产面临遗产点分散,互相之间较难建立关联的困境。要让零散的遗产要素交织互动,需要发现和描绘生活在当时、当地的人的生活状态、行动轨迹乃至精神世界。
本文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探寻蕴含在宏大叙事之中的生命景观。魏峻曾对近年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内外考古研究进行全面综述,发现在传统的沉船考古、货物研究之外,也展现出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视角的转向,开始较多关注海洋相关的社群。本文采取从宏观到微观逐步聚焦的方式,首先回顾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叙事。其后,文章将“俯瞰”转换为“平视”视角,挖掘海洋栖居者的生活世界,将历史上来往于中国南海的个体经历铺展描绘,并将这些海洋栖居者的生命景观与广州的海丝文化遗存串联交织。笔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围绕海洋、港口、船舶、货物的“海洋栖居者”通过行动交织而成的生命景观,而这条文化线路上的文化遗产,是古代人们和海洋相关的生命历程的集合。倘若没有这些生命,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便没有了“主语”。
本文在既有材料基础上,以文化遗产价值研究为切入视角,尝试提出的思路,既能够丰富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内涵,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案例提出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新路径。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线路,在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文本团队尝试从宏观视角提出其定义,称:“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主要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路网络,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相互传输的纽带。”在空间范畴,海上丝绸之路映射着一套世界体系,可以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和地中海等板块,是由连接各港口的航线交织而形成的海路网络。一些重要港口及其所连接的区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文化、技术交流的核心地区,可以称为“交流活跃区”。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多样的沿海文化特征。在构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体系时,申遗文本团队根据地理区位,将其细分为四个主要交流活跃区——黄渤海、长江流域、东海及台湾海峡、南海。每个交流活跃区都对应一个概括性的特征,比如南海交流活跃区直接面向东南亚,是海丝在中国持续不断产生重要影响的见证,外来宗教文化从海路传入中国的首要节点。
每当我们打开一幅描绘海上丝绸之路的示意图,映入眼帘的都是世界著名港口以及将其串联起来的线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关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示意图,用线条表示路径,表现古代世界相互连通的状态。但这种图像容易造成一种知识上的假象,即古代世界不同文明和人群之间的交往是畅通便利的,甚至两个遥远的港口之间是直接连通的。标准化的港口和线路标识,让观者很难想象出那些远航者真实的生命体验。
如果回归古代海上世界的原貌,海上丝绸之路则绝然不是平稳的线条,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交错互动的场域,是充满随机和不确定的生活世界。当我们在描述一个庞大的文化遗产时,往往会淡化或虚化存在其间的行动者。群像式的概述和抽象性的定义固然必要,但仍是一种俯瞰的视角,忽视了人的行动的复杂多样。在描绘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和文化时,我们也需要追问——“主语”在哪里?那些跨越大洋的人到底是谁,因为什么动机,在什么情境下进行的航海行动?要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下,理解从事海洋相关的生产和生活的主体——往来的商贾、朝觐的僧侣、出使的官吏、奔波的水手。他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语”,也是让这一文化线路遗产拥有血肉和灵魂的要素。
海上丝绸之路的远航可视为一种栖居方式,它是由一个又一个“关节“组成的生命历程。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人生命历程可归结为周而复始的“过日子”,“逢年逢节大多希望如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般又轻快又不留恋地度过了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命”。对于远航于茫茫大海的人们来说,最重要的“过渡仪式”是一次又一次的海上风险;而两次风险间的海上生活,则勾勒出一个微观但完整的生活形态。
(一) 海洋生命景观——风浪、星辰、远航人
古代文献中关于海上遇险的记录有很多。法显所撰《佛国记》详细描述了他从印度回中国过程中的两次险情。第一次是从师子国至耶婆提的路途中,“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弥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第二次是从耶婆提返回国内的途中,遇到黑风暴雨,船上的婆罗门认为法显是不祥之人,差点把他抛弃在海岛上。最终,这条本来要在广州登陆的船绕到今天山东崂山一带才靠岸。日本来华的圆仁和尚在黄海也有类似的经历:“乍惊落帆,桅角摧折两度。东西之波互冲倾舶,桅叶海底,舶橹将破,仍截桅弃柁,舶即随涛漂荡。......船上一众,凭归佛神,莫不誓祈,人人失谋。”阿拉伯来华商人苏莱曼也曾描述海中的风浪:“若然遭到了一种风,海水就立时翻腾起来,像锅子里沸着的水一样。”
虽然狂风骤雨对航行带来危险,但更大的危险则是水下的暗礁。《佛国记》提到“若值伏石,则无活路”。暴风雨虽然可怕,但还可有序补救,而如果撞上礁石,那就是死路一条。宋代《萍洲可谈》谈到的海中险情以礁石为最。“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如果遇到这番情形,不能从船中去补漏,而是让善于游泳的东南亚“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除了搁浅之外,《萍洲可谈》还提及了海中巨型生物的危害,“锯鲨长百十丈,鼻骨如锯,遇舶船,横截断之如拉朽尔”。可见,除了祈祷顺风相送、海不扬波之外,躲避海面之下的隐患,是更让远航者提心吊胆的“劫点”。
海上远航者的心理状态,就如同在晴空万里中忧惧暴风骤雨,每一次雨过天晴,都是一次“过日子”的完成时刻。正如法显所写:“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从暗夜大浪中的不知哪向,到天晴后的望正而进,就是周而复始的海上“日子”。
期待晴空万里,不仅是平稳航行的需要,更是海中定位和导航的必须。远航者的生命很大程度寄托于日月星辰。《佛国记》记载,即使不是狂风暴雨,哪怕只是阴天,导航系统就会出现问题。“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而归国那一段旅程之所以偏航,也是因为阴天所致,“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可见,当时的导航技术完全依赖于天文知识。到了宋代,天文导航已经可以用指南针来配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确定方位,“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这种方法和常见于描述古代阿拉伯船的西方文献所说的“测深锤”(lead sounding weights)类似。海上航行最关键的技术之一是能够准确对当下的位置进行定位,而这一技术最大的限制就是天气本身。因此,如果我们进入古代航海者的生命,能在夜晚看到漫天繁星,对他们的意义绝不只是浩瀚宇宙带来的心灵冲击,而是意味着生命的平安。
这些关于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上的经历,在阿拉伯的航海文献中也有丰富多彩的记载。一部名叫《印度奇观》的著作收集了很多关乎航海人的有趣故事和经历。据信该书完成于10世纪中期,汇聚了这一时期发生在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广袤海洋区域的奇闻轶事,其中也少不了海难的场景。
公元936年,一艘船被风浪直接摧毁,目击者说:“我看到它被风浪推向暗礁,翻倒了。我看到货物和人们从暗礁的顶端被抛入海中。船被吞没,没有人幸免于难。”还有人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海难,这是一只由三艘船组成的船队,从波斯湾的尸罗夫(Siraf)出发,一共搭载1200人,有商贾、船主、水手等,就当他们即将抵达目的地塞米尔(Saymur)时,“风向改变,从山上吹向我们。突然间,一场狂风袭来,伴随着闪电、雷声和大雨。帆无法收拢,狂风卷走了我们”。最终,只有讲述者等几个人因为登上了逃生小船而获救,其他人都命丧大海——包括一位宁可和船一起沉没也不愿意逃生的船主。
对于天文等自然条件因素,人力虽然无法掌控,但人和自然之间还是可以实现“沟通”的,沟通方法就是祭祀。出发前在特定空间进行祈祷仪式,是所有远航者必须开展的活动。比如在广州,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都是重要的祭祀祈风场所。在茫茫大海上航行,船上一般要配备掌握祭祀技能的人员。比如商船中一般会带上佛僧:“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至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随船的祈祷也不是必须宗教人士才能开展,圆仁曾记载:“舶上官人,为息逆风,同共发愿,祈乞顺风。”遇到雷电时,“北方有雷声,掣云鸣来。舶上官人惊怕殊甚,犹疑冥神不和之相,同共发愿兼解除,祈祠船上霹雳神,又祭船上住吉大神,又为本国八幡等大神及海龙王,并登州诸山岛神等,各发誓愿”。
面对风浪和天空,《印度奇观》中也讲述了充满经验的海上智者,描绘他们如何对自然景观了如指掌。一位船长教育他的水手,要判断附近是否有岛屿或山脉,最佳的观测时刻是下午的礼拜结束、太阳即将落山之时,“如果处于陆地或山的对面,会很清晰地看到它”。这些充满智慧的船长面对突变天气时显得游刃有余。其中最神奇的是一名经常往返中国的阿巴拉船长(Abhara),他曾帮助一艘遇险的阿拉伯商船,准确预测了即将到来的险情,凭一己之力拯救了整艘船命运。当被问到为什么能够把海上风险预判的如此准确,他回答:
当我遇见你们的时候,是在[阴历月]第30天的高潮,但潮水已经下降了很多。我和之前其他人曾穿行过那片海域。我们注意到每个阴历月的第30天,水位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下降,以至于裸露出这些岩石。与此同时,一场猛烈的大风从深处袭来。我所乘坐的船只就曾在这些岩石中遇险,因为当我们在礁顶度过夜晚时,正值低潮,我在这艘船的小艇上幸存了下来。
这种对于大海“习性”的描述,以及基于种种经历和知识基础上的具体行动,在中文文献中相对少见,《萍洲可谈》中提到过的“舟师识地理”,论及的是同样的内容,可惜没有展开讨论这些舟师如何“识”地理。《印度奇谈》这类同时代的外文文献很好地补充了这个空白,也让我们对远航人的日常行动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熟练的航海者还有一种铭刻在身体中的“海上直觉”。迪奥尼修斯·阿久斯(Dionisius Agius)曾整理了航行于红海的阿拉伯帆船上人们的口述史。虽然这些信息年代大约是18世纪,但仍能够让读者想象一千多年前的航海体验。这些航海者拥有对于沿海地貌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经验教会了他们计算距离和最佳离港时间。一位名叫阿里·阿尔加班(Ali AlGhabban)的船长回忆其祖父和父亲的经历,表示经验丰富的航海者会培养一种“海上直觉”(sea sense),他说:“船长非常了解海洋。他熟悉航线、珊瑚礁通道,但最重要的是他了解风向,知道何时出发是正确的时机。”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生命景观,是船上的人与风雨、海水、星辰之间的互动,是人的生命在凶险自然景观之下实现一次次“过渡仪式”的总和。但是,只要是人的行动,就会有误差。Eric Staples曾尝试在现代帆船“马斯喀特珍珠号”(Jewel of Muscat)上使用古老的牵星过洋技术,但是他发现,不同的人在同时同一地点的测星数据会不尽相同,导致对位置的判断出现不确定性。古代船只上在进行“牵星过洋”时,测量失准很可能是一种常态。因此,即使日月星辰保障了天时和地利,“人和”恐怕也是海丝生命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航行在海上的帆船之中,每个生命除了要面对自然因素带来的挑战,还要进入一个微观而完整的生活世界。下一节,我们将以唐代沉船“黑石号”为切入,窥测远航者的船上社会生活。
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掘出了一艘沉船,因附近有一块黑礁石被命名为“黑石号”,又称“勿里洞号”(Belitung)。根据一件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落款的长沙窑瓷器,可推断沉船发生时间约在唐宝历二年(826)后的几年之间。根据船只的结构和材料,可推断黑石号是一艘阿拉伯制造船,全长达18-22米左右,宽度为7-8米。Natalie Pearson认为,黑石号能够同时承载的人数不超过20人。该船共出水文物近7万件,最大宗为陶瓷器,其中长沙窑的瓷器超过59000多件。总之,这是一艘阿拉伯的缝合帆船,满载着中国唐代的商品,自中国的广州或扬州出发,行驶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古代贸易通道上,没有抵达目的地便不幸沉没。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的《唐代沉船——九世纪的艺术与交往》一书,对黑石号上文物所见证的船上生活有过详细描述。船体中发现的研钵、研杵和擀面杖等工具应该是准备食物之用,大桶用来存储淡水,铅质的渔网坠表明船员们捕鱼以获取食物。还有针和木棍,推测是用来缝帆和渔网的工具。“在沉船中找到的一个中国砚台几乎可以确定属于一个有文化的中国商人。用于准备茶的陶瓷研磨器也可能是船上的一个中国人所拥有的。”船上还发现了一颗骨骰子,应该是船员们玩游戏或是赌博用的。
上述文物看似可以呈现出一个其乐融融的船上世界,但实际情形可能要复杂得多。首先,黑石号上的航海者很有可能是一个多族群、多语言的社会形态。Natalie Pearson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个多样化的船员组: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并来自四面八方。”吴小平则根据出水的几件提梁壶和釜之类的陶器,判断其使用者应该是岭南南部的俚人,并据此推断黑石号上有部分船员为善于航海的俚人。
文欣在观察五代至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使团的人员构成后发现,这种多族群、多语言的大型团队,是穿越沙漠的丝绸之路外交行旅的常态,这样的团队需要高度有序的管理指挥系统。海上丝绸之路远航船上的社会生态也非常符合这一特点。这就导致每一次航行除了面临自然挑战之外,还有社会互动的事务要处理。如果是一个阿拉伯船,上面很可能有阿拉伯或波斯的商人或其代理,有熟悉当地海域的东南亚船长和水手,有搭乘船只的旅客、僧侣。这个小社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或许会爆发分歧甚至冲突。甚至也有可能在一个人病倒之时,船上其他人为了防患未然,在其还有生命迹象的时候就把他抛进大海喂鱼,“舟人病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气未绝便卷以重席,投水中”。
海上航行生活时刻面临社会压力,船上也有非常严格的制度以应对风险。以分配淡水为例,《佛国记》记录了法显等人迷途日久、缺少淡水补给时的情形:“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以水仓水充舶上人:官人已下,每人日二升;傔从已下水手已上,日每人一升半。”过了两天,又改为每人每日分得水一升。18世纪时,红海阿拉伯船上淡水的定量配给方式依旧如此,“在炎热而潮湿的日子,配给变得非常艰难,船员们因为强壮且习惯了这种情况而可以应对。但也听说过作弊的现象,特别是在非常炎热的航行中,绝望感加剧时,船员和/或乘客之间可能发生争吵。在这种时刻,船长通常会寻找一个锚地,指示船员从井中取水......有时,船长被迫与当地的贝都因部落进行贸易,用一些货物换取水源”。可见,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生存物资的分配是极为严格的事务。
《伊本·白图泰游记》曾记载,前往中国的船只上有六百名船员,四百名武装人员。这一描述和哈桑·哈里莱所分析出阿拉伯远航船的构成基本相同,后者包括船主代表、船长、首席领航员、记录员、武装人员、舵手、船首水手、瞭望员、船上木匠、厨师、公共奴隶或仆人、乘客等人。黑石号没有这么多人员,但同样需要有序管理,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性很高的船长,甚至要具备一定的“卡里斯玛”特质。上文提到的船长阿巴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最初是沙漠中的牧羊人,后来成了渔夫,进而成为远航印度的水手。接着他登上了一艘中国船,再后来他成了船长,在海上穿梭往来。”此人最大伟大的壮举是七次航行到中国。“如果一个人抵达中国而没有在中途死去,那已经是个奇迹。平安无事地返回更是闻所未闻。除了他之外,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人能够完成两次往返而不出意外。”
除了介绍阿巴拉船长出色的能力之外,这段故事还介绍了他“强势”的一面。在营救遇险船只的时候,他的第一要求是获得支配对方的绝对权威:“我只会以具有充分权力的船长身份登上你的船。”上船后,阿巴拉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原来的船长支开,占据了船长的舱位。随后,他行使绝对的权力,让船上所有人听他的号令行动——扔掉负重、砍断主桅杆、切断大锚的缆绳......等等。最终,这些决策都被迅速执行,而且事后证明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保障了船只在风浪中的平安。这则故事一方面表现出海上丝绸之路上杰出的航海智慧,同时也凸显了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船上领袖在如社会般复杂的船上生活领域的重要性。
简而言之,面对自然和生活的挑战,具有权威和魅力的船长、拥有船只和货物的商贾、掌握生存核心技能的船员、能够与神明沟通的僧侣,在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形成了牢不可催的命运共同体。他们之间互相依靠,等级明晰,分工有序,共同面对不确定的海洋行旅,共同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危险甚至死亡。跨越大洋船只上的人们,是一群以远航为栖居形态的生命体。他们每天所经历的星辰大海、狂风骤雨、人伦关系、生死存亡,他们眼睛看到的蔚蓝世界,身体体验的颠沛流离,心灵祈祷的神明庇佑,共同交织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命景观。那么,这种海上的生命景观,如何能够与留存在岸边的文化遗产价值发生关联?下面一节,我们将以唐代两名远航者的行旅记录为线索,以广州城的海丝文化遗产为切入,尝试构建人的海上生命历程与文化遗产的有机关联。
建城至今2000多年,广州一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和商业都会闻名于世。《唐大和尚东征传》曾记载,天宝九载(750),鉴真和尚期待东渡日本时,并没有在广州找到去日本的船,反而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甚至因此动了舍日本去印度的想法。各国来华客商在城西聚居,形成了“蕃坊”。朝廷在这里专门设置市舶使负责管理海外交通和贸易。苏莱曼的东游见闻记录“汉府城是(中外)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中国商货和阿拉伯商货所荟萃的地方”。这里所记录的汉府普遍被认为指的就是广州。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众多,其中三处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海神庙遗址、光孝寺、怀圣寺。南海神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地处城区以东的珠江北岸,唐代时为广州外港“扶胥港”,是船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这里长期作为祭祀南海神的主要场所,是中国沿海历史最悠久的海神祠。光孝寺始于三国时期。公元5-6世纪前后,罽宾国和印度的高僧先后泛海来到广州,并在此兴建佛殿,弘扬佛法,禅宗初祖达摩也曾驻锡于此。作为中国沿海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光孝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现了佛教沿海路传至中国并实现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怀圣寺处于广州唐宋“蕃坊”的中心区域,创建于唐代,被认为是由早期来华传教的伊斯兰先贤宛葛素与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共同修建。唐朝时,怀圣寺西侧为珠江在城内的支流——西澳水道,设有专门的蕃舶码头区。作为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见证了伊斯兰教沿海上丝绸之路初传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互动、融合的历史过程。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点,这三处文化遗产各自有其独立的历史脉络,但其之间的关系仍缺乏更具细节的联结。下面,我们引入人的变量——将海丝的远航者串联其中,以真实历史人物的生活轨迹,构筑其海洋、港口、人物之间的生命网络,呈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蕴含的价值。僧人义净和宦官杨良瑶都是唐朝时期曾沿海上丝绸之路远航的实践者,其行动轨迹和远航经历可以将海洋与广州城内文化遗产串联起来。
1.义净
义净生于唐贞观九年(635),咸亨二年(671)秋天,他从广州出发,搭乘波斯商船踏上赴印度取经之路。其间他在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岛东部)停留半年学习佛学和梵语,随后在室利佛逝王室资助下搭乘“王舶”,途径末罗瑜、羯荼等地,在印度东部港口耽摩立底登岸,最终在上元二年(675)抵达佛教圣地那烂陀。义净在印度求学十年,于武周垂拱元年(685)原路返程,但在抵达室利佛逝后,义净长期在此停留,翻译佛经。其间,义净往返过广州一次,即永昌元年(689)七月随商船回到广州,招募了四位可以作为帮手的僧人,并一同在当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最终,义净于证圣元年(695)在广州登岸归国,当年夏天回到洛阳,受到武则天的盛大欢迎。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义净的远航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关系。第一是路线选择。义净选择海路的原因是其时海路航行体系已经成熟;室利佛逝作为佛教在东南亚的中心是非常可靠的中转站;义净在扬州时遇到一位正好要南下广州的冯姓官员,获得了他的慷慨资助。这一系列因素使得海路在技术和后勤保障方面都更有优势。
第二是其在海上的经历。义净曾对穿越大海的艰辛进行过描述:“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他还记录了僧友命丧大海的故事:一位法名常愍的禅师和义净选择相同的海路,“忽起沧波,不经半日,遂便沉没”。商人纷纷抢上小船逃生,常愍禅师却选择了与大船同沉:“当没之时,商人争上小舶,互相战斗......常愍曰:‘可载余人,我不去也!......’于是合掌西方,称弥陀佛。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面对这些航路上的坎坷,义净感叹求佛之旅“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
第三是义净的行动轨迹和广州的联系。首先是光孝寺,义净在中途往返广州招募随行者的活动开展地就是制旨寺(今光孝寺):“于时在制旨寺,处众嗟曰:‘本行西国,有望流通,回住海南,经本尚阙。所将三藏五十余万颂,并在佛逝国,事须覆往。既而年余五十,重越沧波。’”光孝寺始终是唐代广州最重要的佛教寺庙,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在当时的大云寺(光孝寺)甚至动了从海路往印度的想法。另外,义净第一次远航“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这次“期会”很可能发生在广州城西的蕃人聚居地。开元年间《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记载:“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府洞开。”虽不能确认义净的时代蕃坊已经成型,但此区域属蕃商云集场所是明确的。可与《旧唐书·王方庆传》对照,王方庆“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根据“则天临朝”判断,王方庆在广州主政之时正和义净从室利佛逝和广州之间往返的阶段重合。同时,活动在这一区域,义净也必然会看到已经建成的怀圣寺。除了上述有明确记载的内容之外,我们还可以推测,义净所乘船只很可能如黑石号一样装载了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并配备有波斯和东南亚的水手。离开广州前,这艘波斯商船的船主或许也在还没有翻新的南海神庙进行了祭祀。
2.杨良瑶
杨良瑶是中唐时期的一位宦官。根据陕西泾阳《杨良瑶神道碑》记录,杨良瑶于贞元元年(785)受委派从广州出发出访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并在贞元三年(787)回到长安。这一段文字抄录如下:
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
杨良瑶出行的线路或许参考了杜环所撰《经行记》的内容。杜环于天宝十载(751)的怛罗斯之战中被阿拉伯俘虏,游历阿拉伯世界多年后,在宝应元年(762)乘坐商船从阿拉伯回到广州,将游历故事写成《经行记》,部分内容由其族叔杜佑收录于《通典》。虽不能证实杨良瑶与杜环直接见过面,但杨良瑶在广州准备出航时,担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的正是杜佑。两人应对远航线路和方式有过交流。
杨良瑶回国后不久,宰相贾耽完成了《皇华四达记》,共列出了七条中国通往国外的线路,其中便有“广州通海夷道”,描述了从广州到今天巴格达的海上路线。根据《旧唐书·贾耽传》介绍,贾耽对地理非常感兴趣,“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根据荣新江先生推测,贾耽和杨良瑶本人可能有过交往,广州通海夷道的内容很可能参考了杨良瑶的经历。同时,作为和杜佑同朝为官的贾耽,对于杜环《经行记》之中的内容应该也有了解。
关于杨良瑶远航时的生命经历。神道碑中明确提及了出发前祭祀的情景,“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剪掉自己的头发进行祭祀,在《萍洲可谈》中也再次提到“乃断发取鱼鳞骨同焚”。出发前的祭祀祈风活动大概率是在南海神庙进行,担任广州刺史的杜佑应该也参与了祭祀活动。关于导航的方式,碑文中所写“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荣新江先生认为神灯可能是波斯湾看到的灯塔,直接对应广州通海夷道中所说的“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的说法。陈烨轩则认为,有可能指的是中国传统木帆船船尾处设置的灯台,由南海神庙请来。考虑到熟悉印度洋航行的中国水手很少,尽管所用船只应为中国官船,也有可能在蕃坊之中招募阿拉伯船员同往。
杨良瑶时期,广州的城市有了极大发展。《旧唐书·卢怀慎传》载,开元天宝年间,“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钜万而死”。通过当时担任广州主官因贪赃而被处死的结局,可折射出广州作为商贸名城的地位。作为对比,大历四年(769)时担任广州刺史兼任岭南节度使的李勉则清廉可靠:“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杜佑在广州任职期间,也是广州城市建设因海丝的发达而进一步提升的阶段,“南金象齿,航海贸迁,悍将反覆,远夷愁扰,吏困沓贪,商久阻绝。公乃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可见,在广州担任主官,能够正常引导和管理海外商贸,保持自身的廉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这也是义净、杨良瑶等人在广州活动时的一个基本政治人文生态。
我们尝试绘出杨良瑶这次行动在广州所依托的知识和社会网络。空间角度而言,杨良瑶或其手下应该与生活在制旨寺的僧人和生活在蕃坊的穆斯林商人交往,请教航行知识。佛僧甚至可能参与了南海神庙的祭祀活动,并可能同乘前往室利佛逝王国;而考虑到目的地是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有可能直接登船随同出访。其船只从南海神庙所在的珠江口启航,临行前在此祭祀,沿着广州通海夷道梯航万国。时间角度而言,杨良瑶的知识体系来源于义净、杜环、蕃商等有过远航经历的人,又进而传给了贾耽,海上丝绸之路的知识通过身体力行的航行不断完善和传承。而南海神庙、光孝寺、怀圣寺地,作为文化遗产,也在这些行旅的生命穿插交织之下构建起更有生命质感的联系,焕发出独特的价值。
在广州的光孝寺中,保留着唐宝历二年(826)修建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幢,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经幢实例。同是宝历二年,一艘阿拉伯商船从怀圣寺边的蕃坊码头出发,船上装载了一件当年七月十六日出品的长沙窑瓷器。这艘后世称为黑石号的商船在不久之后沉没,经过一千多年才重见天日;而那座大悲心陀罗尼经幢,则一直伫立在光孝寺。
光孝寺、怀圣寺、黑石号,在同一个历史切片之中,发生了奇妙的联动。广州这座延续两千年的海丝城市,也在这些文化遗产的联系和纠缠下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历史质感,并可以在更大尺度下不断延展——那件长沙窑瓷器,很可能是从长江口的扬州转运而来;同船前来的,或许还有效仿义净当年的路线,从扬州到广州,随后去印度求佛的僧侣,以及往来东南亚的昆仑奴,返乡的波斯客商。这些建筑、遗址、沉船、货物,这些行走在港口之间的远航者,其生命形态本身即是海洋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他们在星辰的指引下前行,在波浪的追逐下扬帆,在遇到艰难险阻时祈祷神明的保佑。他们在这一段特定的时间里,在特定的空间中,是海洋的栖居者,用自己的身体和眼睛,构建出海上丝绸之路上最具质感的故事。
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是文化线路,这条线路不仅是一条条画在地图上的线条,而是无数行动者、海洋栖居者的行动之网,是这些行旅轨迹所构成的生命景观。英戈尔德提出,世界是由“线”组成的。他将“远足”(wayfaring)和“运输”(transport)进行区分,认为现代式的运输消弭了远行中的意义,被运输的人和物只有在抵达目的地时才重新进入这个世界。相对而言,生活在海上的水手,栖居世界的方式更接近于远足,或远航(seafaring)。“远足者或远航者都没有最终的目的地,无论他在哪里,只要生活还在继续,他就可以去往更远的地方。”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每一个行动者,都是英戈尔德意义上的远航者,是大海的栖居者。他们以远航的方式实现栖居在海洋上的生命状态。“栖居者从内部参与了世界不断形成的过程,并通过留下生活的踪迹,对世界的编织做出了贡献。”无论是义净、杨良瑶,还是不知名的商贾、水手,他们通过远航和栖居的方式,编织起一个有血有肉的海洋世界。“旅行者和他的线是一回事。随着他在持续生长和发展或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前进。”远航者的身体和行动,构成海上丝绸之路缠绕不休的线。
这也给我们认识文化线路类遗产的价值有了新的启示。中国的先民是海上丝绸之路共同的创造者。要发掘其中独具中国特色和生命力的部分,需要在宏大叙事之下,进入历史行动者的微观世界和生命景观,理解他们在晴夜观星时的喜悦,在波涛汹涌中的惊心;理解“剪发祭波,指日誓众“的意气风发;感悟“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的孤独寂寞。文化遗产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杰出辉煌和家国意义,这些辉煌和意义背后,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灵所经历和创造的生命景观。他们是文化遗产真正的主语、主人。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 露)

文章由作者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欢迎读者阅读、选购纸本期刊。
敬请阅读:
燕海鸣:《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命景观》,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