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SERINDIA | 萨珊印章上的希腊鸟身女仙
2
春
季
卷
萨珊印章上的希腊鸟身女仙【美】乐仲迪提要:萨珊波斯印章上多次出现人面鸟身的神异动物,但是国际学界对此漠视、误读甚至否认其存在。本文试图对这一印章上的人面鸟身图像加以梳理和分析。源自古典希腊的鸟身女仙哈耳庇厄和塞壬,还有源自印度神话的金翅鸟和紧那罗,都是萨珊波斯人鸟形象的图像源头。本文考证了人鸟图像在萨珊王朝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
一、消失的狮身人面和人面鸟身
就像早期的两河流域一样, 萨珊波斯王朝(224—651) 的人们也喜欢拿组合式神异动物来雕刻印章:比如说鹰嘴狮身的格里芬、牛身人面的格列列之类。但是神异动物的命运并非都是受宠的,狮身人面和鸟身人面的神异动物就是两个悲催的例子。令人好奇的是,源自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居然在萨珊艺术里绝了踪迹。1969 年波斯学家毕瓦尔教授(A.D.Bivar)在伦敦出版的《大英博物馆藏西亚印章图录》一书中指出 :在萨珊王朝取代狮身人面形象的,是蜷卧姿势的有翼人面公牛,身躯明显是牛身而不是狮身。女学者巴艾(E. Baer)也关注过类似的替代现象,发现有须髯的人首神兽身躯是牛身 ;她撰写了《早期伊斯兰艺术中的狮身人面和希腊鸟身女妖:图像研究》,1965 年刊登于耶路撒冷的《东方文书和研究》第 9 期。诡异的是,虽然在早期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 330 年)、帕提亚王朝(前 241—224 年)乃至希腊罗马艺术中,狮身人面兽都是一个核心神兽,萨珊艺术家对于狮身人面的态度却是完 全漠视或者刻意拒纳。但在萨珊王朝覆灭 500 年之后的伊斯兰世界里, 狮身人面像再度出现,诉说着两河流域千年传统的回归。
在萨珊王朝的组合式神异动物中,有一个迄今为止特别经典,却未 被学界充分解读,甚至被否认其存在的艺术图像,那就是萨珊版的人面 鸟身或者说鸟身女仙。为了试图树立起人面鸟身的经典图像系统,巴艾女士单单引用了中亚和印度的考古图像作为它们的直接前身,并建议:“波斯出现的人面鸟身是扎根于古典希腊罗马的艺术灵感”,因为“这一人面鸟身形象在两河流域的图像证据十分稀少,从早期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一直到萨珊王朝千年如一 ;而最终它作为一个经典图像出现在伊斯兰艺术中”。发掘片治肯特古城的俄罗斯考古学家别列尼茨基在 1960 年出版的 《塔吉克斯坦考古》一书中宣称,在前伊斯兰的波斯艺术中根本不存在人面鸟身这一图像。德国学者高布尔则认为人面鸟身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类神异动物,凡是人头、羊头、鹿头的鸟都只能算是附加品。本文就是为 这一人面鸟身神祇鸣不平,重新梳理和分析萨珊王朝印章上的人面鸟身图像。

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的两枚萨珊印章上出现了人面鸟身图像。其中一枚描绘着人鸟天使,上半身是男子的头和躯干,手里握着一个有飘带的花环,下接鸟身鸟尾(图 1)。在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伊朗德黑兰的摩赫森藏品以及设拉子古城外的夸希尔—伊—阿布—纳希尔遗址,都有印章描绘了有须髯和没须髯的鸟身男子(图 2、3、4、5、6)。另一组萨珊印章,则把鸟身鸟尾与绵羊头、羚羊头、公鹿头、阿拉伯叉角羚头拼接。这些图像的不同仅仅是在人面和兽面之间作选择,除了对怪兽和人脸的喜好之外,这些组合式神异动物还表达了萨珊王朝艺术的象征意涵。
二、中亚人鸟源自印度神话
在7—8 世纪的粟特地区、布哈拉古城外的瓦拉赫沙宫殿,苏联考古学家锡思金(V. A. Shishkin)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白垩质壁画残片,描绘了几只有着仙女头脸和胸脯的神鸟,飞翔在巨大的神话狩猎场景中。锡思金考古队复原了这些残片,在复原图上可以看到这些鸟身仙女或者梳着长辫子,或者长长的卷发披落在胸背上,还有一些仙女头顶扎着蝴蝶结发带,胸脯上披着有皱褶的纱衣。她们的身躯有羽毛覆盖,呈大叶子形状,鸟爪的残痕表明她们曾经紧紧抓住树枝。在近年中亚片治肯特古城的发掘中,还出土了两个相似的黏土小雕像,神鸟只有仙女的头,没有躯干。她们出现在一个神龛中,明显组成了一队天国神鸟,昔日曾装饰神庙的穹顶和天花板。这些片治肯特的鸟身女仙小雕像,明显在创作上要比瓦拉赫沙宫殿的壁画残片更为拙朴,仙女的秀发纷披两肩;但与后者相似,她们也把前额的头发扎上印度时尚的蝴蝶结。
瓦拉赫沙的发掘者锡思金, 片治肯特小雕像的发掘者别列尼茨基,都把鸟身女仙解读为印度神话中的金翅鸟(Garuda)或者紧那罗(Kinnara)。 前者本是在烈火中涅槃重生的太阳鸟,也是印度神话中毗湿奴的坐骑,到了4世纪成为印度笈多王朝的皇家标志。在笈多王朝晚期,金翅鸟图像是一个肥胖的鸟身和人脸的组合。而紧罗那分雌雄,雄鸟名为紧那罗,雌鸟名为紧那丽丝,二鸟为情侣,是从印度神话中衍变出来的神异组合。这对人鸟情侣是天国音乐家,出现在中印度公元初的佛教遗址中,或者是稍晚些的中亚佛教石窟中。二者常常是全部鸟身或者仅现鸟尾,人首有时也带人类躯干,翅膀连带着人类双臂,手持花环或者其他供养物。在贵霜王朝的贝格拉姆古城(今天阿富汗境内)出土了象牙做的人面鸟身紧那罗,学者推测是来自于印度的公元初的古物。在同一遗址还出土了一个带釉彩的动物形水罐,有着仙女的头脸、胸脯和鸟身。在印度笈多王朝晚期也就是5—6 世纪,出现了成双成对的人鸟情侣图像,它们有着完整的鸟类身子,仅仅头部采用了人脸。别列尼茨基认为,在中亚瓦拉赫沙和片治肯特古城出现的人鸟图像,是受到印度笈多艺术影响,但进一步放在粟特信仰的语境里来观察,壁画和雕塑中的这些人鸟象征着人类的灵魂。在片治肯特古城的家族神庙里,成对出现的人鸟被用在中亚广泛流行的祭祀祖先风俗中。
三、古希腊鸟身女仙,载着亡魂飞升天国
这些出现在中亚墓葬艺术中的粟特人鸟,是古希腊神话中鸟身女仙 哈耳庇厄和塞壬的重现,她们是引导亡魂升往天国的驮载者。描绘鸟身 女仙载着亡魂飞往天国的最著名例子,是古希腊的“哈耳庇厄之墓”,出自里奇亚省的扎索斯城,年代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之交。在罗马帝国 时代,鸟身女仙哈耳庇厄和塞壬就被铸造在早期皇家钱币上和同一时代的阿瑞底姆器皿上。在遥远的东方,早在公元前 2 世纪,鸟身女仙就已被苦学古希腊的帕提亚人所知,在其古都尼萨(在今中亚土库曼斯坦境内)就出土有此类图像的古物,稍晚在帕提亚统治下的伊朗也有。在上述的 考古例子中,所有的鸟身人面形象都是女性的,躯干胸脯如果有的话也是女性的,虽然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泛希腊化时代也出现过没有性别的塞壬。
在萨珊波斯的印章艺术中,原来的古希腊鸟身女仙哈耳庇厄和塞壬,渐渐变身成了男性,也许是因为萨珊王朝格外推崇肌肉累累的男子。除了看护动物的鸟身女仙还保留着女身,其他出现在萨珊印章上的人鸟都成了男性。例如,手持有飘带的花环、裸体有羽翼的人鸟天使都是男性。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萨珊王朝晚期开凿于塔克—伊—布斯坦的摩崖石窟,其中石窟门楣上的一对胜利天使,手持有飘带的花环,却是女性,风格采自之前塞琉古王朝(前 323—前 131)和帕提亚王朝(前220—244)抛弃的造型。另一方面,萨珊的人鸟造型也可能从东方借来,是印度神话中金翅鸟或者紧那罗的重现。在阿富汗巴米扬石窟 35 米高的大佛背后壁画上,月天(摩诃萨)身边描绘了两个飞翔的人鸟紧那罗,都是有须髯和头发的男子模样。他俩还带着照明的火把,象征着带来光明。另一个人鸟图像来源是两河流域的“祖”,是一个植物神的重生和演化,也常常出现在早期印章上。在公元前 3000 年人鸟纹样十分流行,到处是祖神的传说,这一图像通过晚期亚述王国的印章而留存于世。从那时候起,人鸟开始借用古希腊的鸟身女仙塞壬的形象,但却是男性版的塞壬。男版塞壬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宝石上,明显受到古希腊的影响,只不过人物头上戴着波斯王冠,还有波斯人喜爱的浓密须髯。在比此更早的上古波斯时期,有须髯的人鸟青铜瓶子出现在鲁里斯坦,还有一些人鸟出现在东方青铜大釜上作为捏手,她们是古希腊风格的女性塞壬形象。
还有一个来自贵霜王朝古城贝格拉姆的青铜雕像,描绘了一个人头公鸡。学者库尔茨(O.Kurz)研究了这一头像,发现这个人物是古希腊 商业神赫耳墨斯(罗马名墨丘利),类似图像也出现在古罗马宝石上,墨丘利头戴有翼飞帽、手持双蛇权杖(图 11)。在希腊罗马文化中墨丘利总是和公鸡在一起,因为墨丘利的神格之一是引导着亡魂战胜死亡,安然升上天国;而雄鸡是太阳的使者,也是死而复生的吉祥象征。墨丘利掌管亡魂的这一神格,在钱币上和宝石上常常与鸟身女仙哈耳庇厄和塞壬混同。据笔者研究,在萨珊印章上的鸟身经常是公鸡、鸭子、孔雀、老鹰之类。此处墨丘利的头和公鸡身结合,其他非萨珊的考古图像出现的则是鹰身。综上可知,萨珊王朝的人鸟图像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的元素,也吸收了古印度神话的元素,然后带有相似的内涵和神格功能。
1
插图目录
1 大英博物馆,萨珊印章,藏品 WA I I9376 号。
2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萨珊印章,藏品 GL I242 号。
3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萨珊印章,藏品 GL 1410 号。
4 纽约大都会艺术馆,萨珊印章,藏品 62.66.24 号。
5 伊朗德黑兰博物馆,摩赫森藏品。
6 德国柏林伊斯兰艺术馆,藏品 VA 1486 = No. 8。
7 纽约大都会艺术馆,萨珊印章,藏品 38.40.99 号。
8 印章痕迹,印度笈多王朝,约 530 年(Banerjea,op. cit.,P1. XXVIII :I)。
9 尼萨古都出土的帕提亚王朝鎏金银碗,底座为塞壬造型,现藏 于土库曼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阿什哈巴德城。
10 早期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图章,纽约大都会艺术馆藏品,41.I60.268 号,描绘了一个戴王冠、有须髯的人鸟站在花朵上。
图 11 罗马帝国的宝石印章,描绘有着商业神墨丘利头的公鸡,采自富特旺格勒(A.Furtwangler)著《德国文物》,1900 年柏林出版,图版 . XLVI :29。
其中图 2、图 3 和图 6 的萨珊印章是笔者亲手制作的印章痕迹,在此鸣谢下列学者盛情邀请笔者前往各大博物馆访学:
德国柏林伊斯兰艺术馆,布里斯奇教授(K. Brisch);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珀教授(P. O. Harper);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鲁考宁教授(V. G. Lukonin)。
(本文初次刊登于大英波斯学院出版的《伊朗》学刊,1975年第13期,第166—171 页。2009 年7 月刊登于 JSTOR 国际学术网站。)
本文选自《丝路艺术》春季卷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 乐仲迪博士 Judith Lerner

哈佛大学艺术学博士, 现任纽约大学古代学院教授,《丝路艺术》期刊编委。历任华盛顿史密斯学院讲师,哈佛大学副教授,维也纳大学访问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教授,科威特皇家讲席教授等。精通中古波斯语、大夏语,近二十年来是唯一以现代波斯语在西亚国家大学授课的欧美考古界女学者。
在国际考古领域,成果涉及粟特、大夏、波斯的壁画、摩崖、印章、金银器等。本人多次参加波斯波利斯、巴比伦、大夏、犍陀罗考古遗址发掘,也在考古场地经历过战火洗礼。
译者 毛铭(Mao Ming)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亚考古队员伦敦大学《中亚艺术考古学刊》编辑,北京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丝路艺术》期刊编委,《丝路译丛》(《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唐风吹拂撒马尔罕》《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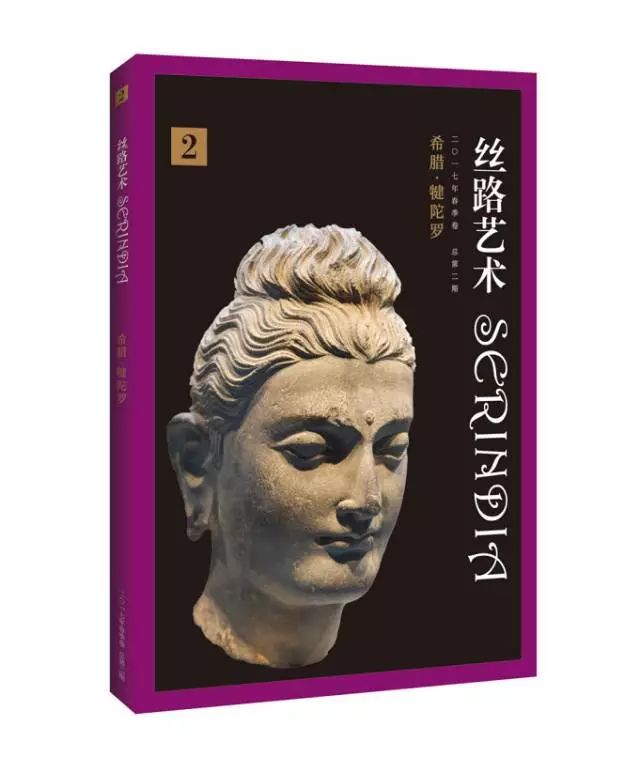
刊名:丝路艺术
英文刊名:SERINDIA
出版方:漓江出版社
2017 年春季卷 总第 2 期
字数:150 千字;图幅数:160
页码:236;开本:1/16
定价:45.00 元
出版时间: 2017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