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王炳华:从新疆考古觅丝路精神——“丝绸之路与西域考古系列讲座”第三讲纪要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3月31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丝绸之路与西域考古系列讲座”邀请著名考古学家,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炳华先生作了题为“从新疆考古觅丝路精神”的讲座。讲座吸引了自治区相关研究单位、新闻媒体和爱好新疆历史文化的各界人士到场聆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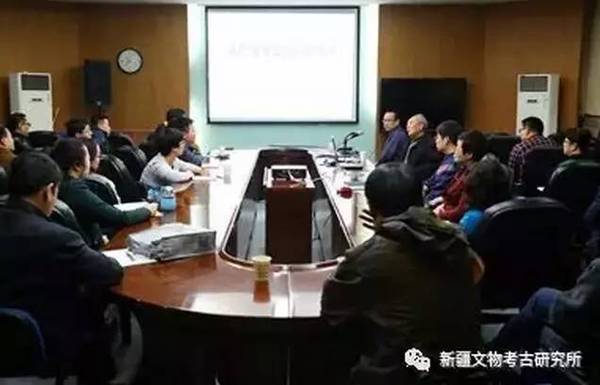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炳华先生在新疆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讲座伊始,先生以自身的工作、研究、治学经历,回顾了个人学术研究所历经的风风雨雨,这些既是个人的宝贵历练,饱含了先生对新疆考古的热爱之情;也是新疆考古发展所历经的成长,让人动容。听讲者通过先生的经历深刻体会到,要通过新疆考古认识西域文明,既需要深入的开展考古工作,把握考古文物的细节;又要跳出新疆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认识相关细节,才有可能更深刻品味到古代新疆的历史文化内涵。感受新疆考古在认识新疆史、中国史、欧亚文明交流史方面的重要作用。
进入主题后,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实例,就丝绸之路的开拓、丝绸之路与新疆、新疆考古与丝路研究、新疆考古与现实社会四个方面向大家作了精彩的讲解。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
先生指出,“丝绸之路研究”是当下的显学,这得益于总书记“丝绸之路经济带”伟大战略的提出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提出,是指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丝绸贸易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实际上,“丝绸之路”并不只局限于丝绸的贸易与交往,它实际上是亚、欧、北非不同政治、经济实体间物质、精神文明交流的总称。在地球形成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地质资源有异,各地居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各有千秋。因此,追求新的物质、精神文明,改善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人类群体的本能,也是一种非常伟大的驱动力量。在这种自发力量地驱动下,亚欧大陆从上古时便产生了交往、交流,为丝绸之路的滥觞。
自发的、本能的追求推动了丝绸之路从萌发逐步走向兴盛。此过程中,汉武帝起了重要作用。“汉初匈奴凶黠”,雄踞北方,不仅常年侵犯汉之边境,也控制着汉王朝向西的陆路通道。因经济、军事力量的差异,汉王朝多采用和亲方式确保边境平安,即便冒顿单于发来“孤偾之君,生于沮泽,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充满蛮横亵狎之气的国书,吕后也只能以“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来应对。在外蒙诺彦乌拉等匈奴贵族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得、上林苑制造的丝绸、漆器即是当时和亲的实证。后历经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汉王朝国力强盛、将才辈出、军事强大,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虽然此行未能达到目的,但却打通了东西方的交流。此后,历经近十年的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彻底击败了匈奴,张骞的再次出使西域,开拓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交流通道——“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疆土的扩张同样激起了汉王朝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奉旨西去的官员考察、记录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情况并呈报朝廷,中国和外界的贸易交流随之进一步开展。丝路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民间到政府组织、管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受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难免存在有冲突。因此,丝绸之路的发展并不是一路玫瑰,处处鲜花,往往伴随着矛盾甚至是灾难性的冲突。

二、丝绸之路与新疆
先生提出,特定的地理环境虽然不能决定历史进程,但却可以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要的,特定情况下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古代中国,位居欧亚大陆东南,北临砾漠,东南大海,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相对封闭,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对外的开放程度较低,与其他文明的联系较少,直至清乾隆时期,仍固守“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观念。
从某种程度上讲,受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尚未掌握信风和航海技术之前,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交往主要依赖“丝绸之路”进行。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西出玉门关,无论是沿着天山南、北麓还是昆仑山北麓,均可通往一个崭新的世界。虽然这条道路有戈壁、沙漠、冰川、雪原等不少阻障,但却还是人力、畜力能跨越的道途。实际上远在人们掌握、发明文字以前,先祖们己经筚路蓝缕,一步步、一程程,接力捧似地拓展,不断走向了远方:美索不达米亚,是欧亚大陆最早培育、种植小麦的中心,距今4000年前的孔雀河流域古墓沟、小河墓地也出土了小麦;小河墓地发现的贝珠,用材为只产自南海的海菊蛤;同时段,这里也种植了最早在华北平原培育出的粟;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崇信的麻黄,与古代印度居民崇信的“苏麻”、古代伊朗人民信仰的“豪麻”,经生物学家验证,就是同一种植物;孔雀河古代先民生活中最重要的黄牛,属早期欧洲品系……林林总总,这些考古文物,清晰提示在人类还没有文字记录前,新疆大地上早就存在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
汉武帝击败匈奴后,设置西域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彻底打通了古代中国与欧亚、北非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通道,在历代中原王朝的有力统治和悉心经营下,西域借助特殊的地缘优势,成为了四大文明交汇的中心、互相影响的所在。
三、新疆考古与丝路研究
先生指出,考古材料在研究、复原历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远古时期,不见文字记录,但人们实际展开过的物质、文化生活,总会留下片鳞只爪,在难以尽说的机缘下,进入沙尘之中;人类步入文明后,发明了文字,大量的史实被掌握文字工具的精英分子们记录下来,成为了传世的文献,但这些文献资料无一不是为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服务的,无一不蕴涵、表现着文字作者的追求,存在有一定的局限。相反,考古资料则存在偶然性、随意性,是先民们在无意识的情势下丢弃的存在,是特定时段内的物质、精神的真实存在,历经岁月,又十分偶然地进入考古学者们的视野。将这些偶然的、无序的、实际存在的考古资料放在特定的历史基点之上,就能够破译和把握当时社会物质生产、工艺、科学技术、精神文化的种种细节,从而成为认识特定时段先人们物质精神文明的素材。
新疆地理位置特殊,自然气候干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来自多种文明的珍贵遗存在这里完整的保存,成为复原和认识西域史、中国史、世界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素材,许多文献中不见记载或无法理解的内容在新疆考古中得到了答案:如文献记载的“琅玕”一物,至今尚未明确。百年前,斯坦因在尼雅遗址N14(现已确定为精绝王室的一处垃圾堆中),获得8枚汉简,清楚记载,“琅玕”是当年精绝王室成员间持以互赠、联络感情的瑰宝。尼雅墓地发掘时,在多个贵族墓主贴身随葬的皮套内均装有一至两颗蜻蜓眼玻璃珠,从发现的位置看,极为珍贵,显然不是作为装饰品使用,应具有辟邪、祈福的特殊功能。无独有偶,这种原产埃及,时代早到公元前15世纪的玻璃珠(材质为钠钙玻璃),公元前9世纪,见于新疆轮台,至公元前5世纪,已普遍见于山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贵族墓中,成为当地贵族心目中的神物,视其为可以带来生命、幸福的宝贝,不惜为它倾其所有。这种被赋予了特殊内涵的蜻蜓眼玻璃珠,很可能就是文献所载之“琅玕”;连接天山南北的阿拉沟,地处偏僻,与文献记载的丝路干道无法相提并论,但仍可见到来自中原地区的精美漆器、山字纹铜镜、凤鸟纹刺绣和来自西边的祆教祭祀台、金、银器等。这些鲜活的考古资料,蕴含着大量未见于文献著录的历史事实,亟待进一步整理、分析、研究。
新疆特殊的历史文化遗存,要求从事新疆考古的工作者,要有广阔的视野,注重与周边的联系。例如,《汉书·西域传》中所载的“奄蔡”(即现今的高加索地区),这里两边临海,高加索山脉自西北向东南横贯于黑海和里海之间,地貌多样,人种复杂。是南欧地区进入西亚、南亚、东亚的一条天然的、最重要的陆上通路。当有战争发生或气候变异时,北欧人群会沿此通道向南迁徙,公元前2000年的一次小冰期,导致了一次大的人口迁徙。因此,在现在小河、古墓沟墓地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中可以见到古典欧洲人的特征;距今三千年前雅利安人的南下,改变了印度、伊朗的历史;距今一千年前,希波战争影响下的斯基泰人与新疆地区关系密切。这些人口的迁徙表明,来自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通过高加索地区进入中亚后,会沿着各个通道向周边辐射,通过天山走廊进入新疆地区,进而与华夏文明产生交流,无疑是一条重要的通道。那么,这些人口的迁徙与文化的交流究竟对新疆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就十分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梳理研究。
哈密五堡、雅尔墓地发现的实木车轮,曾在距今5000-4000年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普遍使用,在宫廷的建筑绘画、雕塑上,在墓葬出土的遗物中都可以见到。其制作工艺与哈密发现的实木车轮不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所见车轮是采用木板铆钉成圆形,而哈密发现车轮则是将两个半圆用木楔楔成圆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存在怎样的联系?就很值得分析。同样,将人的两条腿或动物的四条腿转化为轮式运动,在世界文明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哈密白杨河水系早期文明是否与西亚有间接地交往,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这些考古材料看似琐碎无序,但鲜活、具体的表现着古代新疆的特殊地理优势和丝绸之路物质、精神文明交往的情形,全面的认识新疆出土的文物,加强新疆考古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西域文明、中国文明、丝路文明和欧亚大陆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新疆考古与现实社会
先生在波士顿大学访学时,曾与东亚考古与文化史系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慕容杰教授(Robet E.Murowchick)交流,对其“考古学研究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后面都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的观点深感为然。在印欧语研究界影响一个多世纪的“吐火罗”研究,即是显例。二十世纪初,当德国考古队将得自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的佛经《弥勒会见记》残页携归柏林时,扉页上的“Toχri”引发了印欧语研究学者西格(E.Sieg)、西格林(W.Siegling)的注意,他们很快将这一题识与印欧语西支中的“吐火罗”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就是消失无痕的“吐火罗语”在新疆土地上的两种方言,通行在焉耆——吐鲁番者为“吐火罗语A”,通行在库车绿洲者为“吐火罗语B”。这一观点提出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其中,不乏批驳之声,法国学者列维、伯希和根据库车地区所获的文字残片指出,佛经出土地早有“龟兹”“焉耆”的自称,与“吐火罗”并无关联;出土的相关文献,是公元5到8世纪左右的遗物,与印欧语早期时段的“吐火罗”在时代上存在很大的悬殊;从语言学本身的研究出发,也存在不少的疑点。此后,关于“吐火罗”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但从未撼动德国学者的信念。与西格、西格林最初可能是从语言学研究角度出发不同,在20世纪初的德国语言、考古、民族研究学中,不少人坚持“吐火罗语”研究结论,是别有深厚感情寄托在其中的。作为印欧语西支的吐火罗语,原生地与北欧有重大关联,出现在新疆,就可能意味着早期北欧居民尤其是日耳曼民族很早就到达了这片地区,这对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与欧洲其他列强在对中、西亚殖民扩张的争夺战中,无疑提供了一种民族、文化、感情上的理论支撑。对这一点,表达得最清楚的是冯·勒柯克,他在1929年刊发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大作中,毫不隐晦的宣称“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印度人占据着,沙漠的西沿伊兰塞人占领者,沙漠的西北边缘是伊兰粟特人(Soghdier),从库车到吐鲁番却是那些欧洲印度——日耳曼语的蓝眼睛民族,吐火罗人(Tocharer)。所有这些部落都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佛教……随着民族迁徙,刚刚兴起的欧洲日耳曼国家历史的重要时期开始了。”将一个尚无科学结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语言学现象,十分清晰、毫无顾忌的化为了一种政治概念,注入了强烈的政治、经济利益,满溢着殖民主义的追求。考古文化与政治的关联、被政治绑架的现实,清楚的呈现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实际上,关于吐火罗人由欧洲东迁的历史事实,在斯特拉波的地理著述和汉文史籍中均有记载。隋、唐时期的史著,玄奘的行纪,都清楚记述,吐火罗国是早就出现在今阿富汗斯坦大地上的历史存在,与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关联密切。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前些年出土的一份唐代文书中,记载了一支来自西亚的商队在吐鲁番接受关卡检验的情况,其中商队中的几个吐火罗人,身份遭到了严格的核验,从核验过程看,当时吐鲁番地区根本不知道吐火罗语为何物。吐鲁番晋唐时期出土的文书,上引只是个例。新疆现藏的吐鲁番汉文文书,总数过万,时代在公元四至十世纪之间,是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以汉文为主要文字工具的最有力说明,如果当年吐鲁番曾是吐火罗语A流行的地区,为什么在考古发现中却截然相反?德国学者对这些当时人记当时事的著作,一概不见,背后内涵着强烈的政治利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的“吐火罗语”讨论,已逐渐沉寂。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当古墓沟、小河墓地发现的古尸被研究者认为具有古典欧洲人特征时,一些学者又有意无意将它们与“吐火罗人”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学者的《乌鲁木齐古尸》《新疆古尸》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们将吐火罗跟新疆地区现代的民族联系在一起,妄称新疆地区从来就是某个民族的主源地,新疆文明的开始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背后别有用心的政治追求表现得十分清楚。“Toxirei”一词,在不同时期引发的不同分析和舆论导向,清楚的表明,考古学确实与现实的政治利益挂钩在一起,密切关涉着现实社会的追求,毕生以新疆考古为事业的A·斯坦因在新疆持续数十年的活动中,从不把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称之为新疆,而称为亚洲腹地,并生造出“Serindia”一词,意味古代中国(Seris)与印度(India)之间的土地。对发现的与希腊、印度文化有关的遗存,记载阐发极为详细;但对发现的汉文化遗存却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其背后的寄托、追求,与德国学者们在“吐火罗”研究中的情结,并无差异。
因此,先生认为,考古学初看似乎是纯文化的研究,但却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尤其是主动性的选题,从选题到工作的开始、到研究报告的完成,都可能存在特定利益的追求。在新疆做考古,面对当前新疆“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面对如此特殊、庞杂的文物材料,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力求把问题搞的比较清楚,比较准确,以具体的实物和真实的历史服务于新疆的稳定与祖国的统一。
最后,先生再次以阿拉沟唐代古烽——鸜鹆镇的研究实例告诉后辈学者新疆考古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舞台、是一个造就人的舞台、一个出大学问家的舞台。新疆考古,涉及面广。从事新疆考古,不能不了解文献,但无法、也无力全部掌握相关文献,因此要放开胸怀,加强多学科间的合作,取长补短,收获成果,这也是当下考古学发展的趋势与必然要求。
随后的互动环节里,先生就听讲者提出的楼兰考古、汉代屯田、新疆考古与旅游业的结合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个半小时的讲座,年过八旬的先生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饱满激情,对具体问题抽丝剥茧,层层展开,要言不烦;听者亦沉浸其中,并深为他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特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所折服。无论是在具体知识、研究方法及研究态度上,在场的后学俱获益良多。
(党志豪整理、王炳华先生审定 文章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