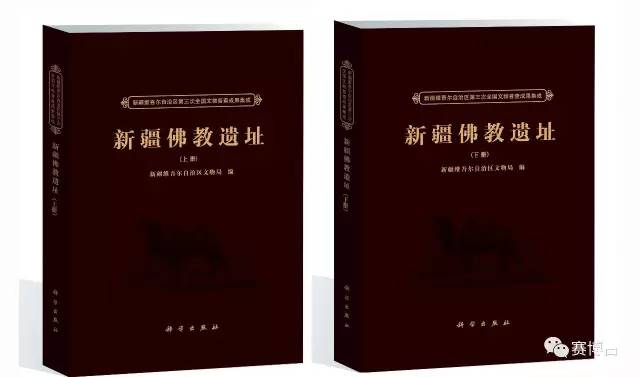研究前沿
新疆佛教遗址的考察与探险活动
2016-12-17 赵莉 赛博古
佛教产生于印度,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印度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佛教继承了印度崇尚艺术的传统,佛教思想借助造型艺术的有力支撑,使佛教艺术达到极高的成就,因而佛教也被称为像教。
佛教从印度向外传播,主要有两条路线,即“北传路线”和“南传路线”。北传路线自印度西北部出发,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传入西域,继续东传进入中原。这条传播路线就是沿着古代贯通东西方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行进的,因此,学术界称这一线上的佛教为“丝路佛教”。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传入新疆。配合佛教弘法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说唱、变文等佛教艺术亦十分兴盛。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经过与西域的传统文化融合发展,新疆地区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丝路北道有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丝路南道有于阗和鄯善。两道南北相应,构成了繁盛的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佛教文化环形带。从公元前后开始,至15世纪,在这片土地上,先后有月氏人、汉人、吐火罗人、吐蕃人、回鹘人等信仰佛教。而佛教的大、小乘部派及密教在西域都有传播。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多样的佛教宗派使西域佛教更加丰富多彩,也使西域佛教艺术绚丽多姿。
佛教传入中原是以西域为媒介的,新疆是我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区,也是佛教从印度向东传播的桥梁。
汉唐间,在这条东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上,西来的天竺、西域经师为传佛法持箧东进,中原大德为求佛法负笈西行,经年络绎不绝。西域译经高僧的足迹和他们的翻译成果遍及中原大地,对我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汉地佛教与西域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国大乘佛教的“华严”思想,离不开对于阗佛教的研究,研究敦煌、云冈等佛教艺术离不开对龟兹、高昌等佛教艺术的研究。因此,有学者称,西域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第二故乡。
由于佛教的兴盛,新疆地区建造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寺。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虽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仍然保存下来为数众多的遗存和遗物。其中一些遗址在20世纪初被外国探险队发现和发掘过,还有一些是近30年来新发现和发掘的。这些佛教遗址,反映了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况,同时也包含了古代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诸多重要信息。
在印度,佛教建立初期,并无寺院。佛教徒按照佛陀制定的“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的制度,白天到村镇说法,晚上回到山林,坐在树下,专修禅定。后来摩揭陀国的频毗沙罗王闻听释迦牟尼说法后,皈依了佛教,布施迦兰陀竹园,印度佛僧才有了第一座寺院。印度人称寺院为“僧伽蓝摩”,略称“伽蓝”。伽蓝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精舍式,二是支提式。精舍式的伽蓝,设有殿堂、佛塔,殿堂内供奉佛像,周围建有僧房。支提式伽蓝,是依山开凿的石窟,内有佛塔和僧侣居住处。
这两种式样的伽蓝,先后传入了中国。印度“精舍式”伽蓝传入后,很快与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相结合,成为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佛教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已采用中国传统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重,层层深入。到了隋唐时期,供奉佛像的佛堂,成为寺院的主体,塔被移到殿后,或另建佛塔,这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已有很大的不同。
石窟通常也称为石窟寺,就是开凿在河畔山崖间的佛教寺院,石窟寺在形式上虽然与地面上的土木结构的寺院有所不同,但它是模仿地面寺院建筑而建造的,规模较大的石窟寺大都有与一般木结构寺院相同的功能,其本身就是一座寺院,是供信徒礼拜、供养、起居和禅修的场所。丝绸之路新疆段北线保存有大量的石窟,而在南线几乎全是寺院和佛塔,不见石窟。
新疆佛教遗址被重新发现肇始于18世纪中叶清代的一些文人官吏,在他们的著作和游记中对一些石窟寺有所记载。1916~191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官员谢彬到新疆调查财政状况,同时也关注了新疆各地的历史、地理、民俗等,在其所撰的《新疆游记》中对新疆部分地面佛教遗址有所记载。
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染指亚洲腹地,先后有俄国、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派遣“探险队”来新疆考察,他们从新疆非法挖盗掠走大量精美珍贵的文物,使本已成凤毛麟角的历史遗存又遭浩劫,造成新疆文物的巨大损失。在流失国外的文物中,佛教文物占很大比重,其中包括各种文字的经卷、文书,石窟寺的雕塑、壁画、绢画、木板画、纸画、建筑构件、舍利盒等。其中于阗、疏勒和焉耆寺院的雕塑以及龟兹和高昌的石窟壁画等损失最为惨重。现在新疆佛教文物收藏在德国、法国、英国、匈牙利、土耳其、俄罗斯、美国、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几十个博物馆和美术馆中,还有一些收藏在私人手中。
首先是瑞典人斯文·赫定,他于1895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这一发现引起西方学术界对新疆古代遗址的关注。之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俄国的奥登堡以及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均在这一地区做过考古调查发掘。
斯坦因于1901~1914年间在新疆进行了三次考察探险,于阗、疏勒、焉耆、吐鲁番的地面佛教遗址是其调查的重点。
伯希和在1906~1908年期间调查发掘的主要地点是疏勒地区的图木舒克和托库孜萨来佛寺遗址、龟兹的夏合吐尔和玉其吐尔(都尔都尔阿库尔)遗址与苏巴什佛寺遗址。
德国探险队在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的带领下,1902~1914年间先后在新疆进行了四次考察和发掘。前两次的重点在吐鲁番地区,后两次则主要在龟兹地区。
1902~1914年期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龟兹部分石窟以及高昌部分石窟进行了测绘和小规模的发掘。同时,他们先后调查发掘了楼兰、米兰等佛教遗址。
俄国的别列佐夫斯基于1905~1907年,奥登堡于1909~1910年先后率领考察队考察了焉耆、龟兹和高昌地区的佛教遗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活动加以禁止。因此,这个阶段国外探险家的考古发掘不如前一阶段频繁,主要是1928年德国的特林克勒在于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新疆大批文物的流失使当时中国学术界深受刺激,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保护国宝和关注西域的考古发掘。1927年,以黄文弼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为标志,中国学者也开始在新疆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1928~1930年,黄文弼对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佛教遗址都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的发掘。
我国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于1946年和1947年两次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他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拍照和临摹,还发掘清理了一个洞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界继续关注新疆佛教遗址,但相关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不多,其中主要有:
1953年,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对新疆各地石窟进行调查,对洞窟进行了编号。1957~1958年,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沿线佛教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其中包括对焉耆七个星佛寺和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的重新发掘。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了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了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
1959年和1983年,新疆文物工作者在托库孜萨来古城发掘和调查,获得很多遗物。
1978~1979年,新疆博物馆对米兰佛教遗址进行调查。1979年秋,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考察了喀什的三仙洞。
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带领研究生马世长、晁华山、许宛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生丁明夷四人,到克孜尔石窟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石窟考古实习,期间还调查了库木吐喇和台台尔等石窟。
20世纪70~8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谭树桐先后多次考察龟兹石窟。
1979年和1987年,北京大学晁华山先后两次在七个星石窟考察。
197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吉木萨尔县北庭西大寺进行了发掘与考察。
1980~1981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崖前遗址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发掘。
1986~1991年,《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编辑组对龟兹石窟和高昌石窟进行了多次调查。
为配合克孜尔石窟维修保护工程,新疆文化厅文物保护维修办公室、新疆文物保护研究所和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于1989、1990、2000年先后三次对谷西区和谷内区窟前进行清理发掘,共清理出洞窟30余个。
198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机构合作组成的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察。1995年,对遗址北部的佛堂(FS)遗址进行了发掘;翌年,又发掘了佛堂周围编号为93A35中的FA、FB、FC、FD遗址。这次联合发掘向人们展现了魏晋时期精绝佛教寺院、佛教艺术和佛教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使尼雅遗址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93~199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交河故城发掘西北小寺和一座地面寺院遗址。
1993~1994年,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河保护修复工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组织专家对交河故城的佛教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这次除了过去调查和发掘的9处佛教遗址外,还重点调查了43处佛教遗址。
1995年,第二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在克孜尔石窟举办,学员实习期间考察了龟兹诸石窟。
1996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和法国科学院联合调查发掘喀拉敦遗址,清理了两座寺院。同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找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
1998年,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还未来得及对丹丹乌里克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前,瑞士人鲍默带领所谓“中瑞探险队”对该遗址私自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2000年以来,新疆龟兹研究院(原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多次组织专业人员前往龟兹各石窟进行考察,测绘并记录洞窟形制和壁画题材内容及现状等。
2002年10月,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迹学术研究机构共同组队考察丹丹乌里克时,发现一座佛寺遗址,暴露出部分残存的精美壁画;同年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座佛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是中国文物考古专业机构对丹丹乌里克遗址进行的首次正式考古调查与发掘。
2002~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策勒县达玛沟托普鲁克敦1~3号佛寺建筑基址进行发掘。
2006~2009年,为了配合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五次对高昌古城进行了清理发掘,包括大佛寺、大佛寺北佛塔、东南佛寺和内城西墙上佛寺等遗址。
2008年,为了配合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台藏塔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2009年,为配合柏孜克里克石窟窟前抢险加固工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涉及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居址、佛塔、洞窟等各类遗迹52座。
2009年和201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胜金口石窟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洞窟13座、居址26间。
2010~201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库车县文物局对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察。
2010~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和新疆龟兹研究院联合清理发掘了吐峪沟石窟群沟东区和沟西区窟前部分洞窟。这是我国实行新的田野考古规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石窟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对今后类似工作有极大的示范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吐峪沟石窟的内涵、价值及地位。
此外,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对新疆地区的所有佛教遗址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并整理出了相关的普查报告。
本文由孙莉、刘能摘编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 编《新疆佛教遗址》(上下册)之“概述”。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新疆佛教遗址》是“新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丛书之一。收录了新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151处佛教遗址和增补的56处佛教遗址,共计207处。全书按照古代区域划分为于阗、鄯善、疏勒、龟兹、焉耆、高昌和伊吾七个部分,各部又按照现行地州(市县)行政区划顺序编排,同时还补充了大量流失海外的新疆佛教遗址藏品。本书反映了目前关于新疆佛教遗址最全面的综合性成果。